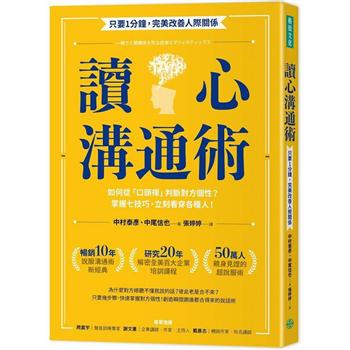真正的獨家不在報紙頭條
在總編輯的筆記裡
◎近距離記錄金融危機、中國崛起、新媒體興起、民粹與恐攻、英國脫歐、川普執政、美中貿易戰,傳達劃時代變動氛圍。
◎與北京、莫斯科、柏林、利雅德、德黑蘭、東京、華府等執政者對談,旁觀掌權者面貌,一窺高層決策與政治算計。
◎力促「金本位」報導、編採自主,推動報社改革,帶領《金融時報》從傳統紙媒轉變為獲獎項肯定的數位媒體。
洞察動盪的15年,以鋒利之筆描繪富豪與強人的焦慮與脆弱。
這本筆記是「危機時代」的第一手見證、領導者的快照。
身為《金融時報》總編,巴伯以職位之便突破知名人士身邊的保護泡泡,近距離與掌權者及(偶而會有的)壞蛋私下互動。
他記錄了新聞編輯台面臨新媒體興起、金融風暴、中國崛起、民粹主義、英國脫歐,以及主流媒體與假新聞鬥爭的採訪報導內幕與心路歷程;寫下遇見的新聞製造者:政治領袖、倫敦與華爾街金融人士、身價億萬的銀行家、王室貴族、矽谷科技大師、外國使節,他們之間的交流訪談、私下會面的插曲。甚至在雷曼兄弟倒閉前採訪了執行長富爾德,還有歐巴馬、溫家寶、林鄭月娥、黃之鋒的深度訪問,並數次與川普、梅克爾、普亭過招。
數百則筆記毫無保留公開這時代權貴(有時還有壞蛋)的即時反應,以及值得細細品味的微妙時刻。可見識到大媒體總編輯的工作與生活,也可當散文閱讀。幽默、誠實、有見地,有時直率得令人發笑。
| FindBook |
有 13 項符合
權貴與壞蛋——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世工作筆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權貴與壞蛋——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世工作筆記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萊奧納.巴伯Lionel Barber
2005年至2020年間擔任《金融時報》總編輯,成功將英國《金融時報》從傳統新聞報社轉型為多頻道的全球新聞機構。在擔任總編輯期間,《金融時報》突破了100萬付費訂戶的里程碑,新聞工作贏得許多國際獎項與讚譽。《金融時報》在2008年、2017年和2019年的英國新聞獎中被評為年度報紙/新聞提供商。
譯者簡介
謝孟達
曾任新聞編譯與翻譯社譯者。譯著包括《大數據與公共政策》、《我哥的名字是潔西卡 》與《找到你的聲音:國際頂尖教練教你在任何場合自信說話》等書。賜教信箱:craftlingual@gmail.com 個人網站:https://craftlingual.cloudaccess.host
萊奧納.巴伯Lionel Barber
2005年至2020年間擔任《金融時報》總編輯,成功將英國《金融時報》從傳統新聞報社轉型為多頻道的全球新聞機構。在擔任總編輯期間,《金融時報》突破了100萬付費訂戶的里程碑,新聞工作贏得許多國際獎項與讚譽。《金融時報》在2008年、2017年和2019年的英國新聞獎中被評為年度報紙/新聞提供商。
譯者簡介
謝孟達
曾任新聞編譯與翻譯社譯者。譯著包括《大數據與公共政策》、《我哥的名字是潔西卡 》與《找到你的聲音:國際頂尖教練教你在任何場合自信說話》等書。賜教信箱:craftlingual@gmail.com 個人網站:https://craftlingual.cloudaccess.host
目錄
登場人物
前言
第1部 活在金融時代
二〇〇五年:序幕
二〇〇六年:泡沫隱憂
二〇〇七年:信貸緊縮
第2部 全球墜落谷底
二〇〇八年:雷曼倒閉
二〇〇九年:餘波盪漾
第3部 樽節當道、列文森調查與IPHONE世代
二〇一〇年:聯合政府
二〇一一年:海嘯
二〇一二年:新媒體與舊媒體
二〇一三年:報慶盛事
二〇一四年:萬年王儲
第4部 英國脫歐與國族民粹主義崛起
二〇一五年:日經登場
二〇一六年:英國脫歐
第5部 終章
二〇一七年:屹立不搖
二〇一八年:總裁俱樂部
二〇一九年:傳承接班
後記
謝誌
前言
第1部 活在金融時代
二〇〇五年:序幕
二〇〇六年:泡沫隱憂
二〇〇七年:信貸緊縮
第2部 全球墜落谷底
二〇〇八年:雷曼倒閉
二〇〇九年:餘波盪漾
第3部 樽節當道、列文森調查與IPHONE世代
二〇一〇年:聯合政府
二〇一一年:海嘯
二〇一二年:新媒體與舊媒體
二〇一三年:報慶盛事
二〇一四年:萬年王儲
第4部 英國脫歐與國族民粹主義崛起
二〇一五年:日經登場
二〇一六年:英國脫歐
第5部 終章
二〇一七年:屹立不搖
二〇一八年:總裁俱樂部
二〇一九年:傳承接班
後記
謝誌
序
出自世界上最知名的記者,此書必讀。你會在書中遇到國際金融、政治和媒體領域的關鍵人物,看到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在壓力底下的想法。書一旦翻開,真的停不下來!——蘇世民(Steve Schwarzman),黑石集團董事長兼執行長,著有What It Takes: Lessons in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除了有引人入勝的報導和軼事,這本書是他對真正新聞的信念和承諾:尋求事實,而不是置於預設的描述中;平衡和公平是基本,沒有恐懼或偏袒;並善盡報紙解釋和告知的任務。透過接觸領導世界的商業、金融和政治人物,對動盪時代的十五年有非凡的個人與專業洞察力。——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前英國首相
妙語如珠的萊奧納.巴伯講述他在確保《金融時報》在數位時代蓬勃發展時所遭遇的人物與議題。你會發現,這是本宣導新聞美德的最佳著作。——麥可.莫瑞茲爵士(Sir Michael Moritz),矽谷風險投資家、布克獎贊助者
從前排見證到的權力、金錢、自私與災難的世界。——沙茲(Philipe Sands),作家,著有《人權的條件》、The Ratline
一本非凡的書……巴伯的作品時而殘酷精采,時而滑稽可笑……同時是一份寶貴的歷史記錄,深刻反思瞬息萬變環境中的媒體,最重要的是,他用鋒利之筆描繪富豪與強人的焦慮與脆弱。不要錯過。——米夏.格蘭尼(Misha Glenny),BBC影集《黑道無國界》(MCMAFIA)原著作者
非常有趣且有見地的編年史,記錄了一位頂尖編輯訪問VIP、寫強硬報導的走鋼索生活,而那些VIP通常不欣賞那些報導。從普亭在大使館晚宴上用鋼琴彈奏《筷子華爾滋》,到金融崩潰和英國脫歐的動盪,巴伯站在前排看到這一切。他將英國《金融時報》改造成數位媒體,並擴展了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力。讀來令人振奮。——哈羅德.埃文斯爵士(Sir Harold Evans),《星期日泰晤士報》前主編
關鍵十五年的真正內幕——來自目睹一切的編輯。
——米莎.海珊(Mishal Husain),BBC廣播四台Today節目主持人
除了有引人入勝的報導和軼事,這本書是他對真正新聞的信念和承諾:尋求事實,而不是置於預設的描述中;平衡和公平是基本,沒有恐懼或偏袒;並善盡報紙解釋和告知的任務。透過接觸領導世界的商業、金融和政治人物,對動盪時代的十五年有非凡的個人與專業洞察力。——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前英國首相
妙語如珠的萊奧納.巴伯講述他在確保《金融時報》在數位時代蓬勃發展時所遭遇的人物與議題。你會發現,這是本宣導新聞美德的最佳著作。——麥可.莫瑞茲爵士(Sir Michael Moritz),矽谷風險投資家、布克獎贊助者
從前排見證到的權力、金錢、自私與災難的世界。——沙茲(Philipe Sands),作家,著有《人權的條件》、The Ratline
一本非凡的書……巴伯的作品時而殘酷精采,時而滑稽可笑……同時是一份寶貴的歷史記錄,深刻反思瞬息萬變環境中的媒體,最重要的是,他用鋒利之筆描繪富豪與強人的焦慮與脆弱。不要錯過。——米夏.格蘭尼(Misha Glenny),BBC影集《黑道無國界》(MCMAFIA)原著作者
非常有趣且有見地的編年史,記錄了一位頂尖編輯訪問VIP、寫強硬報導的走鋼索生活,而那些VIP通常不欣賞那些報導。從普亭在大使館晚宴上用鋼琴彈奏《筷子華爾滋》,到金融崩潰和英國脫歐的動盪,巴伯站在前排看到這一切。他將英國《金融時報》改造成數位媒體,並擴展了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力。讀來令人振奮。——哈羅德.埃文斯爵士(Sir Harold Evans),《星期日泰晤士報》前主編
關鍵十五年的真正內幕——來自目睹一切的編輯。
——米莎.海珊(Mishal Husain),BBC廣播四台Today節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