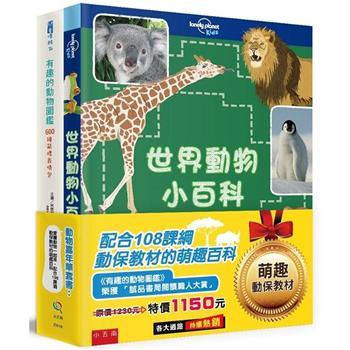兩岸知名學術大儒及思想家 龔鵬程 四海飲食之作
遍嚐臠肥膩脂與異卉奇珍
體會風土人情與歷史演變
華人為何釀不好葡萄酒?
蜀中辣風,其實起自清末時期?
天上龍肉吃不著,定要試試地下驢肉?
古代女人會常喝酒、喝得酒精中毒嗎?
「臥冰求鯉」原來是王祥的繼母想吃生魚片?
一方水土一方人,不能親近該地的飲食,就絕不能懂它。能把異鄉鮮奇美食挖掘出來,需要有發現者的眼光和好機緣,這是一名優秀或稱職的旅人所應具備的條件。
往往就是那令遠方來的人無法欣賞的食物
才最足以代表那個地方的特色
飲食文化乃是文化發展的表徵。把各種不同的植物、肉類、調料,搭配在一塊,控制火候,爆炒得宜,還真是一門藝術,須求其君臣佐使、左右調劑。古人比喻治國之道,輒以宰庖為說,良非無故。
歐洲文學獎得主諾特博姆在西班牙旅行時偶然聽見服務生提起「蜥蜴」一詞,立刻警覺了起來,連忙向老闆打聽。獲知他們果然有賣蜥蜴餐,馬上要了一客來品嘗。
這尾蜥蜴,伴在一盤碎番茄中,配上百里香、迷迭香,正是西班牙的氣質。諾特博姆形容西班牙是「混亂的、粗野的、自我中心的、殘酷的。行過之處,永無止境的驚歎」。
相對來說,武術界的朋友,演武論技,固擅勝場,但文史非其所長,又常不曉學術規範,故其講古論藝,時不免河漢其談。更常因門派所囿、見聞所限,知識不廣。
這種氣質,鬥牛,或西班牙舞孃的舞蹈,或許都足以顯示,但都不夠;只有那一股迷迭香混雜著蜥蜴肉味刺竄入腦時,你才能懂得什麼叫作西班牙。無怪乎他要刻意記述這一餐了。
我們每想起一個地方,總會想起那裡某一種或某幾種吃食,想起某一餐,道理即是如此。食物的氣味,用餐時的氣氛,店家的風情,一同用餐者的神態、聲語,整體激擾著我們的神經,在腦子裡浮漾出一幅特異的地圖,標示著那一個無可替代的地點。
史上第一為烤羊而丟官的國學大師龔鵬程,大談吃之典故:原來四川傳統菜色並非無辣不歡;「切仔麵」其實是南北文化差異造成;擅用米穀釀酒法的中國總是釀不好葡萄酒;「臥冰求鯉」是因為王祥的繼母想吃生魚片;古代女人其實慣常飲酒和聚會;吃不到天上龍肉,至少要吃地下驢肉;為什麼孟子總愛用飲食做論述;楚辭記載以超級饗宴招魂;古詩居然提及一兔三吃。吃之學問實在其妙無窮。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吟遊問俠之食趣:飲饌叢談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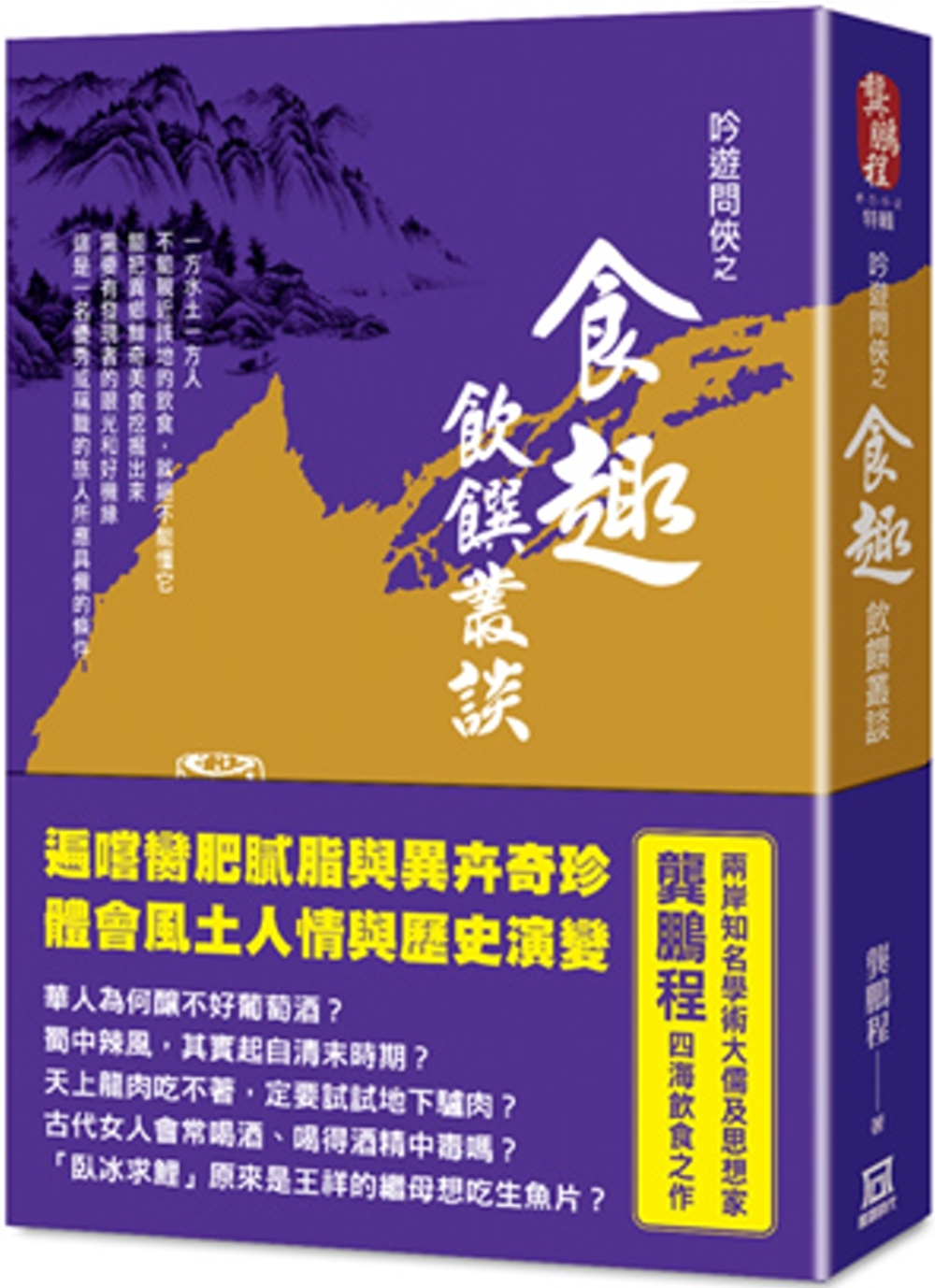 |
吟遊問俠之食趣:飲饌叢談 作者:龔鵬程 出版社:風雲時代 出版日期:2023-02-0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16頁 / 15 x 21 x 2.08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0 |
華文文學研究 |
$ 395 |
華文文學研究 |
$ 450 |
飲食總論 |
$ 450 |
社會人文 |
$ 500 |
華文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吟遊問俠之食趣:飲饌叢談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龔鵬程
1956年生於台北,為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歷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等職。曾獲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傑出研究獎等。2004年起,任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等職,現為山東大學講席教授、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曾任中華武俠文學學會理事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歷史文學學會理事長等職。旅行講學兩岸三地,博涉九流,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著有《文人階層史論》、《經典與生活》、《唐代思潮》、《龔鵬程四十自述》、《文學與美學》、《知識與愛情》、《中國文學批評史論》等百八十部作品。
龔鵬程
1956年生於台北,為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歷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等職。曾獲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傑出研究獎等。2004年起,任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等職,現為山東大學講席教授、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曾任中華武俠文學學會理事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歷史文學學會理事長等職。旅行講學兩岸三地,博涉九流,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著有《文人階層史論》、《經典與生活》、《唐代思潮》、《龔鵬程四十自述》、《文學與美學》、《知識與愛情》、《中國文學批評史論》等百八十部作品。
目錄
編 序 人文的感應,友情的見證 陳曉林
自 序 定光古佛今又來 龔鵬程
旅行者的美德
巴生宿緣
川中滋味長
特重飲食的文明
文化交流的飲食
土耳其旅遊答客問
土耳其咖啡
道士酒
南洋‧山東‧葡萄酒
啤酒花的歲月
四川壓酒
雨雪霏霏
飲酒好色對
酒鄉之歌
酒禮新篇
喝酒的女人
德亮找茶
密碼一九八九
輝煌的北京?
老店的歷史
吃 典
且食羊
杭城食事
廣結善緣
十二生肖
以人為藥
附說以人為藥
論《食穢文化》
鹽文化
鹽的城池
禁食不禁食
殺生不殺生
聖俗穢淨
儒家的飲饌政治學
飲食、男女以通大道
貓狗論
狗與藏羚羊
觀念的偏執
飲饌之道
知 味
養 生
從食譜到散文
飲饌的文學社會學:從《文選》到梁實秋
吃垮中國?
閒話西餐
西餐雜說
飲食錄
自 序 定光古佛今又來 龔鵬程
旅行者的美德
巴生宿緣
川中滋味長
特重飲食的文明
文化交流的飲食
土耳其旅遊答客問
土耳其咖啡
道士酒
南洋‧山東‧葡萄酒
啤酒花的歲月
四川壓酒
雨雪霏霏
飲酒好色對
酒鄉之歌
酒禮新篇
喝酒的女人
德亮找茶
密碼一九八九
輝煌的北京?
老店的歷史
吃 典
且食羊
杭城食事
廣結善緣
十二生肖
以人為藥
附說以人為藥
論《食穢文化》
鹽文化
鹽的城池
禁食不禁食
殺生不殺生
聖俗穢淨
儒家的飲饌政治學
飲食、男女以通大道
貓狗論
狗與藏羚羊
觀念的偏執
飲饌之道
知 味
養 生
從食譜到散文
飲饌的文學社會學:從《文選》到梁實秋
吃垮中國?
閒話西餐
西餐雜說
飲食錄
序
自序
定光古佛今又來
龔鵬程
一、羊頭燉之已爛,挑燈說劍未央
晚清楊守敬以書名天下,友朋來往,筆札亦多妙趣。如梁鼎芬一短簡云:「燉羊頭已爛,不攜小真書手卷來,不得吃也。」詩人周棄子先生外祖母就是楊氏女兒,故後來看見此柬,不禁感歎「承平文宴,脯醊風流。神往前賢,心傷世變,不止妙墨劫灰之可為太息也!」
周棄公之嘆,當然與他們那一輩師友棄其鄉里、流散入台有關。但當年楊守敬、梁鼎芬等人的詩酒文墨之樂,台灣未必不能繼承。棄公自己在東坡生日時與友人劇談,便曾說:「清班台省夙迴翔,載酒江湖亦敢狂。直以友朋為性命,豈因才略掩文章……」。
當時他們一批輾轉入台的學仕文人,迴翔於故土和島嶼,歌哭於清班和江湖,正如此詩所云。大難之後,友朋尤親。我和陳曉林兄即在此時,因緣際會,輒與作歡,羊頭燉之已爛,挑燈說劍未央。
後來少年子弟江湖老,前輩師友漸漸消散,幸而陪著我們的共樂同袍卻始終不曾離去。
從前孫悟空怕闖禍,連累了師父,所以起誓說「絕不敢提起師父,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希臘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說自己不是誰的學生,辯證法皆出於自己的探討。
我非老孫,豈敢說此違心之語?我的本領,都憑師友。早期的,是前文所述周棄公一類人,後來仰賴同行同業則愈來愈多。相信許多人也是如此。
但道遠而歧、術用而紛,靠知識專業或職業維繫下來的友誼,往往經不起消磨,因為人事變遷,知識專業和職業也隨之屢變。所以我還需要另一群非親、非故、非同鄉、非同行、非同業、也無任何利益交換的朋友。
不必噓寒問暖,不必引經據典,也不用家長里短,更不須以國破家亡、新愁舊怨來藉口。我鴻飛冥冥,他們也天南地北,擔簦異路,事業各別,彼此不能長聚。但想到王維形容古遊俠:「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或李白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時,我馬上就會遇到他們了。
我是靠曉林兄跟他們聚起來的,非儒非墨,蓋近於俠乎?飲於山巔水涯,必以缺一人為憾。
今年我將返台,曉林說疫後久不見矣,應大集慶祝以補憾。乃輯編了我論儒道佛三教、論遊、論俠、論武、論飲食,以及在大陸十年間的遊記,合為十本,諸友贊助,共為紀念。
二、定光古佛今又來
我的感動是不消說的。但在此刻,正猶豫著,欲說感謝之辭還是休說為好呢,忽然想起從前恰好日本有位和尚就叫一休。
一休出身本也高貴,父親是後小松天皇,母親是藤原照子。可惜父母不合,照子逃出宮廷,生下了他。所以一休之名,意思大約同於「也罷」。
也罷之人,行止不免狂亂,狎妓縱酒,無所不為。「夜夜鴛鴦禪榻被,風流私語一身閑」「美人雲雨愛河深,樓子老禪樓上吟」。本應為名教所訶,不料竟暴得大名。晚年自稱「忍辱仙人常不經,菩提果滿已圓成。拔無因果任孤陋,一個盲人引眾盲」,也不知是自詡還是自傷。
我曾看過一休自己寫的「一個盲人引眾盲」書法條幅,拍賣價格三十八萬八。
其實此語是用典,早期丹霞天然、大慧宗杲等禪師都說過這等話。
大慧宗杲尤其是臨濟宗楊岐派高僧,與富季申,張九成等友善,積極參政。秦檜恐其議己,竟褫奪他僧籍,刺配衡陽。不料入城前夕「太守及市民皆夢定光佛入城,明日杲至」。所以百姓赴從者萬餘人,都說是定光佛降世。
一休寫這句詩,雖謙稱自己只是一盲導引眾盲,但心中不會沒有大慧宗杲這段故事,也不會不知道佛教自家的忍辱仙人故事。
我們學者文人,大抵皆如一休,乃時代之棄嬰。或苟全性命於亂世、或詩酒婦人以自晦、或議政干時以賈禍、或膺淡泊寧靜之空名、或蒙盲以導盲之譏誚,誰能僥倖有定光古佛之譽望哉?
詩曰:我亦定光佛,曾燃七寶燈,煮字三千萬,塊然土木僧。感激唯舊友,冰塍曾偕登,又觀雲中道,稽首謝鯤鵬。
三、莽蒼歲月,大海洄瀾
回首當年,我還年輕時,時代倒真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曾經講得豪氣干雲:「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
大概那時民國肇建,少年中國遂給了少年無窮底氣,故歌聲嘹亮若此。隨後毛澤東、方東美、王光祈都參加了的「少年中國學會」顯然即繼其風而起者,五四運動期間的北大「新青年」也是,但少年很快就成青年了。
青年都做了些什麼?壯烈者,如十萬青年十萬軍;陷於盲動者,如學潮不斷,趕老師、趕校長;到台灣以後,馮滬祥雖然還在寫著《青年與國運》,青年其實已對國運無從措手。
不只台灣如此。年輕的美國,才剛剛以年輕氣盛自誇,看不起老大腐朽的中國和英國;卻很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青年就成了垮掉的一代(或稱疲憊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然後是性解放、搖滾樂、衣衫襤褸、反戰和躺平。青年成了國家的對立面。
台灣不是美國,青年的氣焰張揚不起來,學潮都壓住了,時代也不一樣。一九四九年大批中壯老年學者來台,「新青年」只成為期待,老專家和中壯學者文化人才是主力。
張其昀、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在辦學;臺靜農、魏建功、洪炎秋、何欣等在台大、國語日報社;林尹、魯實先在師大;故宮、中研院、中央圖書館也是大老雲集。出版界,如王雲五的商務、劉國瑞的學生書局、劉紹唐的《傳記文學》等等更是。台灣及港澳新馬緬越各地不願附從紅旗之青年,乃亦因緣際會,群聚於此。
青年得前輩調護引導,甚或可以詩酒相從,無疑是幸運的。那些年,雖然李敖一直悻悻然喊著老人應該交棒,可實際上老輩愛才、獎掖青年,佳話頗多。
那時,美國流行大師為青年開設大一通識課程,台灣也頗從風。像我大一參加國學營,方東美先生居然親臨授課,大氣磅礡、渾淪浩瀚,令人難忘。
台北以外地區,隱士素儒,教化一方者也不罕見。友人王財貴,於師專畢業後去鄉間實習,聽聞當地有掌牧民先生,常指導鄉人讀書。財貴好奇,也跟著去看看。掌先生一問才知,除教科書外他並沒讀過任何古籍,於是才教他讀經之法。如今財貴在大陸推動兒童讀經,成果斐然,皆掌先生之賜也。
我最近在花蓮,地方人士也常與我談到當年老儒駱香林成立說頑精舍、奇萊吟社,編《洄瀾同人集》的事。花蓮青年受其裁成鼓舞者甚多。近年風氣澆薄,一說起五六十年代,好似白色恐怖之外,這些激揚文運、少長咸集的事都不值一提了。我對此,是深不以為然的。
四、出入三教,以實濟虛
當然,論斷老蔣在台功過,非我小文所能為。但相對於大陸之文化大革命、破四舊,老蔣主推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無論如何,都是裨益千秋的大事,我自己亦深獲其益。
首先是潘重規、周何先生等所編語文課本,加上以四書為主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對於國人之文化教養,植基甚厚。大陸至今引進、仿擬不斷,便足以見其價值。
我父立逑公,江西吉安(古名廬陵)人。鄉邦素以「文章節義」自許,崇拜歐陽修、文天祥。明正德年間,廬陵知縣王陽明又在當地青原山講學,嘉靖年間且在六祖惠能弟子行思的道場(淨居寺)旁創青原會館,並於附近安福、泰和、永豐、吉水、新建、南城等地廣設書院。一時人才稱勝,故黃宗羲說:「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
我生長雖在台灣,但廬陵父老很早就教會我歐陽文章、文山節義、陽明心學了。入學後,對於國語文課程植本立基之教自然也就少習若天成。
學校對我很滿意,要不就勸我跳級,不必浪費時間;要不就鼓勵我自學,免得在校淘氣;要不則留著我,派去各種國語文競賽(作文、閱讀、朗誦、演講、書法)得獎。我則樂於以此為保護傘,可以雖在校而嬉遊浪蕩為俠客行。老師輩憫其憨直,看了也只是笑笑。
其實那時已漸入魔道,不只是行為上練武、鬥狠、打架、爭地盤,更是從台灣武術秘笈漸漸搜羅到了香港《當代武壇》之類;從神打,進而講求神術神方如《秘術一千種》《萬法歸宗》之類江湖術士的奇門道法,續命、起魂、入陰、養鬼、圓光、降神、修禪等等,差點還要去台北南懷瑾的十方叢林。
我家世傳之學,本來瞧不起這類江湖道術。伯父乾升公出身國立中正大學,可算新派知識份子。離開大陸時,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大真人在韶關相遇,一時莫逆,竟爾結拜入台。天師後來主持政府冊封之嗣漢天師府,伯父翊贊甚力,而道法本諸易學易圖,從不講怪力亂神。即使後來以風水揚名,所用亦不過江西楊救貧、賴布衣之法。堂兄龔群後來輔佐天師多年,以符法精湛見稱,但大抵也是如此。
所以這時隱然覺得不妙,武人李小龍又猝死了,我則考上了大學,改弦更張,正當其時。乃下定決心由正道上去探微掘隱,闡發儒、道、佛的奧秘。
除了努力聽講,還要氾濫群書,充分利用淡江大學舊藏。其次是擔心遊騎散漫無歸,每年都要自訂功課,寫成稿本。大一是註解《莊子》,大二寫《謝宣城詩研究》,大三是《古學微論》,總說儒、道、名、法、墨、與陰陽,大四又寫了《近代詩家與詩派》。一年義理考據、一年詞章,交替而行。
五十年來,總是如此,縱橫求索,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藝術史、社會史,什麼論題都要研究。每年不少於七十萬字,不徐不急,盈科而後進。
思想當然逐年遞有進境,範圍也愈來愈為廣袤,精勤博大,學界少有其比。古人常惋惜才子多半沒學問,因為揮灑其才即足以驚世了。享此才名,就懶得在書卷裡打熬氣力。這是才子的虛名和危險,所以我要下滿堅實工夫,不敢懈怠。
五、遊者不拘墟、百家不通竅
「我用我自己的流浪,換一個在你心裡放馬的地方,像那遊牧的人們一樣,把寂寞憂傷都奔到天上。」
讀書人何嘗不如此?他們雖只在書齋裡坐破蒲團,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可總是自以為在書中流浪,尋找適合墾牧的地方。而學者思想流浪之處,也希望能成讀者心裡放馬馳騁的草原。
可是,流浪的歌者並不曉得學者所謂浪跡、放馬只是飾詞。守著地盤的專家哪需博學?田連阡陌,就耕不過來了,更何須草原連天?糊口學林,亦不能如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或如老子之為博大真人,只須簡單扼要、旗幟鮮明,便於品牌行銷即可。
此等專家,莊子就不滿了:「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我當年既註莊子,自然就不肯再做一曲之士,想要博通載籍,「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內聖外王,能到不能到,不曉得,但立志當然如此。
我如此博、大、高、遠,迥異於一般學人,源頭雖皆本於孔子;入機,也就是方法和方法論卻無疑來自莊子。我自稱能「以逍遙遊為養生主」,當然也是從莊子那兒學來。
無論莊子孔子,所說道術當然沒能包括後世佛教道教,但論析判查他們的方法,我覺得可與研究古代道術一以貫之,也要通、博、美、備,不受某宗某派某時代之限。像道教,我傳承的是正一,但全真、金丹南北東西中也都講,辦「中華道教學院」時,於符籙、練養、文獻、科儀等更沒少傳授。佛教,我生長台中市,最盛的是李炳南居士的蓮社,但我沒參加,研究佛教仍從般若學六家七宗開始,空有雙輪,加上唯識和禪宗,原原本本。
後來我把這些三教論衡的文章稱為新論、新思、新解。是因為「三教講論」形成制度,是在唐高祖時期。每年祭孔後,邀請儒學祭酒、道教大法師、佛教大和尚一齊商兌義理。可是此等論辯,成果有限,甚至增添了誤解和火氣,原因在於沒一個人真能同時懂三教,所以爭來辯去,不免出主入奴、雞同鴨講,唯我乃期一洗舊觀,再開新局。
換言之,傳統整齊貫通了,自然就能脈絡井井,洞明諸家聚訟之癥結,並打開新思想的空間。
六、遊居四野,以義合天
想這樣,不只須要搏極群書,也得遊半天下(這次特輯中《時光倒影》、《龍行於野》、《遊必有方》即是我一部分遊記)。
因爲學與遊不是一般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分列關係。《論語》第一句話「學而時習之」就強調學本身就該時時練習熟習。朱子解習字為「鳥數飛也」。可見學本來就有實踐性,人不斷學,猶如鳥不斷飛。《莊子.逍遙遊》開頭大鵬小鳥那一大段,即是從《論語》這兒化出。
遊即是學,學在遊中,故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就是消遙遊,學與遊是二而一的。學,依文獻、耳目見聞和思慮省查;遊就加上了貼地的人類學、鄉土志工夫,以及遊屐中偶得的機緣。
機緣屬於天,不可能以計劃、調查得之,而要靠我的性氣、人緣,「以人合天」庶幾得之。
所謂性氣、人緣等說不清楚的條件,古人常統稱為俠氣。俠,很難從階級屬性、行為類型或是非善惡去辨認,但其共同點是「挾」,其人皆有俠氣,能聚眾。聚眾當然也可憑權、錢、勢,但涉及俠和遊,卻還有個「義」的性質需要考量。
義是什麼?我有次說自己寫書,有點俠義心腸。古詩《獨漉篇》云: 「雄劍掛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在我看,中國文化現今就彷彿這柄原是神兵利器,可以斬犀斷象的寶劍,無端遭了冷落,瑟縮在牆角裡生苔長蘚。美人落難、明珠蒙塵,皆是世上大不堪之事,我遂深懷出而搭救之心。
這不就是義嗎?見義勇為;義不帝秦;義憤填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說的都是這個。
而這種義,有美國羅爾斯《正義論》或我國一般政治社會學者如陳喬見《義的譜系:中國古代的正義與公共傳統》之類所不能含括者,即是俠的精神。
俠有不軌於正義者,但正義不彰,俠者恥之,俠又是人間正義的持守者。凡事有可為、當為、不能不為,則俠客出焉,不出不足以為俠。學者的毛病,是書卷氣太重而人氣多半不足,所以要張天義、行俠道以振作之。這次特輯中《吟遊:遊的精神文化史論》、《大俠:俠的精神文化史論》、《武藝:俠的武術功法叢談》,即是例證。
七、集思,也集喜怒哀樂
我如此學、如此思、如此俠遊不已,當然成書數百種、交友無量數。此中是要有真正實踐工夫的,如人飲水。書要寫、酒要喝,一字一思,千折百轉,不是昏沉懵懂即可花開見佛。一人一緣,覯面相親,不是僅有「人類」、「人民」、「同胞」、「民主」等大詞就能歃血心傾。
歷年同學、同事,與我一同闖蕩社會,辦報、辦學、辦雜誌、辦活動之同懷友生,乃因此幾乎人人皆有可憶之處。
其中最特別的,當然是與這套書直接相關的陳曉林、吳安安、黃滈權、龔明湘、古凌、林鍾朝權、張正諸位。曉林與我,文字骨肉,俠情尤為我所敬重。擅張鐵網之珊瑚,收輯神州欲散之文心;心光無量,又能傳將盡未盡之燈。黑白有集,宗風不替。他和安安、滈權等時日相聚,輒常邀我,或竟與我同其沆瀣。如我遠去新疆特克斯辦周易大會武林大會,他們也鷹揚草原,隨至雪山;明湘號召於台灣東北角觀海嘗鮮,我等亦簇湧而聚……,實踐並體驗著我這特輯中《食趣:飲饌叢談》的趣味。此時,定光佛亦跳牆過來矣!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友道裹人,未嘗不能如詩。故我的學、思、俠、遊,朋友們也最能欣賞。現在大家一起玩玩,把它印出來,也為時代添些光彩罷!
壬寅虎兒年,龔鵬程寫於泰山、倫敦、花蓮旅次
定光古佛今又來
龔鵬程
一、羊頭燉之已爛,挑燈說劍未央
晚清楊守敬以書名天下,友朋來往,筆札亦多妙趣。如梁鼎芬一短簡云:「燉羊頭已爛,不攜小真書手卷來,不得吃也。」詩人周棄子先生外祖母就是楊氏女兒,故後來看見此柬,不禁感歎「承平文宴,脯醊風流。神往前賢,心傷世變,不止妙墨劫灰之可為太息也!」
周棄公之嘆,當然與他們那一輩師友棄其鄉里、流散入台有關。但當年楊守敬、梁鼎芬等人的詩酒文墨之樂,台灣未必不能繼承。棄公自己在東坡生日時與友人劇談,便曾說:「清班台省夙迴翔,載酒江湖亦敢狂。直以友朋為性命,豈因才略掩文章……」。
當時他們一批輾轉入台的學仕文人,迴翔於故土和島嶼,歌哭於清班和江湖,正如此詩所云。大難之後,友朋尤親。我和陳曉林兄即在此時,因緣際會,輒與作歡,羊頭燉之已爛,挑燈說劍未央。
後來少年子弟江湖老,前輩師友漸漸消散,幸而陪著我們的共樂同袍卻始終不曾離去。
從前孫悟空怕闖禍,連累了師父,所以起誓說「絕不敢提起師父,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希臘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說自己不是誰的學生,辯證法皆出於自己的探討。
我非老孫,豈敢說此違心之語?我的本領,都憑師友。早期的,是前文所述周棄公一類人,後來仰賴同行同業則愈來愈多。相信許多人也是如此。
但道遠而歧、術用而紛,靠知識專業或職業維繫下來的友誼,往往經不起消磨,因為人事變遷,知識專業和職業也隨之屢變。所以我還需要另一群非親、非故、非同鄉、非同行、非同業、也無任何利益交換的朋友。
不必噓寒問暖,不必引經據典,也不用家長里短,更不須以國破家亡、新愁舊怨來藉口。我鴻飛冥冥,他們也天南地北,擔簦異路,事業各別,彼此不能長聚。但想到王維形容古遊俠:「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或李白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時,我馬上就會遇到他們了。
我是靠曉林兄跟他們聚起來的,非儒非墨,蓋近於俠乎?飲於山巔水涯,必以缺一人為憾。
今年我將返台,曉林說疫後久不見矣,應大集慶祝以補憾。乃輯編了我論儒道佛三教、論遊、論俠、論武、論飲食,以及在大陸十年間的遊記,合為十本,諸友贊助,共為紀念。
二、定光古佛今又來
我的感動是不消說的。但在此刻,正猶豫著,欲說感謝之辭還是休說為好呢,忽然想起從前恰好日本有位和尚就叫一休。
一休出身本也高貴,父親是後小松天皇,母親是藤原照子。可惜父母不合,照子逃出宮廷,生下了他。所以一休之名,意思大約同於「也罷」。
也罷之人,行止不免狂亂,狎妓縱酒,無所不為。「夜夜鴛鴦禪榻被,風流私語一身閑」「美人雲雨愛河深,樓子老禪樓上吟」。本應為名教所訶,不料竟暴得大名。晚年自稱「忍辱仙人常不經,菩提果滿已圓成。拔無因果任孤陋,一個盲人引眾盲」,也不知是自詡還是自傷。
我曾看過一休自己寫的「一個盲人引眾盲」書法條幅,拍賣價格三十八萬八。
其實此語是用典,早期丹霞天然、大慧宗杲等禪師都說過這等話。
大慧宗杲尤其是臨濟宗楊岐派高僧,與富季申,張九成等友善,積極參政。秦檜恐其議己,竟褫奪他僧籍,刺配衡陽。不料入城前夕「太守及市民皆夢定光佛入城,明日杲至」。所以百姓赴從者萬餘人,都說是定光佛降世。
一休寫這句詩,雖謙稱自己只是一盲導引眾盲,但心中不會沒有大慧宗杲這段故事,也不會不知道佛教自家的忍辱仙人故事。
我們學者文人,大抵皆如一休,乃時代之棄嬰。或苟全性命於亂世、或詩酒婦人以自晦、或議政干時以賈禍、或膺淡泊寧靜之空名、或蒙盲以導盲之譏誚,誰能僥倖有定光古佛之譽望哉?
詩曰:我亦定光佛,曾燃七寶燈,煮字三千萬,塊然土木僧。感激唯舊友,冰塍曾偕登,又觀雲中道,稽首謝鯤鵬。
三、莽蒼歲月,大海洄瀾
回首當年,我還年輕時,時代倒真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曾經講得豪氣干雲:「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
大概那時民國肇建,少年中國遂給了少年無窮底氣,故歌聲嘹亮若此。隨後毛澤東、方東美、王光祈都參加了的「少年中國學會」顯然即繼其風而起者,五四運動期間的北大「新青年」也是,但少年很快就成青年了。
青年都做了些什麼?壯烈者,如十萬青年十萬軍;陷於盲動者,如學潮不斷,趕老師、趕校長;到台灣以後,馮滬祥雖然還在寫著《青年與國運》,青年其實已對國運無從措手。
不只台灣如此。年輕的美國,才剛剛以年輕氣盛自誇,看不起老大腐朽的中國和英國;卻很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青年就成了垮掉的一代(或稱疲憊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然後是性解放、搖滾樂、衣衫襤褸、反戰和躺平。青年成了國家的對立面。
台灣不是美國,青年的氣焰張揚不起來,學潮都壓住了,時代也不一樣。一九四九年大批中壯老年學者來台,「新青年」只成為期待,老專家和中壯學者文化人才是主力。
張其昀、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在辦學;臺靜農、魏建功、洪炎秋、何欣等在台大、國語日報社;林尹、魯實先在師大;故宮、中研院、中央圖書館也是大老雲集。出版界,如王雲五的商務、劉國瑞的學生書局、劉紹唐的《傳記文學》等等更是。台灣及港澳新馬緬越各地不願附從紅旗之青年,乃亦因緣際會,群聚於此。
青年得前輩調護引導,甚或可以詩酒相從,無疑是幸運的。那些年,雖然李敖一直悻悻然喊著老人應該交棒,可實際上老輩愛才、獎掖青年,佳話頗多。
那時,美國流行大師為青年開設大一通識課程,台灣也頗從風。像我大一參加國學營,方東美先生居然親臨授課,大氣磅礡、渾淪浩瀚,令人難忘。
台北以外地區,隱士素儒,教化一方者也不罕見。友人王財貴,於師專畢業後去鄉間實習,聽聞當地有掌牧民先生,常指導鄉人讀書。財貴好奇,也跟著去看看。掌先生一問才知,除教科書外他並沒讀過任何古籍,於是才教他讀經之法。如今財貴在大陸推動兒童讀經,成果斐然,皆掌先生之賜也。
我最近在花蓮,地方人士也常與我談到當年老儒駱香林成立說頑精舍、奇萊吟社,編《洄瀾同人集》的事。花蓮青年受其裁成鼓舞者甚多。近年風氣澆薄,一說起五六十年代,好似白色恐怖之外,這些激揚文運、少長咸集的事都不值一提了。我對此,是深不以為然的。
四、出入三教,以實濟虛
當然,論斷老蔣在台功過,非我小文所能為。但相對於大陸之文化大革命、破四舊,老蔣主推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無論如何,都是裨益千秋的大事,我自己亦深獲其益。
首先是潘重規、周何先生等所編語文課本,加上以四書為主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對於國人之文化教養,植基甚厚。大陸至今引進、仿擬不斷,便足以見其價值。
我父立逑公,江西吉安(古名廬陵)人。鄉邦素以「文章節義」自許,崇拜歐陽修、文天祥。明正德年間,廬陵知縣王陽明又在當地青原山講學,嘉靖年間且在六祖惠能弟子行思的道場(淨居寺)旁創青原會館,並於附近安福、泰和、永豐、吉水、新建、南城等地廣設書院。一時人才稱勝,故黃宗羲說:「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
我生長雖在台灣,但廬陵父老很早就教會我歐陽文章、文山節義、陽明心學了。入學後,對於國語文課程植本立基之教自然也就少習若天成。
學校對我很滿意,要不就勸我跳級,不必浪費時間;要不就鼓勵我自學,免得在校淘氣;要不則留著我,派去各種國語文競賽(作文、閱讀、朗誦、演講、書法)得獎。我則樂於以此為保護傘,可以雖在校而嬉遊浪蕩為俠客行。老師輩憫其憨直,看了也只是笑笑。
其實那時已漸入魔道,不只是行為上練武、鬥狠、打架、爭地盤,更是從台灣武術秘笈漸漸搜羅到了香港《當代武壇》之類;從神打,進而講求神術神方如《秘術一千種》《萬法歸宗》之類江湖術士的奇門道法,續命、起魂、入陰、養鬼、圓光、降神、修禪等等,差點還要去台北南懷瑾的十方叢林。
我家世傳之學,本來瞧不起這類江湖道術。伯父乾升公出身國立中正大學,可算新派知識份子。離開大陸時,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大真人在韶關相遇,一時莫逆,竟爾結拜入台。天師後來主持政府冊封之嗣漢天師府,伯父翊贊甚力,而道法本諸易學易圖,從不講怪力亂神。即使後來以風水揚名,所用亦不過江西楊救貧、賴布衣之法。堂兄龔群後來輔佐天師多年,以符法精湛見稱,但大抵也是如此。
所以這時隱然覺得不妙,武人李小龍又猝死了,我則考上了大學,改弦更張,正當其時。乃下定決心由正道上去探微掘隱,闡發儒、道、佛的奧秘。
除了努力聽講,還要氾濫群書,充分利用淡江大學舊藏。其次是擔心遊騎散漫無歸,每年都要自訂功課,寫成稿本。大一是註解《莊子》,大二寫《謝宣城詩研究》,大三是《古學微論》,總說儒、道、名、法、墨、與陰陽,大四又寫了《近代詩家與詩派》。一年義理考據、一年詞章,交替而行。
五十年來,總是如此,縱橫求索,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藝術史、社會史,什麼論題都要研究。每年不少於七十萬字,不徐不急,盈科而後進。
思想當然逐年遞有進境,範圍也愈來愈為廣袤,精勤博大,學界少有其比。古人常惋惜才子多半沒學問,因為揮灑其才即足以驚世了。享此才名,就懶得在書卷裡打熬氣力。這是才子的虛名和危險,所以我要下滿堅實工夫,不敢懈怠。
五、遊者不拘墟、百家不通竅
「我用我自己的流浪,換一個在你心裡放馬的地方,像那遊牧的人們一樣,把寂寞憂傷都奔到天上。」
讀書人何嘗不如此?他們雖只在書齋裡坐破蒲團,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可總是自以為在書中流浪,尋找適合墾牧的地方。而學者思想流浪之處,也希望能成讀者心裡放馬馳騁的草原。
可是,流浪的歌者並不曉得學者所謂浪跡、放馬只是飾詞。守著地盤的專家哪需博學?田連阡陌,就耕不過來了,更何須草原連天?糊口學林,亦不能如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或如老子之為博大真人,只須簡單扼要、旗幟鮮明,便於品牌行銷即可。
此等專家,莊子就不滿了:「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我當年既註莊子,自然就不肯再做一曲之士,想要博通載籍,「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內聖外王,能到不能到,不曉得,但立志當然如此。
我如此博、大、高、遠,迥異於一般學人,源頭雖皆本於孔子;入機,也就是方法和方法論卻無疑來自莊子。我自稱能「以逍遙遊為養生主」,當然也是從莊子那兒學來。
無論莊子孔子,所說道術當然沒能包括後世佛教道教,但論析判查他們的方法,我覺得可與研究古代道術一以貫之,也要通、博、美、備,不受某宗某派某時代之限。像道教,我傳承的是正一,但全真、金丹南北東西中也都講,辦「中華道教學院」時,於符籙、練養、文獻、科儀等更沒少傳授。佛教,我生長台中市,最盛的是李炳南居士的蓮社,但我沒參加,研究佛教仍從般若學六家七宗開始,空有雙輪,加上唯識和禪宗,原原本本。
後來我把這些三教論衡的文章稱為新論、新思、新解。是因為「三教講論」形成制度,是在唐高祖時期。每年祭孔後,邀請儒學祭酒、道教大法師、佛教大和尚一齊商兌義理。可是此等論辯,成果有限,甚至增添了誤解和火氣,原因在於沒一個人真能同時懂三教,所以爭來辯去,不免出主入奴、雞同鴨講,唯我乃期一洗舊觀,再開新局。
換言之,傳統整齊貫通了,自然就能脈絡井井,洞明諸家聚訟之癥結,並打開新思想的空間。
六、遊居四野,以義合天
想這樣,不只須要搏極群書,也得遊半天下(這次特輯中《時光倒影》、《龍行於野》、《遊必有方》即是我一部分遊記)。
因爲學與遊不是一般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分列關係。《論語》第一句話「學而時習之」就強調學本身就該時時練習熟習。朱子解習字為「鳥數飛也」。可見學本來就有實踐性,人不斷學,猶如鳥不斷飛。《莊子.逍遙遊》開頭大鵬小鳥那一大段,即是從《論語》這兒化出。
遊即是學,學在遊中,故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就是消遙遊,學與遊是二而一的。學,依文獻、耳目見聞和思慮省查;遊就加上了貼地的人類學、鄉土志工夫,以及遊屐中偶得的機緣。
機緣屬於天,不可能以計劃、調查得之,而要靠我的性氣、人緣,「以人合天」庶幾得之。
所謂性氣、人緣等說不清楚的條件,古人常統稱為俠氣。俠,很難從階級屬性、行為類型或是非善惡去辨認,但其共同點是「挾」,其人皆有俠氣,能聚眾。聚眾當然也可憑權、錢、勢,但涉及俠和遊,卻還有個「義」的性質需要考量。
義是什麼?我有次說自己寫書,有點俠義心腸。古詩《獨漉篇》云: 「雄劍掛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在我看,中國文化現今就彷彿這柄原是神兵利器,可以斬犀斷象的寶劍,無端遭了冷落,瑟縮在牆角裡生苔長蘚。美人落難、明珠蒙塵,皆是世上大不堪之事,我遂深懷出而搭救之心。
這不就是義嗎?見義勇為;義不帝秦;義憤填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說的都是這個。
而這種義,有美國羅爾斯《正義論》或我國一般政治社會學者如陳喬見《義的譜系:中國古代的正義與公共傳統》之類所不能含括者,即是俠的精神。
俠有不軌於正義者,但正義不彰,俠者恥之,俠又是人間正義的持守者。凡事有可為、當為、不能不為,則俠客出焉,不出不足以為俠。學者的毛病,是書卷氣太重而人氣多半不足,所以要張天義、行俠道以振作之。這次特輯中《吟遊:遊的精神文化史論》、《大俠:俠的精神文化史論》、《武藝:俠的武術功法叢談》,即是例證。
七、集思,也集喜怒哀樂
我如此學、如此思、如此俠遊不已,當然成書數百種、交友無量數。此中是要有真正實踐工夫的,如人飲水。書要寫、酒要喝,一字一思,千折百轉,不是昏沉懵懂即可花開見佛。一人一緣,覯面相親,不是僅有「人類」、「人民」、「同胞」、「民主」等大詞就能歃血心傾。
歷年同學、同事,與我一同闖蕩社會,辦報、辦學、辦雜誌、辦活動之同懷友生,乃因此幾乎人人皆有可憶之處。
其中最特別的,當然是與這套書直接相關的陳曉林、吳安安、黃滈權、龔明湘、古凌、林鍾朝權、張正諸位。曉林與我,文字骨肉,俠情尤為我所敬重。擅張鐵網之珊瑚,收輯神州欲散之文心;心光無量,又能傳將盡未盡之燈。黑白有集,宗風不替。他和安安、滈權等時日相聚,輒常邀我,或竟與我同其沆瀣。如我遠去新疆特克斯辦周易大會武林大會,他們也鷹揚草原,隨至雪山;明湘號召於台灣東北角觀海嘗鮮,我等亦簇湧而聚……,實踐並體驗著我這特輯中《食趣:飲饌叢談》的趣味。此時,定光佛亦跳牆過來矣!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友道裹人,未嘗不能如詩。故我的學、思、俠、遊,朋友們也最能欣賞。現在大家一起玩玩,把它印出來,也為時代添些光彩罷!
壬寅虎兒年,龔鵬程寫於泰山、倫敦、花蓮旅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