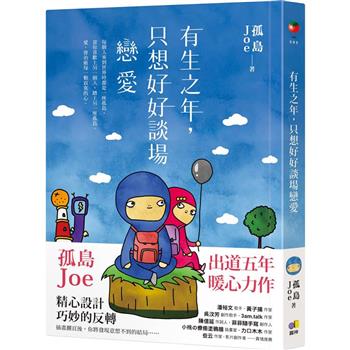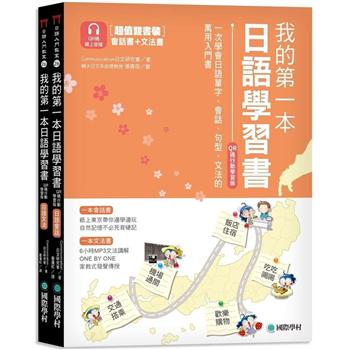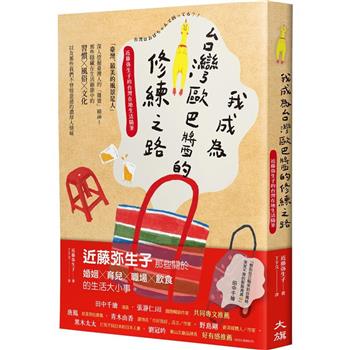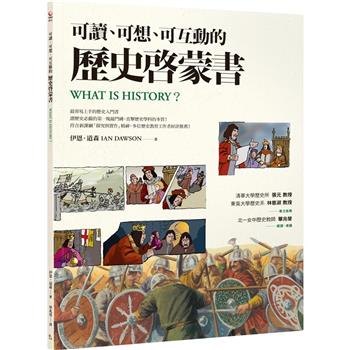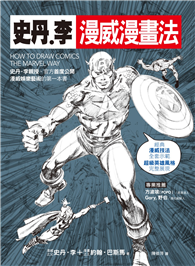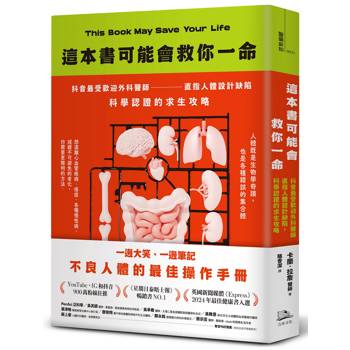圖書名稱: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
內容簡介
紐伯瑞文學獎金牌獎得主暢銷系列最新一集
亞馬遜網路書店五顆星最高評價!
笑翻美國一千五百萬個孩子,
歪歪小學再度精采回歸,師生們依舊人見人愛!
歪歪小學上方被末日烏雲所籠罩,校園生活變得更加驚險難料!
丹丹和基茲瓦特先生的臉被卡住了;
大家都怪烏雲害他們寫錯答案和遲到……
更倒楣的是,終極測驗要開始了!
不祥的烏雲就在頭頂上方,他們能否順利通過重重關卡?
現實世界很煩,但你可以選擇哈哈大笑!
【本書關鍵字】
路易斯.薩奇爾、校園生活、美國文學、荒誕故事、幽默、無稽美學
【本書資料】
無注音
適讀年齡:10歲以上
【本書特色】
1. 睽違多年,紐伯瑞文學獎金牌獎得主「歪歪小學」暢銷系列故事最新一集。
2. 角色們超現實又荒誕不經的不幸遭遇,同時也富含教育性質,讓師生們都愛不釋手,手不釋卷!
3. 顛覆一般校園故事,讓普通的孩子置於非凡的情境裡,以看似「荒謬」的敘事手法,激盪出「荒誕」本身的趣味性及深層意義!
4. 路易斯.薩奇爾特別以「末日」為故事背景,鼓勵讀者在不盡然美好的現實世界裡,積蓄正能量。
5. 由珠兒老師舉行的終極測驗,看見學生們各個淋漓發揮特長,潛移默化體會「天生我材必有用」。
名人推薦(按姓氏筆畫列名)
邢小萍/臺北市永安國小校長
吳在媖/兒童文學作家、99少年讀書會創始人
李志軒/臺南市仙草國小校長
杜明城/前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教授
林玫伶/前臺北市國語實小校長、兒童文學作家、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
曾品方/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臺灣閱讀協會秘書長
葛琦霞/悅讀學堂執行長
謝鴻文/兒童文學作家
各界熱烈迴響
打開《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這本書,你會發現每一則故事都是一個驚喜、一種期待、一股會心微笑的幽默感,躍然於紙上。整本書充滿了奇思妙想的校園故事,特別能貼近小讀者的內心世界,反映出充滿好奇心、正義感、不認輸的率真童趣。我很期待和所有的小讀者們,相遇在怪怪的歪歪小學裡,一起解開末日烏雲裡的所有祕密!
──曾品方/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臺灣閱讀協會秘書長
彷彿看見比利時畫家雷內.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那種超現實畫作被化為立體的故事呈現,乍看搞怪荒謬,但對孩子而言,最可貴的東西之一莫過於想像力,只有孩子的超現實想像,最能認同歪歪小學這個連時間都不合理的超現實學校,在那裡發生的一切情境,孩子最能開心歡呼感受與同理。
大人與其擔憂追問這樣的故事有沒有意義,不如先放下嚴肅檢驗的眼鏡,以及保守的意識,去思考莊子哲學中「無用之用」,當腦袋不被僵化規馴下,生命的活力與創造力由是而生,頭頂縱有烏雲,也會被活潑的元氣趕走,看見彩虹的美麗。或許這也是作者隱藏的教育意圖。
唯有如此寬闊的思維胸襟看待事物,也才能包容讚美像這集故事裡的凱文,長大後只想成為能彎曲迴紋針的人。如此微小的志願,在這故事裡也被祝福期待,這樣的寫作心意和觀點,實也翻轉了許多人對「意義」或言「價值」的界定了。
──謝鴻文/兒童文學作家
〈開場白〉裡提及,這本書是「歪歪小學」系列故事的第四集。這個系列的第一本書──《歪歪小學的荒誕故事》,是路易斯.薩奇爾在四十多年前寫的。所以,他建議我們「先讀其他三本,等過了四十年,再來讀這一本。或者,你現在就可以開始讀了」。無庸置疑,後者肯定是眾多書迷們的最佳選擇。
──美國《號角圖書雜誌》
路易斯.薩奇爾的喜劇性腳步,自從《歪歪小學的荒誕故事》出版以來,繼續大步向前邁進,而他並未錯失第四部作品的節拍──在本集故事中,為了向學生們展示「一百萬」的概念,珠兒老師和全班同學一起收集起一百萬片指甲;皮克爾醫生巧妙操縱催眠術,利用懸掛綠色石頭的金鍊子治療愛唱反調的凱西。
自從歪歪小學上方被末日烏雲所籠罩,校園生活變得更加驚險難料:丹丹和基茲瓦特先生的臉被卡住了;學生們以末日烏雲為藉口,想要逃避考試和遲到的處罰。然而,由於珠兒老師堅持舉行終極測驗,學生們的特長才得以淋漓發揮。
──美國《出版人週刊》
歡呼吧!十多年來,歪歪小學仍在上課,而珠兒老師位於三十層樓班級裡的孩子們也一點都沒變!這一回,他們超現實又荒誕不經的不幸遭遇,同樣具有奇特的教育性質。歪歪小學裡的師生們依然是十足的開心果,逗得我們哈哈大笑,像是虛構單字的拼寫課程,還有全班師生無比投入地收集一百萬枚指甲片。此外,一向苛薄的凱西自從穿過了那面神奇的鏡子後,竟奇蹟似地變得友善,而她也喜歡自己的改變;娣娣弄丟了家庭作業,牢不可破四人幫的友情卻在垃圾箱旁更加堅定;珠兒老師長期向學生們「威脅」的終極測驗,則為每個人帶來展現才能的機會。再加上許多冷笑話,還有讓整座歪歪小學雞飛狗跳的末日烏雲,更讓人回味無窮。最後,路易斯.薩奇爾以莫許小姐提供的彩虹燉菜作結,即興料理、美味多彩。
讓普通的孩子置於非凡的情境裡,依舊是輝煌成就和捧腹大笑的良方。
──美國《柯克斯書評》
導讀
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有什麼意義?
文/葛容均(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自第一部《歪歪小學的荒誕故事》(Sideways Stories from Wayside School,1978 )誕生,路易斯.薩奇爾於一九八九(《歪歪小學要倒了》)至一九九五(《歪歪小學來了一個小小陌生人》)年間持續發展關於「歪歪小學」的系列故事。睽違十五年,薩奇爾於二Ο二Ο年又發表了新作品,即《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Wayside School Beneath the Cloud of Doom) !「歪歪小學」又開學了,多令人期待!小學建築依舊是三十層樓高,一層樓一班級,不存在的第十九樓與神祕的地下室依然存在,就連莫許小姐也還在積極地研發新食譜。而這回,薩奇爾為歪歪小學捎來了一片「末日烏雲」!
就「學校故事(the school story)」此一文類而言,屬於當代的「歪歪小學」系列已可名列經典。愛丁堡學者M. O. Grenby在其Children’s Literature(Edinburgh:Edinburgh UP, 2014 )中,特別為「學校故事」撰寫一章節,追溯該文類於西方的發展歷史與沿革。根據M. O. Grenby的考察,百年來的「學校故事」不外乎環繞著師生與同儕關係,甚至是作為兒少「社會化歷程(socialization)」的重要橋梁,協助兒少在「順從(submission)」與「反抗(defance)」、「權威(authority)」與「自主(autonomy)」之間,習得一種平衡內在自我發展和建立與學校作為小型社會關係的舞臺。而薩奇爾在「歪歪小學」的系列書寫中,正靈活巧妙、揮灑自如地運作此種舞台,這部新作亦不例外。
閱讀過「歪歪小學」故事的大小讀者們或許並不會在意「歪歪小學」系列是否符應百年來「學校故事」之敘事傳統。「幽默」當然是「歪歪小學」系列故事所持有的特色,例如保羅就是忍不住要去拉扯萊思麗的辮子,薩奇爾將萊思麗的辮子賦予神奇的召喚聲音,使得保羅「不得不犯錯」。這即是薩奇爾於其官方網站上表明的,「歪歪小學」系列故事是他自身作為孩童的經驗,以及揣摩孩童心思的同理構想。而筆者所言,「歪歪小學」系列已可列名當代學校故事之經典,並不僅止於薩奇爾作品中的幽默。倘若只以「幽默」作為「歪歪小學」系列的特色,那便小瞧了薩奇爾的功力!「無稽美學」才當是「歪歪小學」系列的核心。「無稽美學」並非毫無意義的「無稽之談」,它旨在反思正規與傳統、顛覆制式化與僵化的邏輯,以看似「荒謬」的敘事手法,激盪出「荒誕」本身的趣味性及深層意義。
另一方面,有關於「末日」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於今已然層出不窮,這是當代人類對其未來的惴惴不安或深層恐懼。就連薩奇爾也為此部新作添增了一片「末日烏雲」,而這片籠罩著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或多或少都影響了孩童們,甚至是「史上最棒的校長」的心境。薩奇爾在其作家官網上言明,縱然他的「歪歪小學」系列帶有詼諧之趣,卻仍內含教育意義。新作中的〈有什麼意義?〉便是最佳例證。即便籠罩在末日烏雲之下,珠兒老師依舊堅持讓學生們勤加練習慣常的拼
寫單字(spelling),薩奇爾先是藉由麥隆同理並表態孩子們受影響的心境:
「末日烏雲變得一天比一天大!」麥隆大聲嚷道。「我們會不會拼寫單字有什麼關係?」
薩奇爾再透過珠兒老師的話語撫慰並激勵年輕學子:
「我了解你們很害怕,也很心煩。」珠兒老師說。「但是,放棄有什麼意義?我們可以乾坐著抱怨,也可以想辦法盡力而為,管他有沒有烏雲。」
薩奇爾讓珠兒老師繼續對孩子們勉勵道:
「總有一天,末日烏雲將會消失。」珠兒老師說。「世界也將變得更美好,甚至比烏雲之前更美更好。顏色變得更繽紛多彩,音樂更富於音樂性。哪怕是莫許小姐的食物吃起來也更可口。暴風雨越大,彩虹越是鮮豔。」
而薩奇爾在此章末了,由珍妮說出「希望(Hope) 」一詞,且讓珠兒老師堅定地「一手拿著蠟燭,另一隻手握著粉筆」,在黑板上為孩子們銘刻下「H—O—P—E」,這般情節絕非偶發奇想的敘事安排。相反的,薩奇爾敏銳地將當
代人可能揣懷的心境—孩童也不例外—以彷若呼應卡爾維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所期許的「輕盈(Lightness)」敘事手法,為當代大小讀者提供在「末日烏雲」之下,屬於歪歪小學的點點滴滴。
作者簡介
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
紐伯瑞文學獎金牌獎、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高中時因為沙林傑與馮內果的作品,開始對閱讀和寫作產生興趣。大學時主修經濟學,也在法律學校修過法律;曾做過清潔用品推銷員、毛衣倉庫員工、律師,最後決定成為一個專職的兒童書作家。大學時期曾經在小學工作,成了影響他一生的重要經驗。那所小學的學生也成了他「歪歪小學」系列裡的角色。在許多讀者心中,他是近年來「寫得最好笑」的兒童小說作家。主要作品有「歪歪小學」系列、《爛泥怪》、《豬城俱樂部》、《小步小步走》、《洞》等(以上皆由小魯文化出版)。
譯者簡介
趙永芬
畢業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及東海外文系,任教中國科技大學近三十年,目前專事翻譯。從小愛讀小說,長大以後愛上小說翻譯。譯有《天藍色的彼岸》、《大探險家》、《爛泥怪》、《小步小步走》、《洞》、《藍莓季節》、《神偷》、《銀劍》等(以上皆由小魯文化出版)。
繪者簡介
毛利
插畫家,一九八四年出生,十四歲隨家人移民至加拿大,大學時在加拿大安大略藝術設計大學(OCAD Univeristy)主修傳統繪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