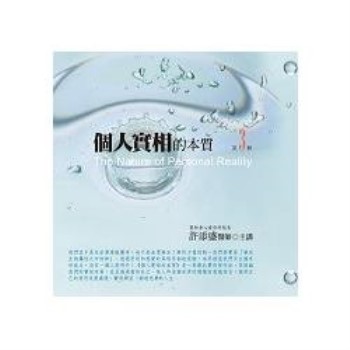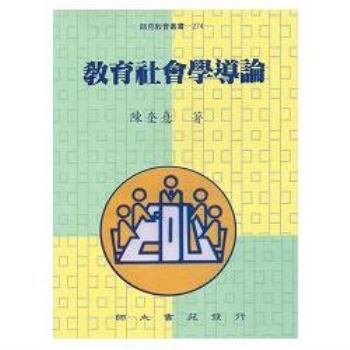這裡的每個人,都在借刀殺人
他們,也都是另一個人的棋子
「你說,如果烏雲有重量的話,那我們不就都被壓死了嗎?」
「賭場會越蓋越高,越蓋越多……無論如何都不會壓到我們頭上的。」
張儒行出生前父親因賭債輕生,富正義感、好打抱不平的他,夢想卻是進賭場工作。
2008年,澳門已成世界第一賭城,每年都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畢業生直接到賭場就職。張儒行就讀的聖德學校更是威尼斯人度假村檯面下的人才訓練所,校長盧高勤則是促成這合作的推手。
這是一所校長送學生去賭場、教務主任仲介援交的學校,校園黑幫「玉門幫」的前幫主楊思淮轉學過來,卻不是為了參與這門生意:開學第一天,他就找上了張儒行,直言張的父親其實是爭奪校長大位而遭盧高勤鬥死的。
張儒行只求順利畢業,對復仇毫無興趣。楊思淮一面熱心幫助張儒行岌岌可危的課業,另一面找上了不甘受制於教務主任的援交女孩珮雯,二人設局讓張儒行與女友黎莉一步步參與扳倒校長的大業。
四人的關係始終在單純的校園友情與複雜的鬥爭心計之間維持著奇妙的平衡,直到「復仇」的代價如一道雷電打破這所學校的單純外衣,所有人的醜惡、祕密與絕望盡數揭露了出來……
本書特色
★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大獎評審獎作品,以自身成長經驗為背景寫下的校園輓歌
★以高中生主角們的眼光,看穿澳門賭場經濟五光十色背後的社會陰影
★兼具類型感與文學性的青春小說
好評推薦
資深電影監製 劉蔚然
時報出版副總編輯/影評人 嘉世強
作家 七樂
作家 九把刀
香港小說家 譚劍
名人推薦
「高含金量的商業題材,可想見影視改編成果。」——資深電影監製 劉蔚然
「日本戰後第一編劇橋本忍曾說好的劇本,首重主題,然後故事,然後才是人物設定。這是一個有良好劇本觀念發展出來的小說,借刀殺人的設計張羅散布在故事中,不雜沓也不囉嗦,實為佳作。」——時報出版副總編輯/影評人 嘉世強
「澳門的獨特地景構成這本很不一樣的小說。乍看是男生拉幫結派、女生穿校服去酒店援交的校園故事,讀下去卻是涉及兩代人恩怨情仇的賭城風雲。我喜歡作者剝去成人的外衣,展示靈魂被肉慾控制的不堪。」——香港小說家 譚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