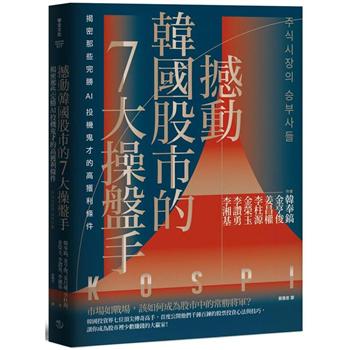起初雖令人恐懼,最終卻讓人覺得溫暖又感動──
小野不由美繼「十二國記」系列,創作生涯又一代表作,
療癒系怪談「營繕師異譚」系列回來了。
「我自己有時也分不清,
究竟是在寫恐怖小說,
還是可愛又令人懷念的東西了。」——小野不由美
★小野不由美從有「民俗寶庫」之稱的故鄉中津發想,深切刻畫土地、建築與人之間的因緣。
明明是該守護我們的「家」,卻成為生存最大的威脅?
既沒有陰陽眼,也不會驅魔的另類建築偵探‧尾端,
藉「營繕」解開老屋謎團,輕巧引領徬徨的心,找到能夠安歇的歸屬之地。
【故事簡介】
「那是危險的東西,會要了你的命!」
本應只有自己的「家」,卻似乎潛藏著另一種存在?
因為父母和弟弟都已經離世,貴樹繼承了位在過往花街的老家。
他發現預定用來當作書房的房間牆上有一道隙縫,隨意地窺視了隙縫,卻看見和鄰家相連的牆壁另一端有一個看似藝妓的女性背影。
在看著對方日常起居的過程中,貴樹不知不覺地被那道背影吸引,忍不住拜訪鄰家,想見那位女性一面。
然而鄰居卻告訴他,那個房間並沒有住人……
──〈芙蓉忌〉
育搬到了一間屋齡超過五十年的老舊町屋。
著迷於自行改造、修繕老屋的她,不斷因為修繕想法的不同和年長的鄰居光子產生衝突。
育有時會在夢中聽到有人影用她不懂的語言斥責她,隨著和鄰居的衝突加劇,育居然開始也在現實生活中聽到斥責聲。
她懷疑是鄰居找她麻煩,然而另外一名鄰居真穗卻告訴她,其實自己也曾經在育家中聽到不該有的說話聲……──〈宿魂〉
建設公司員工遙奈下定決心向男友弘也求婚。沒想到,弘也卻告訴她自己無法和她結婚,因為自己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弘也告訴遙奈,自己打小居住的老宅其實經常飄散著不知從何而來的腐臭水味,有時甚至還會看到一個早已死去的小孩幽魂。
那是他小時候的無心之過害死的小孩……──〈水之聲〉
六篇修繕老屋的同時也修繕生死相隔的人心的小說──
「讀完我恍然大悟,這才是真正的珍惜『因緣』啊!」
──宮部美幸絕讚推薦
【各界迴響】
★《營繕師異譚之貳》是我想要讀,也想要寫的怪談。
即使時代變遷也不會褪色,一定會有人繼續閱讀的名作。──織守きょうや(《記憶使者》作者)
★《營繕師異譚之貳》是一流的恐怖小說,卻也不光是恐怖小說就能概括的作品。
是會讓人覺得「讀了這部作品真是太好了」,非常棒的故事。──阿部智里(《烏鴉不宜穿單衣》作者)
★一邊讀一邊打從心裡覺得實在太恐怖了,但是讀到最後卻感覺獲得了療癒,真是太令人不可思議了。──長江俊和(「放送禁止」系列導演)
日本AMAZON讀者4.5顆星推薦。
BOOKMETER超過2000筆登錄。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營繕師異譚之貳(小野不由美繼「十二國記」系列又一生涯代表系列))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營繕師異譚之貳(小野不由美繼「十二國記」系列又一生涯代表系列))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小野不由美
大分縣中津市出身。大谷大學文學部佛教學科畢業,在學時加入「京都大學推理小說研究會」。
1988年踏入文壇,以「惡靈」系列博得廣大人氣。
1991年「十二國記」系列開始出版,是日本奇幻文學的經典大作。
1993年《東亰異聞》入圍第5屆日本奇幻小說大獎,後於1994年出版,被譽為傳奇推理傑作。
1998年《屍鬼》成為暢銷作,風靡一時。
2012年推出短篇怪談集《鬼談百景》及長篇怪談《殘穢》,掀起話題。
2013年《殘穢》獲第26屆山本周五郎獎,並於2016年改編為電影,由知名導演中村義洋執筒,實力派女星竹內結子、橋本愛主演。
2014年 推出療癒系怪談短篇集《營繕怪異譚》,2019年再推出續作《營繕師異譚之貳》,並以此入圍山田風太郎獎。
相關著作:《營繕師異譚(全新書封,經典回歸版)》《營繕師異譚(漆原友紀彩繪書封)》《殘穢》《鬼談百景》
譯者簡介
王華懋
專職譯者,譯作包括推理、文學及實用等各種類型。
近期譯作有《如碆靈祭祀之物》、《如幽女怨懟之物》、《最後的情書》、《地球星人》、《滅絕之園》、《通往謀殺與愉悅之路》、《孿生子》、《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被殺了三次的女孩》、《dele刪除》系列等。
繪者簡介
CLEA
台灣人,大部分時間玩貓,偶爾畫圖。
小野不由美
大分縣中津市出身。大谷大學文學部佛教學科畢業,在學時加入「京都大學推理小說研究會」。
1988年踏入文壇,以「惡靈」系列博得廣大人氣。
1991年「十二國記」系列開始出版,是日本奇幻文學的經典大作。
1993年《東亰異聞》入圍第5屆日本奇幻小說大獎,後於1994年出版,被譽為傳奇推理傑作。
1998年《屍鬼》成為暢銷作,風靡一時。
2012年推出短篇怪談集《鬼談百景》及長篇怪談《殘穢》,掀起話題。
2013年《殘穢》獲第26屆山本周五郎獎,並於2016年改編為電影,由知名導演中村義洋執筒,實力派女星竹內結子、橋本愛主演。
2014年 推出療癒系怪談短篇集《營繕怪異譚》,2019年再推出續作《營繕師異譚之貳》,並以此入圍山田風太郎獎。
相關著作:《營繕師異譚(全新書封,經典回歸版)》《營繕師異譚(漆原友紀彩繪書封)》《殘穢》《鬼談百景》
譯者簡介
王華懋
專職譯者,譯作包括推理、文學及實用等各種類型。
近期譯作有《如碆靈祭祀之物》、《如幽女怨懟之物》、《最後的情書》、《地球星人》、《滅絕之園》、《通往謀殺與愉悅之路》、《孿生子》、《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被殺了三次的女孩》、《dele刪除》系列等。
繪者簡介
CLEA
台灣人,大部分時間玩貓,偶爾畫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