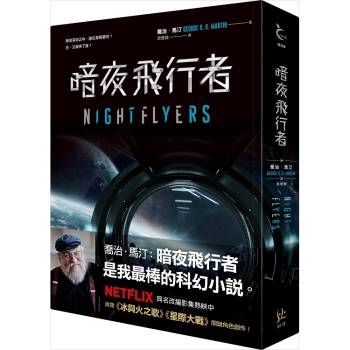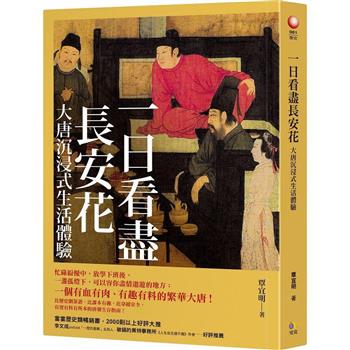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狂骨之夢(經典回歸版,套書不分售)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42 |
二手中文書 |
$ 562 |
日本推理小說 |
$ 600 |
日本推理/犯罪小說 |
$ 600 |
中文書 |
$ 600 |
推理小說 |
$ 600 |
Books |
$ 600 |
Books |
$ 600 |
推理/驚悚小說 |
$ 68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醫師說,他自小便不斷夢見骨頭山前的淫穢儀式;
牧師說,兒時的詭異回憶令他恐懼骨頭;
夢境、現實、妄想纏繞交錯,
三者交錯的夾縫中,始終閃現著骨頭的影子。
坐擁書堆的京極堂,將如何喚醒困在狂骨夢境的他們?
【名家推薦】:
●《狂骨之夢》在作的,是打造怪談的本尊,或者神體。
京極夏彥正實驗著文字與文體,切割它,拼湊它,
用眼睛閱讀的文字去靠近耳朵聆聽的怪談。──陳栢青(作家)
●以「狂骨」串起的夢,不但是這個故事裡所有事件的總稱,
也是京極夏彥對「記憶」一事詩般的喟嘆。──臥斧(作家)
【得獎紀錄】
★1996年版「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第9名
【故事簡介】
一顆金色骷髏頭漂浮在海上,做著跨越時空的夢。
它在冥土與現世相通的水井中自由來去,串連起每個人的夢境。
它在妄想與現實的邊界放聲高歌,令所有人陷入長年瘋狂。
它說我知道你們所有的恐懼,它說我有一個長達千年的大願。
它是狂骨,無人可以從它編織的夢中世界逃脫……
居住在逗子海邊的女子朱美多年來總是夢見自己在海中溶解並化為骷髏頭,從井中仰望天空。
這個令人不快至極的夢境,竟是她數次殺害「死亡的前夫」的前奏。
前精神科醫師降旗多年來鑽研精神分析,卻始終得不到其渴望的「真理」。
精神分析只讓他窺見自己的卑劣之處,因為他自小就不斷夢到男女在骷髏頭山前交合的淫穢夢境。
信仰虔誠的牧師白丘有一個隱瞞多年的祕密。
然而這個祕密,卻隨著海面上漂浮著金色骷髏頭的傳言四處流傳而即將曝光,大大動搖了牧師的信仰之心。
某日,朱美來到醫師和牧師棲身的教會,告解自己的殺人罪行,希望獲得拯救與赦免。
然而,朱美話中的「骷髏頭」就像一個啟動怪事的開關,難以想像的詭譎案件頻繁發生……
五對男女在山中集體自殺,凶器竟是有著皇室菊花紋的匕首;
金光燦爛的骷髏頭在海上漂流,繼而長肉生髮,甚至復活為人;
女子不光數次殺害死亡的前夫,就連最愛的丈夫也命喪其手……
小說家關口和刑警木場因為人情和工作捲入其中。
面對這些怪異案件,束手無策的他們帶著各自的煩惱,
再度走上了那道傾斜的暈眩坡。
坐鎮在古書店「京極堂」中的店主,傾聽了他們的疑惑後,
竟一口斷定:「這真是愚蠢到極點的案件……」
京極堂如此斷言的根據為何?
這三起乍看之下毫無關聯的詭異案件究竟有何相關?
在怪事之間不停閃現的骷髏頭又有什麼意義?
且看京極堂以其淵博至極的學識與如簧之舌,
為眾人驅逐那名為狂骨的附身之物……
狂骨:
狂骨即為「發狂的骸骨」,論者認為,由於過去典籍並無「狂骨」此類怪物,因此應為熱愛創造妖怪的鳥山石燕所創造。
他在《今昔畫圖百鬼拾遺》中這麼形容:骷髏頭下掛著單薄的骨架,儘管披掛的長白髮看似女性,身體輪廓卻隱約不可辨識,
總在井中的汲水桶中以雙手垂放、身下無腳的幽靈姿態現身。
作者簡介:
京極夏彥Kyogoku Natsuhiko
1963年生於日本北海道,曾任職廣告公司,擔任平面設計師、
藝術總監。
1994年將心血來潮寫成的「百鬼夜行系列」首作《姑獲鳥之夏》投稿至講談社,立刻獲得出版,並且大受歡迎,成為日本出版史上的傳奇之一。
1996年「百鬼夜行系列」第二作《魍魎之匣》獲得第49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之後以驚人速度發表此系列新作,至2012年為止共有長篇9作,短篇集4作。暌違7年後,於2019年連續三個月發表「百鬼夜行系列」外傳。以京極堂之妹中禪寺敦子與《絡新婦之理》中登場的女子中學生吳美由紀為主角搭檔的《今昔百鬼拾遺──鬼》、《今昔百鬼拾遺──河童》、《今昔百鬼拾遺──天狗》等三作。
☆得獎紀錄
1996年《魍魎之匣》獲得第49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1997年《嗤笑伊右衛門》獲得第25屆泉鏡花文學獎。
2003年《偷窺狂小平次》獲得第16屆山本周五郎獎。
2004年《後巷說百物語》獲得第130屆直木獎。
2011年《西巷說百物語》獲得第24屆柴田鍊三郎獎。
2016年《遠野物語remix》獲得遠野文化獎。
2019年獲得第62屆埼玉文化獎。
相關著作:《狂骨之夢(上)》《狂骨之夢(經典回歸版)(下)》《魍魎之匣(上)【經典回歸版】》《魍魎之匣(下)【經典回歸版】》《姑獲鳥之夏(經典回歸版)》《今昔百鬼拾遺―河童》《今昔百鬼拾遺--鬼》《書樓弔堂 破曉》《眩談》《百鬼夜行―陰(獨步九週年紀念版)》《百鬼夜行-陽》《怎麼不去死》《邪魅之雫(上)》《邪魅之雫(下)》《百器徒然袋-風》《今昔續百鬼--雲》《冥談》《幽談》《百器徒然袋-雨》《百鬼夜行─陰》《陰摩羅鬼之瑕(上)》《陰摩羅鬼之瑕(下)》《塗佛之宴—撤宴(上)》《塗佛之宴—撤宴(下)》《塗佛之宴-備宴(上)》《塗佛之宴-備宴(下)》
譯者簡介:
蔡佩青
名古屋大學博士。曾任職日本靜岡英和學院大學,現任職淡江大學。主修日本古典文學,著有多部日語學習教材。
從遙遠的彼方,從意識漸遠漸弱的遠方,不斷接近,寂靜卻具脅迫性的隆隆聲。
我聽到的,到底是從哪兒來的?什麼聲音呢?是什麼在作響?發出聲響的是水?……還是風?或是其他東西?我只感到無邊無際的蔓延,無意義的深遠,令人絲毫無法安心。
我原本就討厭海。
在遠離海邊的地方長大,當我第一次見到那個時,我一直在想,海是從哪裡到哪裡呢?
海的主體是水?還是在那之下的海底?
光是這點就沒個準。
浸在水裡的地面算是海嗎?
如果是的話,那該死的海浪又是什麼?
說到海浪,光想就覺得討厭,從彼方綿延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