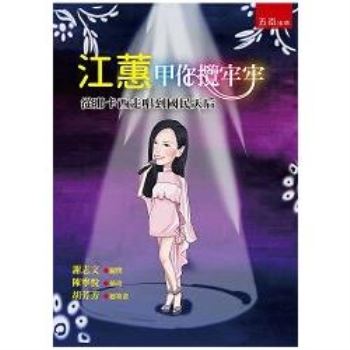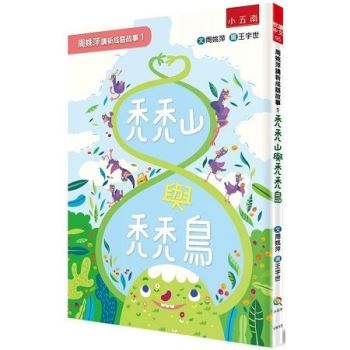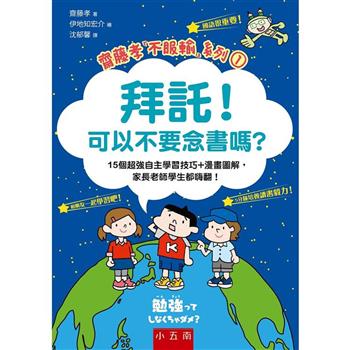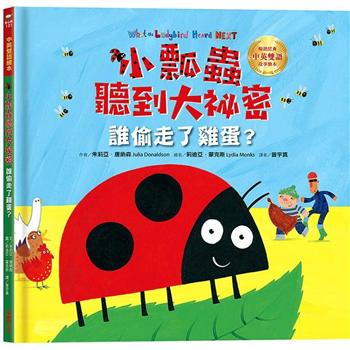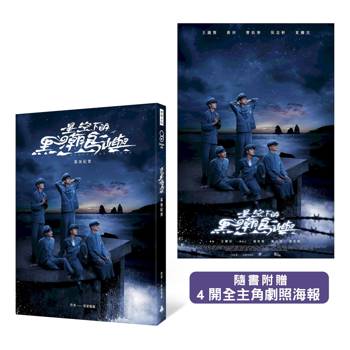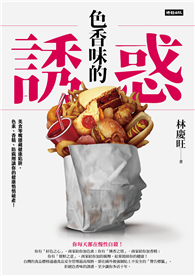將作品裡的「詩意象」純化成火、水、空氣、土四大物質,
探尋陳黎、楊澤解嚴前詩作中個人的存在認同與困境抵抗!
本書借助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的元素詩學,從火、水、空氣、土四大物質的想象切入,分析隱藏在陳黎、楊澤作品中的元素意涵,觀察同一世代的兩位詩人於解嚴前的所思所感,並同時探問「我是誰?」、「我看見了什麼?」、「我面對何種困境?」等題目,進一步開展出「夢想」、「存在」、「抵抗」三大論述面向。
雖然本研究擇取解嚴前的詩作,但無意關注詩歌見證了時代的什麼,而是著重在身處於該時代的詩人如何夢想,並反映在作品當中。作者透過四大元素代表的意義象徵,剖析兩人作品的核心內涵,企圖撕下陳黎詩作多關懷現實、楊澤詩風多走抒情浪漫的標籤,祈望從夢想中照見折射出的新觀點,那是世代交替間不斷更新的意志──詩人將不再受限於審美傳統,而是追求適合該世代或自身獨特的語言質地,在夢想中捍衛自由。
本書特色
★第五屆周夢蝶詩獎評論獎首獎作品。
★從巴什拉元素詩學,透析陳黎、楊澤解嚴前作品中的夢想與困境。
各界推薦
楊小濱(詩人/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