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宮澤賢治的生涯與時代
王憶雲/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宮澤賢治是個難題—或者,該說他是個難以簡略敘述的作家,儘管大抵的作家生涯與作品都是如此。如果我們以某種研究的觀點嘗試談一個宮澤賢治形象,而且力求完整的話,那麼必須請來詩的專家、小說的學者、童話的學者、日本國語教育的學者、宗教學者、熟悉勞動問題的社會學者等,甚至是熟知天文的科學家,坐在一起,或許才能有一個答案。
我想起我第一次走進位於岩手縣花卷市的宮澤賢治紀念館時,驚訝的是除了一般作家手稿、藏書的館藏以外,居然還有樂譜等各種的展品來呈現他對於音樂的喜好。賢治是個古典樂迷,收集了許多唱片,自己也嘗試作曲,同時也填詞(這些曲子讀者有興趣的話YouTube上可以找到)。於是,剛剛提到的宮澤賢治形象討論會議,或許還需要一位音樂家或是樂評。
如此多面向的作家,在現今被廣為閱讀,沒聽過〈銀河鐵道之夜〉名稱的人寥寥可數。比較起作者存活的時期,這狀況其實相當特別。宮澤賢治在生前出版的書,只有可以稱為詩集的《春與修羅》,以及童話集《要求很多的餐廳》,兩者均在一九二四年出版,而且算是自掏腰包。他的創作,在當時除了少數相關人士以外,在文壇可以說是默默無名。在他逝世後,透過草野心平的全力推銷,才讓世人真正看到這位作家的獨特之處,也才會有不到百年的時光,宮澤賢治的全集已經出版過四種:從最早的文圃堂版,還有十字屋書店版、筑摩書房版,以及最新的筑摩書房新校本版。
的確,宮澤賢治是一位生前未能獲得賞識的作家。而且這種前後的落差,包含了空間上的要素。當時的中央文壇便是東京,而宮澤賢治的出生地、求學地(儘管他年輕時有幾次短暫的東京生活經驗)以及主要活動的空間在日本岩手縣,與東京相比,岩手毫無疑問地是偏鄉。因此,偏鄉生產的文學,居然在作者死後迅速地獲得中央文壇的注目,這是日本近代文學中相當罕見的狀況。這罕見的狀況讓文學史難以幫宮澤賢治找個安放的位置,文學史論述頂多在詩,或是在兒童文學的範疇裡稍稍提及這位作家,儘管他留下的作品,以及後來被廣泛閱讀所造成的影響,甚至是以宮澤賢治為核心的文學研究成果,都只能以豐碩一詞來形容(前述的各種全集便是最好的證據)。
當然,能否進入文學史的敘述並不見會是判斷作品好壞的唯一依據(對於作家本人這事可能更不在思考之中),但能以仿若「反攻」的方式從鄉土進入都會,甚至進入教科書,在中心與周邊的固定框架裡,此事自有偶然,也有必然。換個角度說,宮澤賢治製作的作品,或是他耗盡心力想要完成的那些工作(比方說放棄教職,成立羅須地人協會),其實依然與時代緊密相繫,我們能夠去想像那些必然的理由為何。
因此,讓我在這將論述給予一個轉折,也就是—成功的童話作家不單純地只是個童話作家。雖說台灣對於宮澤賢治的宣傳方式,理所當然地集中在童話的框架中,這有著無法深化這位作者存在意義的危機。畢竟,只停留在童話的世界裡,並不能解釋這位作家在死後「反攻」中央文壇且大獲全勝的奇異現象。
在近代文學中嘗試解放個人,探問個人如何存在的脈絡之中,並不會沒有宮澤賢治;在近代日本追求物質層面與思想層面的徹底西化,日本人甚至嘗試信仰基督教的潮流之中,也不會沒有宮澤賢治;甚至是在資本主義無限擴張,壓迫到中下層階級庶民生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思想相繼興起,勞工與農民在大正時期成為文學家的關注對象,一場嘗試顛覆既存文學體系的風暴席捲而來,這時也不會沒有宮澤賢治。
舉例來說,本書所收錄的〈橡實與山貓〉的確是一篇童話,裡頭有我們能夠理解的情感,也有讓我們訝異的奇幻轉折。故事中還有主角一郎在踏上路途的「奇妙」問答,這個問答的確讓我們一步步踏入異世界的迴旋,但是他所問的對象:栗子樹、吹笛瀑布、白色野菇、松鼠,這些只是想像力的隨機產物嗎?仔細瞧,我們可以看到是動物、植物到礦物以及水,生物與無生物的架構。宮澤賢治的世界觀具有龐大的架構,這樣的架構讓他的童話世界自由橫跨更多的藩籬。在一個專精農業的近代人眼中,除了科學以外,重要的還有位居思想根本的《法華經》信仰。在佛教的信仰與世界認識下,橡實與主持審判的山貓才能構成「一幅信眾朝拜奈良大佛的畫作」。
人類以外的動物、植物、礦物,甚至是天體,都是擁有自我的存在,與人類相同,人類能夠與他們進行溝通,進而共存共生。
宮澤賢治出生於富裕的資產階級,讓他有機會接受各種教養訓練,這點與明治末期開始嶄露頭角的「白樺派」文學家相似,他們擁有站在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高處的條件。儘管宮澤賢治接受了白樺派那樂觀、肯定自我的正面影響,但他並未因自己身為資產階級而內心掙扎痛苦,無須步上有島武郎那樣悲慘的末路;同時,他也並未將個人自我絕對化到無法掙脫的困境,農村與偏鄉的立場賦予了他更多的可能性。於是我們至少該去讀一讀,他毅然放棄教職,推動羅須地人協會活動時所撰寫的〈農民藝術概論綱要〉,這是一篇相當精彩的藝術宣言。
我們通常會在許多關於宮澤賢治的介紹文中讀到熟悉的那句:「當全世界的人都幸福的時候,才會有個人的幸福」,然後點頭稱是,儘管我們處在一個個人主義無限蔓延的時代。但這只是〈農民藝術概論綱要〉一開始的一小部分,宮澤賢治的論述從勞苦農民的身分開始,個人意識將離開個人,提升到集團、社會,甚至是銀河系。宮澤賢治解釋了為何需要推動農民藝術,農民藝術的本質又是什麼,進而擴大藝術的定義與可能性,甚至要求正確的農民藝術批評,直到「第四次元」的藝術創造,他在最後呼喊著:「我們需要的是能夠含括宇宙的透明意志,巨大力量與熱情」。
那是宮澤賢治在一九二六年所寫下的文字,也是我們現在重讀宮澤賢治作品,若是想要多理解一點這個作家所創造的世界何以如此特別的關鍵線索。在百年以前,這個大正與昭和的時代交替之際,他誠懇且充滿意志的這則宣言,或許是另一個在「當代」閱讀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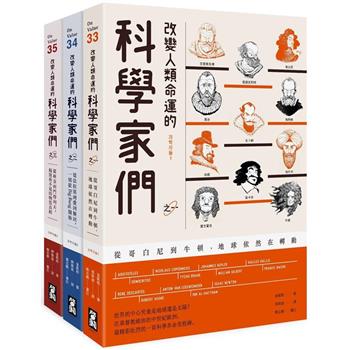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