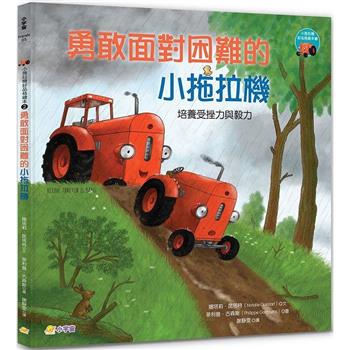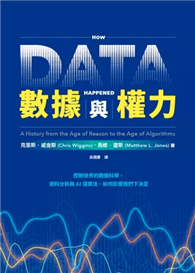正因有許多缺點,
女人的艷姿氣韻反而別具情調,
令人為之心神恍惚……
在忽明忽滅的人性慾念中,窺見美的禪機。
「我的大部分生活,是完全為我的藝術而努力的。」──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是日本唯美主義文學代表大師,文學創作中追求耽美,肉體殘忍、痛切的快感和變態的官能慾望,只為淬鍊美的本質,作品時常出現「嗜虐」、「享虐」、「女體崇拜」、「戀物癖」等變態情慾。本書收錄六篇谷崎潤一郎最具代表性感官小說,完整呈現耽美派文豪從年少成名之作到中年巔峰造極的「谷崎美學」精華。
耽美與惡魔並存,
從感官情慾至人性毀滅、悖德與嗜虐的妖氣之筆
──谷崎潤一郎的感官世界──
⊙ 唯美虐戀經典,當愛與欲望成為信仰──〈春琴抄〉
「春琴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了十歲,膚色雪白,領口更是令觀者頗覺寒氣,渾身起雞皮疙瘩,
指甲色澤光潤的小手端莊地放在膝上,微微垂首的美麗臉蛋吸引舉座目光為之心神恍惚……
佐助曾說,想必人人都以為失明很不幸,但我自己盲眼後倒是不曾有那種感受,
反而覺得人世成為極樂淨土,彷彿只有我與師傅相依為命住在蓮台上……」
川端康成曾評:「如此名作,惟嘆息而已,無話可說。」
〈春琴抄〉為谷崎潤一郎登峰造極之作,以絕對的「女體崇拜」為基調,集感官體驗之大成。故事描寫盲眼女琴師與僕人兼徒弟的佐助間近病態式的畸戀。佐助將春琴的存在,等同於美,他盲目崇拜、獻身春琴,直至最後為春琴致盲。失明的佐助已對現實閉上眼,但他的心靈之眼卻更加敏銳,從此躍向永劫不變的觀念境界,達到與理想的女性結為一體的完美世界。
⊙ 「吸男人的血、踩男人的身體」典型谷崎魔女代表──〈刺青〉
擁有極佳手藝的刺青師清吉,畢生最大的願望是找到一位有光彩動人肌膚的美女,刺入自己的靈魂。在他銳利的雙眼看來,人的腳就與臉一樣擁有複雜的表情。那個女人的腳,對他來說猶如珍貴的肉中寶玉。這雙玉足,正是以男人的鮮血為養分,踐踏男人軀體的腳。擁有這種腳的女人,想必就是他長年來尋尋覓覓,女人中的女人……
〈刺青〉為谷崎潤一郎二十四歲的出道之作,女主角由純真女孩變為妖豔魔女的過程,其實是男人期待的一種罪惡,它反映了男性的慾望。三島由紀夫曾說:「當母親的純潔之愛與性慾混淆時,她會立即改頭換面,變成典型的谷崎魔女,如〈刺青〉中的女孩一樣。她美麗的身體潛藏著一種黑暗、殘暴、罪惡的東西……」
⊙ 女體迷戀、執著的情慾──〈富美子之足〉
「富美啊,拜託用妳的腳在我的額頭上踩一會好嗎?
若妳肯這麼做,我縱使就這麼死掉也了無遺憾……」
〈富美子之足〉描述垂暮之年的老人,納藝妓富美子為妾,他不求性愛的滿足,卻拜倒在富美子曲線優美、白皙滑嫩的玉足下,異色綺情的內容,為谷崎晚期代表作〈瘋癲老人日記〉的原型。
作者簡介:
谷崎潤一郎
1886年生於東京日本橋。東京帝國大學國文科肄業。1910年初試啼聲,發表短篇小說〈刺青〉、〈麒麟〉等,大受好評,從此登上文壇。作品多以女性崇拜、戀物癖、嗜虐等強烈慾念描寫作為基底,將感官美學推展至極致。日本文學界奉其為經典的耽美派大師。曾以《細雪》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及朝日文化賞,以《瘋癲老人日記》獲得每日藝術大賞,1949年獲頒日本文化勛章,1960年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1965年因腎病辭世。
代表作有《春琴抄》、《痴人之愛》、《細雪》、《鍵》、《瘋癲老人日記》等。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包括三島由紀夫《金閣寺》;川端康成《伊豆之旅》;谷崎潤一郎《春琴抄》;太宰治《女生徒》;夏目漱石《我是貓》;宮澤賢治《銀河鐵道之夜》等日本文學作品,皆為大牌出版。
章節試閱
春松檢校家位於靭,離道修町的鵙屋藥鋪約有十丁距離,春琴每天都由小學徒牽著她去上課。那名小學徒是當時名叫佐助的少年,也就是日後的溫井檢校,他與春琴的緣分就是由此產生。佐助如前所述生於江州日野,老家同樣經營藥材鋪,他的父親與祖父在學徒時代都曾來到大阪在鵙屋當學徒,所以鵙屋對佐助而言其實是歷代的主家。他比春琴大四歲,自十三歲起到鵙屋當學徒,算來是在春琴九歲,也就是失明的那年,但他來鵙屋時春琴美麗的雙眸已永久閉鎖。對於自己一次也沒見過春琴眼中的光芒,佐助直至後來始終不悔,反而覺得很幸福。如果在春琴失明之前就認識她,或許會覺得她失明後的臉孔不完美,但幸好他對她的容貌沒有感到任何不足,打從一開始便覺得那是圓滿具足的臉孔。今日大阪的上流家庭爭相遷居郊外,千金小姐們也經常運動,接觸野外的空氣與陽光,所以已經沒有以前那種深閨佳人式的溫室花朵了,不過至今住在市區的孩子一般而言體格還是較為纖弱,臉色也很蒼白,和鄉下長大的少年少女連皮膚的光澤都不同,說好聽點是脫俗文雅,說難聽點是病態。這不僅限於大阪,而是都會的通病,但在江戶連女人都以膚色微黑為傲,膚色白皙的程度終究不及京阪地區,在大阪世家望族長大的小少爺雖為男子也像舞台上扮演的少東家那般骨骼纖細,直到三十歲前後才開始曬得臉色通紅積
蓄脂肪,身體忽然發胖,具備紳士該有的威嚴,在那之前他們就和婦孺一樣蒼白,穿衣也偏好柔弱的風格。遑論生於舊幕府時代的富裕商家,鎮日待在不健康的深閨養大的姑娘,她們那種幾近透明的白淨、蒼白與纖細,在鄉巴佬佐助少年的眼中看來不知有多麼妖豔媚惑。這年春琴的姐姐十二歲,底下的大妹妹六歲,對於剛來到都市的佐助而言,姐妹幾個都是難得一見的嬌貴少女,但盲眼的春琴那不可思議的氣韻格外打動他。春琴緊閉的眼皮比姐妹們睜開的眼睛更明亮美麗,甚至令人感到這張臉就該是這樣才對,這才是本來的樣子。四姐妹之中春琴豔冠群芳的風評最盛,即便真是事實,想必也有幾分是因為人們憐惜她的殘疾,但佐助絕非如此。日後佐助最討厭別人說他對春琴的愛意是出於同情與憐憫,有人那樣觀察令他非常錯愕。他說:我看到師傅的臉從來沒有覺得可憐或同情,和師傅比起來,明眼人才可悲,以師傅那等氣質與容貌何須乞求他人的憐憫,說我可憐反而同情我的人,我與你們只不過五官俱全,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地方比得上師傅,我們才是有缺陷的那個。但那是後來的事,佐助起先只是在心底深處暗藏熾熱的崇拜,雖然勤快服侍,應該還沒有戀愛的自覺,就算有,對方是天真無邪的富家千金而且又是歷代主家的小姐,對佐助而言每天可以陪她一起走路想必已是莫大的安慰了。以他這樣初來乍到的小少年,居然被命令牽著寶貝大小姐的手似乎有點奇怪,但起初其實不只是佐助,女傭也會跟著去,有時也會命令其他的小廝或年輕僕人陪伴春琴,經過種種人陪伴直到有一次春琴自己表示「我想要佐助哥兒陪我」,從此才成了佐助專屬的工作,那是在佐助十四歲的時候。
○
佐助在春琴過世十餘年後,曾把他失明時的經過告訴身邊的人,據此總算得以釐清當時的詳情。換言之,春琴被凶徒襲擊的那晚,佐助一如往常睡在春琴閨房的次間,聽到動靜醒來時,有明行燈的燈光已熄,黑暗中只聞呻吟聲,佐助大吃一驚當下跳起,先點亮燈火,提起那燈籠趕往屏風那頭的春琴寢床,然後在燈籠模糊的燈影反射屏風金底的微光中環視室內的情形,未見任何翻亂的跡象,唯有春琴的枕畔扔了一個鐵壺,春琴也在被褥中靜靜仰臥,但不知何故低聲呻吟。佐助起先以為春琴是夢魘,於是走到枕邊說:師傅,您怎麼了?師傅?他本想把春琴搖醒,這時不禁驚叫一聲,蒙住雙眼。佐助,佐助,我變得好醜,別看我的臉!春琴也在痛苦喘息下扭動身子掙扎,拼命揮動雙手試圖蒙住臉孔。請放心,我不會看您的臉,我把眼睛閉起來了。他說著把燈籠也拿遠,春琴聽了或許這才鬆了一口氣,就此不省人事。之後始終在昏迷中不停囈語:誰也不准看我的臉,此事一定要保密。如果安慰她:您何必那麼擔心,燙傷的痕跡消了之後很快就會恢復原本的容貌。她卻說:這麼嚴重的燒燙傷,容貌怎麼可能沒變,我不想聽那種安慰話,重要的是不准看我的臉。等她恢復意識後更加這麼強調,除了醫生之外甚至在佐助面前也不願展現負傷狀態,換膏藥與繃帶時還把大家都趕出病房。佐助當晚趕到她枕畔的瞬間,雖只瞄到一眼燙傷的臉孔,但他不敢正視立即撇開臉,所以只留下燈影搖曳的陰影中彷彿看到什麼不似人類的怪誕幻影的印象,之後看到的都是繃帶中露出的鼻孔與嘴巴。想來一如春琴害怕被看,佐助也害怕去看,他每次靠近病床總是努力閉眼或把視線移開,因此春琴的相貌竟究有何種程度的變化,實際上他並不知情,也主動迴避知情的機會。經過好生療養,傷勢也漸漸康復時,某天病房只有佐助一人陪侍,春琴忽然苦惱地詢問:佐助,上次你看到我這張臉了吧?沒有沒有,您說不能看,我怎麼敢違背您的意思。聽到佐助這麼回答,春琴說:我近日如果傷勢痊癒就得拆下繃帶,醫生也不會再來,屆時撇開別人不說,至少必須在你面前露出這張臉。向來好勝的春琴此刻或也意氣消沉,終於難得一見地流下淚水,隔著繃帶頻頻按壓雙眼,佐助也為之黯然,想不出該說什麼,只能一同嗚咽。不會的,我一定不看您的臉,請安心吧。佐助似乎心中已有決定般說道。過了幾天春琴也已康復到可以起床,隨時拆繃帶都無礙的狀態時,某日一早,佐助自女傭房間偷偷取來女傭使用的鏡子與縫衣針,端坐在寢床上,對著鏡子把針戳進自己的眼中,他並不知道被針戳到是否就會立刻失明,只是想找個盡量減少痛苦的省事方法變瞎。於是他試著拿針戳刺左邊的黑眼球,要對準黑眼球戳進去似乎很困難,白眼球的部分很硬,針戳不進去,但是黑眼球很柔軟,戳了兩三下後便以巧妙的狀態刺入二分左右,頓時眼球整片變得白濁,可以感到視力正逐漸喪失,沒有出血也沒有發熱,幾乎完全感覺不到痛楚,這是破壞了水晶體的組織引起外傷性的白內障。佐助又對右眼如法炮製,霎時毀了兩眼,不過起先據說還是能模糊看見東西的形狀,過了十天才完全看不見。等到春琴起床時,他摸索著走到裡屋,師傅,我失明了,從此一輩子也看不見了。他伏身低頭在她面前說。佐助,那是真的嗎?春琴說出此句後便長時間默默沉思。佐助此生無論之前或之後,再也沒有比這沉默的數分鐘之間更快樂的時光。昔日惡七兵衛景清有感於源賴朝的器量放棄復仇之念,發誓從此再也不見此人,於是自挖雙眼。佐助雖與他的動機不同,但其志之悲壯如出一轍,不過話說回來,春琴向他要求的就是這個嗎?當日她流淚傾訴的就是自己既遭此大難你也該變成盲人之意嗎?我們難以深入忖度,但「佐助,那是真的嗎」這簡短的一句話,在佐助聽來,似乎因喜悅而戰慄。當他們相對無言之際,唯有盲人才有的第六感在佐助的官能萌芽,他可以自然體會到春琴除了感謝別無他念的心情,到目前為止雖有肉體關係卻被師徒之別阻隔的兩顆心,至此終於緊密相擁合而為一。少年時代在壁櫥裡的黑暗世界練習三弦琴的記憶重現腦海,但與彼時的心態已截然不同,大約一般盲人都只有光的方向感,因此盲人的視野隱約有光影並非黑暗世界,所以佐助知道現在雖失去外界之眼卻開啟了內界之眼,嗚呼,這才是師傅定居的真正世界,這下子終於可以和師傅住在同一個世界了。他衰退的視力雖已無法再清楚分辨房間的樣子與春琴的身影,但唯有那以繃帶包裹的臉部兀然映現在泛白的視網膜,對他來說那一點也不像是繃帶,就在二個月前師傅仍有一張圓滿微妙的白淨臉龐,它在暗淡的光圈中宛如來迎佛般浮現。
春松檢校家位於靭,離道修町的鵙屋藥鋪約有十丁距離,春琴每天都由小學徒牽著她去上課。那名小學徒是當時名叫佐助的少年,也就是日後的溫井檢校,他與春琴的緣分就是由此產生。佐助如前所述生於江州日野,老家同樣經營藥材鋪,他的父親與祖父在學徒時代都曾來到大阪在鵙屋當學徒,所以鵙屋對佐助而言其實是歷代的主家。他比春琴大四歲,自十三歲起到鵙屋當學徒,算來是在春琴九歲,也就是失明的那年,但他來鵙屋時春琴美麗的雙眸已永久閉鎖。對於自己一次也沒見過春琴眼中的光芒,佐助直至後來始終不悔,反而覺得很幸福。如果在春琴失明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