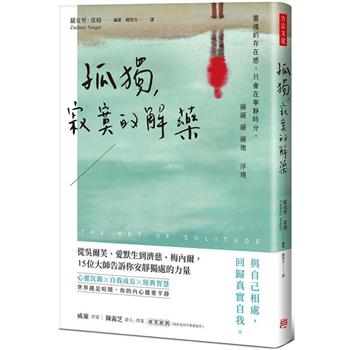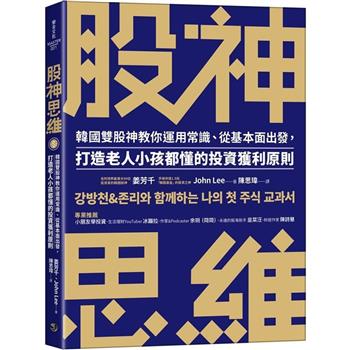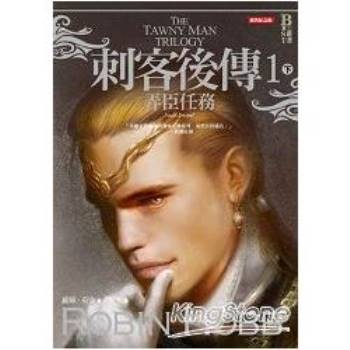這個世界,對少女來說就是地獄……
她以自己的____,為那幅地獄繪卷的真實存在背書。
與江户川亂步、小栗虫太郎齊名!
日本變格派推理代表第一人──超級怪物作家夢野久作
詭色、暗黑、獵奇瘋狂的官能世界
幻滅與墮落交織之華麗書寫
她以自己的____,為那幅地獄繪卷的真實存在背書。
與江户川亂步、小栗虫太郎齊名!
日本變格派推理代表第一人──超級怪物作家夢野久作
詭色、暗黑、獵奇瘋狂的官能世界
幻滅與墮落交織之華麗書寫
日本推理變格派大師夢野久作,作品風格充滿詭譎、恐怖、醜惡,擅長在謎團層層抽絲剝繭中,細膩描繪人性之惡、變態乖張、瘋狂與戰慄恐怖心理。短暫十年的作家生涯,夢野久作猶如文壇中的一顆彗星,作品產量高且豐富多變,包含科幻、偵探、幻想等類型。在推理小說界中獨樹一格,分量之重與江戶川亂步及小栗虫太郎齊名,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更對其才華讚譽有加,自嘆遠遠不及。
《少女地獄》被譽為夢野久作推理短篇巔峰代表作,由三篇小說〈什麼都不是〉、〈連續殺人〉與〈火星之女〉組成。描寫圍繞在人世間的謊話、欺瞞、愛、恨中的三名女性因虛無感而走向幻滅,從這三名女子所墜落的地獄,勾勒出人心最暗黑的真實。以書簡形式高超巧妙地展開複雜且難以預測的情節故事,藉由詭異恐怖卻又怪奇繽紛的筆鋒,帶給讀者多重的快感與戰慄,正是夢野久作最大的魅力。
「無論是謎團、詭計還是名偵探、名犯人,若無必要都可以捨去。神祕、怪奇、冒險、變態心理等等都好……若不確保產生某種令人戰慄、恐怖的毒腺元素,良心上就感受不出生存的價值。若不偵探、暴露到底,本能上就無法滿足。」──夢野久作
※〈什麼都不是〉──愛說謊的少女
「當她自己所構築的那個虛構天堂之夢被打碎後,
不就得再度被放逐於人生冰冷的道路上嗎?
對這種女性而言,幻滅是比宣告死刑更為恐怖的事。」
臼杵醫院的吉祥物天才護士姬草百合子,極具天賦且討人喜愛,在病患間甚至有著比院長更高的名望。然而她卻留下一封遺書,信中隱射自己遭遇了不堪之事而痛苦不已。似假非真的內容,投映出闇黑人性的塊塊殘骸,淒厲控訴的背後,真相究竟是什麼……
※〈連續殺人〉──愛上殺人魔的少女
「從今以後,無論發生什麽事都不可以當女車掌。
千萬不可以成為像我這樣的女人。」
智惠子是一名渴望成為女車掌的鄉下女孩,某天她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也許會成為恐怖殺人事件的祕密證據。寄信人富美子再三慎重囑咐,絕對不能成為女車掌,只要讀完這封信,就會明白其中的理由……
※〈火星之女〉──身分不詳的焦屍少女
「我的屍體被發現時,恐怕已燒成焦黑到任誰都認不出來了吧?
而且報紙也正在大肆報導吧?」
一所高中女校廢棄屋火災後,發現一具焦黑女屍。隨後該校校長失蹤發瘋,校內女教員自縊死亡,書記捲款潛逃下落不明,一連串焦黑女屍事件餘波不斷,調查方向始終毫無頭緒。在一片五里霧中,直到相關人士愛子的書信公開與死者親筆手記曝光,一切謎團才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