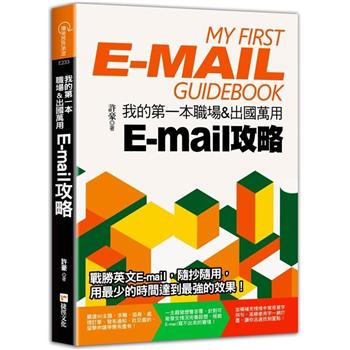初版序
戰地裡哪來的鐘聲
在本書上梓之前,我和幾位朋友有著定期聚會的約定。我們基本上是同代人,獨立戰爭那一年都是中小學生的年紀。他們知道我近年在進行「戰爭記憶」的主題研究,因此若有什麼新發現、哪位值得一訪的報導人,便會在聚會上交換情報。本書若干篇章——為保護資料來源,恕我無法直接點明——,就是在朋友們大力協助下,才得以出土成文的。我們都是有些歷練的年紀了,也都明白「戰爭記憶」在如今的社會環境下,是多麼紛雜、沉痛又充滿矛盾的主題。於是,我們自然發展出一套「不爭辯對錯」的默契,就算彼此收集到的說法、介紹的報導人有明顯的衝突,也不會強求說服對方。
不過,這個默契卻在最近一次聚會破裂了。
起因是某人突發的抱怨:「你們知道嗎?現在的學校,上下課時間都沒有鐘聲了!他們說是為了讓師生一同學習『時間管理』,所以取消制式統一的上下課時間。天啊,沒有鐘聲的學校!你們可以想像嗎?就連戰爭期間,學校的鐘聲都沒有停止過,反而現在通通沒有了!」
某人的有感而發,想必是來自他最近剛上小學的女兒。我雖然沒有兒女,但因為身處文化、教育的圈子,對於取消鐘聲一事早有所聞,對這番話也就沒有太放在心上。我隨著大家一起舉杯安慰某人,說了些「時代變了」之類自己聽了也覺衰老的嘆語。本來這甚至算不上一個話題,大家藉此乾一杯也就完事了。不料另一位朋友瀝乾酒杯後,補上了一句:
「可是,我記得打仗那陣子,學校也沒有鐘聲啊——」
就是這句話掀了鍋。本來和樂融洽、一同暢述往事的大家,瞬間分成兩個陣營。一半的人記得當年校園鐘聲不輟,因為政府官員咬定解放軍不敢隨意轟炸學校,所以除非是陸軍交戰的區域,否則並不停課,當時的教育部長還出來說了「文明不會因為野蠻而暫停」的名言,至今仍時常被引用。但另外一半人卻認為前者記錯了,當時確實是以「盡可能不停課」為原則,甚至因此招致了反對黨「以學生為肉盾」的質疑,但為了節省電力、保持廣播線路暢通等安全考量,所有上下課鐘聲都被取消了。
或許是因為這件事不涉及政治立場、道德難題或創傷記憶,沒有敏感到需要尊重異己的程度;也或許是因為這牽涉到最單純無害的童年回憶,反而重要到不由得他人否定。總之,雙方為此激烈爭辯,卻誰也無法說服誰。賭氣也似的,這批在各自的領域均有所成的朋友,不分教師、作家、工程師、學者、總經理,在聚會結束之後,還持續用自己的方法考證「戰地裡有沒有鐘聲」的問題。有人試圖尋找當時頒布的行政命令,卻仍無法證明鐘聲之有無;有人則從影片下手,寫了爬蟲分析整個國家戰爭史資料庫。但這個看似簡單的細節,就像千千萬萬如今我們再也無法確認的歷史場景一樣,徹底丟失了謎底。一個幾千萬人居住,且手機與網路已然普及的國家,竟然就這麼剛好找不到一個,哪怕只是一個,記錄了戰時學生上下課細節的檔案。而且,這還不是年湮代遠的數百年前,僅僅只是二十年前,我們都親歷過的「當代」而已。
簡直就像是歷史之神刻意惡作劇,基於某種我們不知道的原因,將所有的「鐘聲」一手抹除了。
我沒有參與爭論。長年研究「戰爭記憶」的我,雖然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卻已培養出某種直覺,讓我在聽到鐘聲爭辯的瞬間就意識到:這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果時至今日,我們連每一支部隊的具體行動、每一項政策的執行狀況,乃至於「是否曾有過某一舉措」——包括但不止於本書中提到的「假彈藥」、「戰鬥興奮劑」和「東方明珠塔事件」——都無法確證,那更庶民、更生活性的細節會缺乏記憶以外的可靠證據,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了。
如果說這幾年的研究讓我有什麼體悟,那便是「歷史的流失是不可逆的」,並不以人的情感為移轉。不管你覺得自己記得多麼真確,不管你多麼想要回憶起那些生命中的重要瞬間,戰爭所製造出來的巨大雜訊就是能夠遮蓋一切。
同時,這份體悟也支持了我至今的探索,以及各位所讀到的這本書。正是因為歷史之流失不可逆,因此我們沒有挑選的餘裕,而必須先傾盡全力,保留一切少為人知的記憶。這些記憶或許不被官方承認,或許不為主流意見所喜,或許跟「鐘聲」一樣永遠找不到證據,但「有人活在這些記憶裡」,卻是千真萬確之事。光是這一點,就使之有記錄留存的價值。
也因此,我從過往的研究裡挑出了五組報導人,將他們的記憶編寫為《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的五篇文章。我挑選的標準主要有二:一、他們所提供的細節數量足夠豐富,已到了普通人難以全盤虛構、編造的複雜度;二、他們所提供的視角與官方論述有一定距離,甚至也與其他民間觀點有所扞格,而能補充「另類觀點」。
當然,在此我也要澄清,我並不是認為他們所言必定為真,而官方或主流社會的否認必定有誤。事實上,就如同官方論述不可能句句屬實,我們幾乎也可以確定這些報導人的記憶不可能全然真實。這甚至毋須質疑任何人的道德水準和政治立場,因為這種不準確,是建立在人類心智內建的變形機制上的。任何經驗,必先變形為我們的心智能夠理解、接受、儲存的形式,才能被記憶歸檔。
因此,與其說這些故事的價值在於「它們全是真的」,不如說,我是懷抱著「如果它們不全是假的」之心念,才將之編織成文的。如果這些證言當中,有那麼幾絲如「鐘聲」一般,一旦散佚就無可挽救的事實細節,那就值得我們以文字刻抄,避免它們沖失在時間之流裡了吧。
也基於上述考量,我並未採取三年前的拙作《戰爭證言二○四七》的報導文學形式來撰寫本書。我擔心如此「真實」的、「非虛構」的形式,會讓讀者誤會我全盤接受了報導人的證言。經過長久的思考和探索,我從台灣文學史的一部經典名作得到了靈感:距今大約一世紀前,有一部同樣描寫戰爭的作品,即鄧克保的《異域》。這本書出版之初被視為報導文學,但多年後人們發現,它其實是由作家鄧克保採訪前線老兵之後,重新編排情節的作品,本質上更接近紀實性的小說。
鄧克保的作法,在後世的文學研究引起不少倫理爭議。然而,我認為其「轉譯者」的敘述位置,是有值得取法之處的。因此,我斗膽僭借前輩作家的結構,編寫了這本《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本書的五篇文章都來自報導人的口述,以及若干研究材料的交叉比對;但實際上落筆撰寫的,並非受訪者本人,而是由我消化、重整後代筆。因應不同主題,我也採取了不同的敘述方式,或有「備忘錄」、「報導」,亦有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傳統小說形式。
如此交錯進行,意在混淆真實與虛構的界線。我希望讀者能夠理解:在看似言之鑿鑿的客觀形式裡,我們無法避免錯謬記憶的滲透;而在看似主觀任意的私我敘述裡,我們也無法排除堅硬抵抗著時間的事實。
真實與虛構,都是我希望提醒讀者注意的。至於如此矛盾而又貪心的願望,能不能在我有限的筆力之下完成,就並非我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沒能完成它應完成的任務,責任自然在執筆者我身上。而如果本書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價值,首先當然要感謝匿名的報導人,以及所有曾經提供寶貴記憶的倖存者。其次,便是支持我完成本書、在本文開頭提及的朋友們:永遠的第一位讀者謝宜安,在寫作上提供了我大量意見的林盈志、朱宥任、寺尾哲也、黃致中、李奕樵、陳栢青、林劼宏、田家綾、林于玄、吳俊賢、洪浩植、林衛央、陳慧潔、張喬雅、陳冠宏,以及從專業上提供我許多不可或缺之協助的周漢樺、Eagle Kuo、白兆立。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這本書恐怕是沒有機會誕生的。
最後,關於「鐘聲」一事,我也趁此向前列的朋友們表明立場:是的,我記得。我的腦袋裡,仍不時響起那輕快的、代表禁制解除、能夠跑向操場的水晶音樂。它時時縈繞我的腦際,夾雜著尖銳的空襲警報蜂鳴聲,使我幾乎難以好好思考,那個時候的我到底在哪裡、在做什麼、想些什麼。作為歷史研究者,我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說服和我意見不同的那半邊朋友。但作為一個人,我深深地理解:即便出現了「戰地裡沒有鐘聲」的明確證據,我腦袋裡的旋律與時代,也不可能就此取消。
這也是為什麼,我願意偶爾站在被否認的這一邊。
朱宥勳,二○六七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