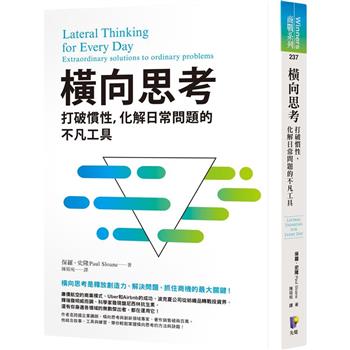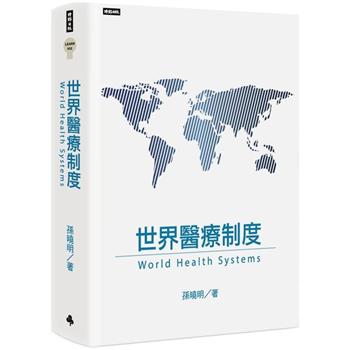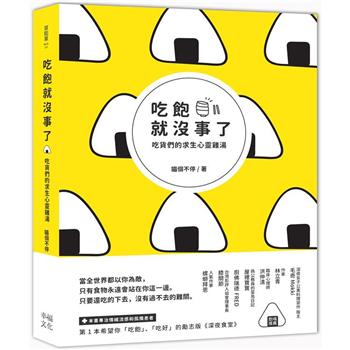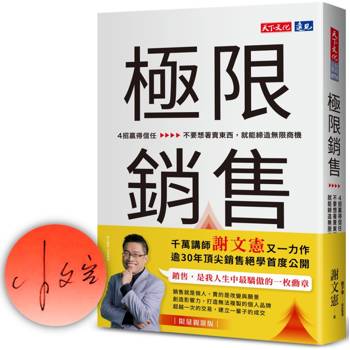導盲犬與調音師
酷爸在導盲犬的引導下,徐徐前進。
雖然才六月初,臺北的高溫卻已讓人招架不住。走在臺北街頭,宛如置身於烤箱中,簡直快把人烤焦了。汗水如水柱般從酷爸身上湧出,他卻顧不得擦拭,反而停下腳步,安撫引導他前進的夥伴。
從英國回到臺灣後,酷爸便發現他的夥伴對炎熱的天氣有些適應不良。牠步履遲緩,而且食欲不振。其實不光是導盲犬,就連他自己也有些受不了。英國夏天的平均溫度大約攝氏二十二度,一年難得有幾天會超過二十八度,他幾乎已經忘了臺灣是這麼熱。離開臺灣那年,他才十五歲。這二十多年來,他曾回來過兩次,不過都是在冬天。重溫臺灣夏天的熱度,這還是第一次呢!
臺灣有多熱,他確實是忘了;但當陽光直射在皮膚上所引發的灼熱感,卻又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童年往事也隨著逐漸增高的熱度在心中沸騰著。
「二十多年了,他們在哪兒?該上哪兒去找他們呢?」
一想起失去聯繫的親人,酷爸不由得嘆了口氣,身旁的夥伴也發出低沉的喘息聲。
根據調音公司所提供的資訊,趙太太家應該就在這附近,但為了謹慎起見,酷爸還是習慣性地向臨近的商家詢問。
「請問居禮大廈還有多遠?」
一個婦人驚訝地看著他,「你,一個人?」
「和我的狗。」
婦人這才注意到他身旁有一隻導盲犬,盯著牠看了好一會兒,才說:「再往前走個一百公尺左右,那幢磚紅色,喔,那幢大廈就是了。」
婦人有些尷尬,酷爸卻不以為意地向她道謝。
到了大廈前,酷爸以堅定而簡短的語氣對導盲犬下達命令,「 Enter the Building(進入大廈)」。導盲犬轉身進入大廈中,找到管理員後,停住腳步,等待主人向管理員說明來意。
管理員用難以置信的眼光打量著導盲犬,「這隻狗真的會帶路?」
「牠是受過訓練的導盲犬。」酷爸簡短地回答。
「這麼神啊!」管理員仍然半信半疑,盯著導盲犬看了半天。
「十二樓的趙太太請我來調音,我現在可以上去嗎?」
「你是鋼琴調音師?」管理員打量著酷爸,再度露出不可置信的眼光,心想他眼睛看不見也能調音嗎?「我記得以前來替趙太太調音的是一個年輕小夥子,他今天怎麼了?」
「我不太清楚,趙太太打電話到調音公司,公司就派我來了。」
管理員又將目光轉向導盲犬,看了老半天,才想起酷爸剛才的問題。
「沒錯,趙太太家在十二樓,要不要我帶你上去?」
「不用了,謝謝。」酷爸說完,便命令導盲犬前進,同時下達找電梯的指令,
「 Find the lift(尋找電梯)」。導盲犬立即引導主人朝電梯走去。
這下子管理員更驚奇了,雙眼瞪得宛如龍眼般大;彷彿在宣告什麼重大發現似的,大聲嚷著:「哇!狗居然會自己找電梯,太神奇了。」這樣的驚嘆聲,酷爸並不陌生。臺灣這幾年才開始引進導盲犬,知道的人不多,看到導盲犬多半都會感到驚奇。
趙太太不在家,開門的是她十歲的兒子。當他看到導盲犬時,驚奇的表情並不亞於樓下的管理員。
酷爸進入屋內,又給導盲犬一個尋找鋼琴的指令。導盲犬在琴房找到鋼琴後,自動趴在鋼琴邊。牠的舉動讓小男孩看得瞠目結舌,連呼三聲,「酷斃了!」酷爸從背包裡拿出調音工具,同時開始自我介紹,「我姓戴,不過大家都叫我酷爸。」
「我叫趙小棣,」男孩說出自己的名字後,急忙又補上一句,「不過,我的棣,不是小弟弟的弟,是棣樹的棣喔!」
酷爸微微一笑。
男孩一陣臉紅,「我是怕你以為我在開玩笑,才會說那麼多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這麼以為啊!」小棣急著說明,「以前很多人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趙小棣。他們不知道我的棣是棣樹的棣,以為是小弟的弟,就會再問一次,『小弟,別開玩笑了,你到底叫什麼名字?』我只好再說一遍,我叫趙小棣。可是他們還是搞不懂,以為我在尋他們開心,就會變得不耐煩,有的人甚至還會生氣,提高嗓門說,『趙小弟,別鬧了,你到底叫什麼名字?』我又說我叫趙小棣,他們就會開始譏笑我,說:『哪有人的名字叫小弟,你爸、媽是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個男生,所以給你取了這個名字嗎?』為了避免發生這樣的誤會,每次有人問我叫什麼名字時,我都要很詳細地說明白。可是每次都要這樣解釋,多累呀!我真擔心等我到了七十歲的時候,大家還是『小弟』、『小弟』地叫我,那有多尷尬啊!」
聽著小棣嘰哩呱啦地解釋他的名字,酷爸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兒子小琺,竟笑了出來。
「這很好笑嗎?」小棣有點生氣。「不,」酷爸連忙搖頭,「你讓我想起了我的兒子。他和你一樣,說起話來就像機關槍似的,劈里啪啦的一大串,常讓我來不及聽。」
「你的兒子幾歲?」
「他今年剛滿十歲。」
「跟我一樣耶!」男孩這才又露出笑容。
酷爸準備開始調音。當他掀起琴蓋時,觸摸到琴蓋上有道刻痕,心中不由得一震。那道刻痕又深又長,刀法零亂錯落,可見留下這刻痕的人當時是多麼憤恨。刻痕的觸面還很粗糙,大概是不久前才刻上的。酷爸反覆觸摸著那道刻痕,心想會是這個小男孩嗎?
突然,一個女孩的聲音傳來,「不過是架鋼琴,幹麼那麼捨不得?」
那聲音宛如一顆猛然投入湖中的巨石,在酷爸的心海激起一陣狂浪波濤。是她嗎?會是她嗎?酷爸遽然轉向聲音來處,並站了起來。那個日日夜夜在他心中盤旋縈迴的聲音,此刻又在耳畔響起。那麼熟悉,那麼真實,沒錯,一定是她沒錯。正當酷爸想叫出深藏在他心靈深處的那個名字時,小棣卻先開口了,「姐,你看,是導盲犬!」
「哇!真的耶!」女孩的聲音立即開朗起來,直奔向導盲犬。
酷爸彷彿從雲端跌下來似的,重重坐在鋼琴椅上。他甩了甩頭,似乎想趕走腦中那個可笑的念頭。事隔二十多年,她早該是個大人了,聲音怎麼可能還像個小女孩呢?但太像了,她們的聲音實在太像了。
酷爸努力地將注意力拉回鋼琴上,卻久久無法定下心來。他一邊聽著女孩與弟弟的閒談,一邊觸摸那道刻痕,會是她刻的嗎?他很想知道,卻又不敢貿然地問。
然而,出乎意料的,女孩的聲音再度傳來,「那是我刻的。」
「你?為什麼?」
「因為我討厭它,我恨它!」女孩冰冷的口吻,讓酷爸大吃一驚。
被父母逼迫學琴而心生厭惡的孩子,酷爸在調音的生涯中碰過不少,但沒有人像她這般激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酷爸沒再問,思緒卻飄回少年時期。當年為了學琴,他可是廢寢忘食,還做出了讓他終身懊悔的事……
「酷爸,牠叫什麼名字?」小棣的聲音將他從回憶中拉回。
「啊?」他還沒會過意來。
「你的導盲犬叫什麼名字?」
「牠叫酷弟。」
「酷弟。哇,好酷的名字喔!」小棣恍然大悟,「啊,我懂了,牠叫酷弟,你是牠的主人,所以大家才會叫你酷爸,對不對?」
酷爸點點頭,心思卻仍在那道刻痕上。
小棣與姐姐喜孜孜地逗著酷弟玩,酷弟卻靜靜地趴在地板上。小棣有點失望,「為什麼牠都不理我們呢?」
「因為牠還在執勤,」酷爸摸索著走向酷弟,拿下牠身上的導盲鞍,拍拍牠的背,示意牠可以四處活動。「現在牠自由了,你們可以給牠一些水喝嗎?」
「沒問題。」小棣爽快地答應,並將酷弟帶去廚房。
琴房頓時安靜下來,酷爸吸了口氣,將心定下來。他拆開上琴板與琴幹,開始調音。
他雖然看不見,卻非常熟悉鋼琴的結構,隨手彈了八小節,試試鋼琴的音準。
然後打開工具箱,將需要的工具一列排開,隨即用鮮紅色的止音布,熟練而有韻律地隔開每條琴弦,仔細地聽音叉的標準音,再用調音棒微微調起第一音。在上千個零件中,他彷彿能一覽無遺,不假思索地以反射動作,迅速找出有問題的琴弦,並加以調整。他的每個動作純熟而輕巧,整架鋼琴都在他的駕馭之中。
當小棣餵酷弟喝水時,姐姐卻被那八小節的琴音所吸引,悄悄回到琴房,坐在一旁,靜靜地看著調音師。
他看起來大約四十多歲,有一對細長的眼睛,眼珠子無神地在眼裡轉著。如果他不失明,那對眼睛必然炯炯有神;那麼,那張臉必定會更有魅力。他的身材就像一般中年人,並沒有什麼特別,不過他卻有一雙鋼琴家的手。女孩的視線隨著他那細長、有力、靈巧的手指在琴鍵上移動著。他的指法靈活而熟練,想必曾經下過一番功夫練琴吧!
他調好音後,隨意彈了一小段舒曼的曲子。雖然只是隨意彈奏,但他的神態和韻味卻宛如鋼琴大師一般,令女孩不由得看傻了眼。
更讓她佩服的是,經過調校之後,整架鋼琴的每個音都達到了完美境界,彷彿能穿透心脾,逗弄身體的每個細胞,讓人感到無比舒暢。這樣的音律才是一架好鋼琴所該有的,女孩不禁陶醉起來。
琴聲停止了,酷爸開始收拾工具,準備離開。女孩卻有意為難。
「如果你沒將舒曼那首曲子彈完,我怎麼知道你已經調好音了呢?」
「你為什麼不自己試試看呢?」
「剛才我已經說過,我討厭鋼琴,我討厭彈琴。」
「你說的不是實話。」酷爸毫不留情地說:「我感覺得出來,你對音樂很敏感,一定是有什麼其他的原因,使你感到厭惡,對不對?」
這個調音師眼睛雖然看不見,卻好像能透視人心似的。女孩對他越來越佩服,但他那一番話卻又讓她想起早上與媽媽的衝突,心情隨之沉落谷底。
酷爸將工具收拾好後,站在鋼琴前,心裡有些遲疑,最後還是開口問:「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女孩仍不想說,心想:「我為什麼要告訴你?」不料,弟弟卻代她說了,「我姐叫趙菲雪,今年十二歲。」
菲雪?酷爸覺得這個名字好耳熟,好像在哪兒聽過,卻又一下子想不起來。「你調好音了,可是我媽還沒回來,我們沒有錢可以給你,你還不能走。」菲雪仍想刁難他。
「我媽一定是以為小陳叔叔會來。」小棣接著說:「小陳叔叔是我們固定的調音師,他來的時候如果媽媽正巧不在,媽媽就會把錢匯到調音公司給他。」
「那麼也請你媽媽把錢匯到調音公司,我收得到的。」
酷爸喚來酷弟,替牠穿上導盲鞍,準備要離去。
這時電話鈴聲響起。
小棣接起電話,喂了一聲,便遞給菲雪。「姐,媽叫你聽電話。」
「我不想聽!」菲雪的語氣十分厭煩。
小棣對著話筒應了幾聲,然後對酷爸說:「我媽說,她會把錢匯到調音公司給你。」
接著,又轉向菲雪。「媽說,調好音後,你要繼續練琴,直到她回來為止。」
「練琴!練琴!一天到晚只會逼我練琴!我偏不練!」菲雪狂亂地叫著,抓起沙發上的抱枕,往鋼琴扔去。
從菲雪激烈的反應,可以預期一場風暴即將到來。酷爸心想,還是早點兒離開吧!他給了酷弟一個離去的指令,然後悄悄走了出去。
「姐,媽叫你來聽電話,快啊!」
菲雪衝過去,拿起話筒大吼著:「我偏不練!」然後將電話一掛。
不一會兒,電話鈴聲再度響起,小棣對著電話應了幾聲後,對菲雪說,「姐,媽說她現在就趕回來,要你立刻練琴。」
菲雪卻像沒聽見似的,往門口跑了出去。
小棣掛上電話,立刻追出去,「你要去哪裡?」
「不用你管。」
「可是,媽就要回來了……」
「別像管家婆似的,處處盯著我,行不行?」菲雪的語氣非常不耐煩。「姐,你不要這樣說嘛!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跟媽吵架,你就練一練嘛!」
「我偏不!」菲雪頭一揚,走進電梯裡。「她越逼我,我就越不練!」
「姐,媽也是為你好……」電梯門關上了,小棣急忙按下另一部電梯。
出電梯後,眼看著菲雪即將邁出大廈,小棣急忙喊著,「姐,等等我呀!」
菲雪停下腳步,「你煩不煩呀?」
「姐,我才不是要管你,只是,不想看你被罵……」
菲雪瞪著小棣,「你要真怕我挨罵,那簡單,你也去學琴呀!這樣媽就不會老盯著我,我也就不會天天挨罵啦!」
菲雪的這一番話,說得小棣不知如何回應,傻傻地望著她跑開。
小棣確實很想學琴,他跟媽媽提過好幾次,媽媽卻沒當一回事,一直將重心放在姐姐身上。媽媽嚴厲的態度,雖然也使得他害怕;但每當他看到媽媽和姐姐在一起彈琴時,那種特別而又親密的感情,使得他非常羨慕,也有一種被忽略的感覺。
既然菲雪不領情,那就算了。小棣原想轉身進屋去,卻發現酷爸與酷弟正緩慢地往巷子口走去,菲雪則悄悄跟在他們後面。酷弟到底是怎麼帶路的呢?一股好奇心自小棣心中湧出,於是也悄悄地跟上去。
轉出巷子後,人群與車陣熙來攘往,酷弟的腳步放慢許多,緩緩地帶著主人朝公車站走去。
「酷弟真厲害,居然知道主人要搭公車。」小棣嘖嘖稱奇。
他們悄悄地跟上酷爸,在公車站停了下來。
不一會兒,一輛公車靠站停住,酷爸向等車的民眾詢問過公車號碼後,立即給酷弟一個上車的指令。
酷弟引導主人準備上車,卻遭到司機阻攔,「狗不許上車。」
「牠是導盲犬,法律規定,牠有權搭乘任何交通工具的。」
司機發出嘲笑聲:「狗也有權搭公車?誰定的法律?聽都沒聽過。」
「我有交通部的文件,你看……」
「我說不行就是不行,就算你搬出憲法來也沒用,下去!下去!」
「砰」的一聲,車門立即關上,害得酷爸差點跌倒。
小棣好生氣,原想出聲替酷爸打抱不平,卻被菲雪及時摀住嘴,還受到譴責:「你想害我們被發現啊!」
午後的高溫已經夠讓人受不了,車子排出的廢氣,震耳欲聾的喇叭聲、引擎聲,此起彼落,更讓人煩躁不堪。陣陣的喘息聲不停地自酷弟口中冒出,酷爸好擔心牠會中暑,不時撫摸著牠的背部,並用話安撫牠,那樣子宛如在對待一個「人」似的,令小棣與菲雪感動不已。
不久後,又來了一班公車,司機還是不讓他們上車。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好幾次,酷爸好沮喪。他將文件放回口袋裡,拉了拉導盲鞍,給酷弟一個走回家的指令。酷弟於是引導著主人走進騎樓裡。
騎樓裡幾乎被摩托車和商家的貨品占滿了,簡直寸步難行。摩托車停放得很零亂,酷弟帶著主人小心翼翼地繞過來,穿過去,以免主人被摩托車把手勾到,或絆倒。當障礙物過多時,酷弟便停下腳步,思索著如何讓主人安然前進。有時候為了讓主人安全行走,牠寧可走出騎樓,頂著大太陽走在馬路上。
看酷弟在騎樓裡鑽進鑽出,走得這麼辛苦,小棣與菲雪好幾次差點出手幫助他們。可是為了怕暴露行蹤,他們還是忍了下來。
酷弟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將主人帶出騎樓,轉進一條巷子裡。這條巷子雖非行人專用道,車子明顯少了許多;不過,摩托車在巷子裡鑽進鑽出,菲雪與小棣不由得替他們捏了一把冷汗。
酷弟引導著主人走到一條叉路前,停住腳步等候主人指示。這時候,一輛摩托車突然從叉路衝出來,小棣與菲雪大叫一聲:「小心!」酷弟迅速閃向一旁,幸運地躲過摩托車的撞擊,但因事出突然,衝勁又大,害得酷爸摔倒在地,袋子裡的東西灑落一地。
酷弟急忙靠向主人,不停地用頭磨蹭主人的身體,好像在問主人有沒有受傷。
牠還發出嗚嗚叫聲,聲音中充滿了自責與焦慮。
路人紛紛圍過來,有的扶起酷爸,有的幫忙撿起掉落的東西,有的則責罵那個摩托車騎士。還有個好心的路人表示願意送酷爸回家。
看著酷爸與導盲犬逐漸遠離的背影,菲雪與小棣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導盲犬與主人間的深厚情誼,還有人情的溫暖,就像一塊含在口中的糖果,讓姐弟倆感到甜滋滋的。但一想到障礙重重的環境,卻不免又替酷爸與酷弟擔憂起來。
正當姐弟倆準備離開時,菲雪這才想起,忘了將剛才撿起的一個小袋子還給酷爸。打開一看,裡面竟全是錄音帶!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雲端裡的琴聲(三版)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雲端裡的琴聲(三版)
※跨越兩個時空,以樂音交織著親情、友情及人與動物之情的故事
盲人調音師酷爸在一次調音服務中,認識菲雪和小棣兄妹倆,酷爸彈琴時投入的神態,彷彿訴說著一個悲傷的故事,吸引著他們想一探究竟。從幾卷神祕的錄音帶中,菲雪和小棣有了十分意外的發現……
作者運用兩個不同的時空背景:一九七○年代的倫敦以及二○○二年代的臺北,交錯鋪陳出動人的故事;字裡行間飄揚著樂音,而樂音中則交織了親情、友情以及盲人與導盲犬之愛!
【本書關鍵字】
導盲犬、盲人、鋼琴、調音師、友情、生命教育
【本書資料】
國小中、高年級適讀
有注音
【本書特色】
1.為導盲犬、盲胞傾心撰寫人與動物之情的小說
曾四度榮獲金鼎獎的林滿秋是臺灣數一數二的重量級青少年小說作家,她以動人的故事描寫人與動物之情,希望透過本書讓社會更關懷導盲犬、視障者。
2.書末附有導盲犬介紹與問題討論
書末附錄以導盲犬的視角介紹,從導盲犬的訓練過程、人們對導盲犬的一些問題,到接近導盲犬的「五不」須知,讓讀者能更認識導盲犬。
得獎紀錄
★文化部優良讀物推介
作者簡介:
林滿秋
典型的獅子座,長髮及腰。
旅行、散步與寫作,是生命中不可缺的三大元素。
擁有兩個可愛的家,一個在臺灣汐止,一個在英國倫敦。
最喜歡的工作是為小朋友寫出動人的故事。
出版的作品有《隨身聽小孩》、《尋找尼可西》、《健身練習曲》、《一把蓮》、《錯別字殺手》、《作文怪獸我最愛》等(以上皆由小魯文化出版)。
章節試閱
導盲犬與調音師
酷爸在導盲犬的引導下,徐徐前進。
雖然才六月初,臺北的高溫卻已讓人招架不住。走在臺北街頭,宛如置身於烤箱中,簡直快把人烤焦了。汗水如水柱般從酷爸身上湧出,他卻顧不得擦拭,反而停下腳步,安撫引導他前進的夥伴。
從英國回到臺灣後,酷爸便發現他的夥伴對炎熱的天氣有些適應不良。牠步履遲緩,而且食欲不振。其實不光是導盲犬,就連他自己也有些受不了。英國夏天的平均溫度大約攝氏二十二度,一年難得有幾天會超過二十八度,他幾乎已經忘了臺灣是這麼熱。離開臺灣那年,他才十五歲。這二十多年來,...
酷爸在導盲犬的引導下,徐徐前進。
雖然才六月初,臺北的高溫卻已讓人招架不住。走在臺北街頭,宛如置身於烤箱中,簡直快把人烤焦了。汗水如水柱般從酷爸身上湧出,他卻顧不得擦拭,反而停下腳步,安撫引導他前進的夥伴。
從英國回到臺灣後,酷爸便發現他的夥伴對炎熱的天氣有些適應不良。牠步履遲緩,而且食欲不振。其實不光是導盲犬,就連他自己也有些受不了。英國夏天的平均溫度大約攝氏二十二度,一年難得有幾天會超過二十八度,他幾乎已經忘了臺灣是這麼熱。離開臺灣那年,他才十五歲。這二十多年來,...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盲人的第二對眼睛——導盲犬
文/林滿秋
臺灣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引進六隻導盲犬,不過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導盲犬,卻遭遇到大部分賣場、世貿展覽館等單位拒絕進入……
包括內政部、教育部、民航局等單位都發文要求不得拒絕導盲犬進入,但盲胞在搭乘公車時出示公文,司機仍置之不理……(聯合報,91.10.23)
又一則導盲犬的報導!
每當我看到這樣的報導,不由得為盲胞與導盲犬憤怒不平,也為我們這個社會的粗糙感到難過。
在國外,導盲犬不僅是獨立的生命體,更被視為盲胞肢體的延伸。只要「人」可以去的地方,...
文/林滿秋
臺灣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引進六隻導盲犬,不過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導盲犬,卻遭遇到大部分賣場、世貿展覽館等單位拒絕進入……
包括內政部、教育部、民航局等單位都發文要求不得拒絕導盲犬進入,但盲胞在搭乘公車時出示公文,司機仍置之不理……(聯合報,91.10.23)
又一則導盲犬的報導!
每當我看到這樣的報導,不由得為盲胞與導盲犬憤怒不平,也為我們這個社會的粗糙感到難過。
在國外,導盲犬不僅是獨立的生命體,更被視為盲胞肢體的延伸。只要「人」可以去的地方,...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孩子的心是最柔軟的,孩子的成長故事最美麗動人……
盲人的第二對眼睛——導盲犬
人物介紹
導盲犬與調音師
安妮,我是魯賓!
巧遇導盲犬
安妮,我聽到雲端裡的琴聲
導盲犬訓練計畫
安妮,給魯賓寫封信吧!
導盲犬相親記
安妮,我有一對新眼睛
導盲犬的祕密
安妮,我和黛兒去探險
導盲犬深夜求救
安妮,你到底在哪兒?
導盲犬尋親記
安妮,黛兒當媽媽了
導盲犬,不准進入
安妮,我必須留下來
導盲犬的安慰
安妮,真的是你嗎?
導盲犬音樂會
和我一起來認識導盲犬
問題討論
盲人的第二對眼睛——導盲犬
人物介紹
導盲犬與調音師
安妮,我是魯賓!
巧遇導盲犬
安妮,我聽到雲端裡的琴聲
導盲犬訓練計畫
安妮,給魯賓寫封信吧!
導盲犬相親記
安妮,我有一對新眼睛
導盲犬的祕密
安妮,我和黛兒去探險
導盲犬深夜求救
安妮,你到底在哪兒?
導盲犬尋親記
安妮,黛兒當媽媽了
導盲犬,不准進入
安妮,我必須留下來
導盲犬的安慰
安妮,真的是你嗎?
導盲犬音樂會
和我一起來認識導盲犬
問題討論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