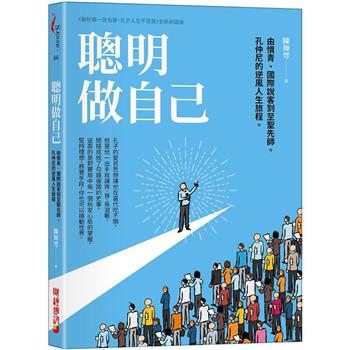中國最有故事張力的禁書!
吊莊是一個偏遠荒蠻的鄉村,這一年,奇童五斤降世,其父老莽魁中風不語,左鄰死牛,右舍瘋騾,怪事接二連三。老袁家對這個七子的降生大為驚駭,但是惟獨長子保英心中隱然,覺得七弟與自己有一種難以割捨的關聯。
莽魁年已古稀的婆姨,夏天裡總被一隻狐精纏身造孽。這個夏天來臨,棗胡老漢(浪跡的神秘人,可以被稱為先知)為其送了一串銅鈴懸掛於門簾之上,院中整日鈴聲搖曳。但有一夜可怕的結局終於來臨,原來造孽的並非狐精。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媾疫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10 |
二手中文書 |
$ 506 |
科幻/奇幻小說 |
$ 563 |
中文書 |
$ 563 |
小說 |
$ 576 |
華文驚悚/恐怖小說 |
$ 57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媾疫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亦夫
陝西扶風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在國家圖書館、文化部和中國工人出版社任職,現旅居日本。
著有長篇小說、散文隨筆集等十餘部,代表作「原欲三部曲」之《土街》、《媾疫》及《一樹謊花》。
長篇小說《無花果落地的聲響》獲中山文學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亦夫:「我的真實名字並不重要,讀我的作品吧,從《土街》到《媾疫》……」
亦夫
陝西扶風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在國家圖書館、文化部和中國工人出版社任職,現旅居日本。
著有長篇小說、散文隨筆集等十餘部,代表作「原欲三部曲」之《土街》、《媾疫》及《一樹謊花》。
長篇小說《無花果落地的聲響》獲中山文學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亦夫:「我的真實名字並不重要,讀我的作品吧,從《土街》到《媾疫》……」
序
序
你的聲音來自洞穴?
《媾疫》二十二萬餘字,是我在短短二十一天時間內草寫而就的長篇。熟悉我做事方式的朋友們,仍投來一片驚詫或疑惑的目光。
寫一部書對我而言,是壓在心頭的一塊黑色石頭。我無法忍受它帶來的漫長的沉重,只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卸掉重荷。已經過去的那二十一個日夜,我的靈魂漂游在吊莊袁家那座充斥著夢魘和災難的土院中,寢食不寧,晝夜難辨。我知道按每天一萬餘字的速度計算,這部小說必將在我能感覺到的時間內畫上最後一個句號。它是自己在流動,它會不容置疑地帶著我結束又一次充滿危險的精神之旅。三月十三日中午,我將沒有一處塗痕的草稿封進紙袋時,心中唯一的感覺是,我終於從惡夢中擺脫出來,又可以放縱地和朋友們胡侃亂聊、喝酒玩牌和到校園中去踢足球,又可以懶睡不起或坐在戶外明媚的陽光下慵倦地漫想往事或發呆。我知道我不會再去考慮有關《媾疫》的任何事情,即便付梓後也不會去翻看任何一頁,就如同《土街》一樣,它已經永遠地過去了。
寫故事是一個沉重的負荷,但同時也是一次在陌地的長旅。它使我輕易地體驗了我貧乏的閱歷難以體驗的人物和場景、情緒和心境,這是我何以無法將這種重荷徹底卸脫的原因。寫作是一種充滿危險的誘惑,我想我很難在忘記《媾疫》的同時,不再為新的誘惑所動心而又一次陷入這種精神苦役。但有一點我十分清醒,那就是在我能維持閒散、輕鬆甚至無聊的時候,我絕不願輕易地背起行囊--那支禿筆和一疊稿紙。
我的幾部長篇和中短篇小說,都是在沒有構思、沒有提綱,也不明確要表達什麼的狀況下,一筆而成的東西。厚厚的手稿沒有塗痕,乾淨得如同精心謄抄過一樣。我一次又一次拒絕了編輯及書商關於修改的要求,但這並非是因為自己認為作品已臻完美。恰恰相反,我的劣習使作品粗陋不堪,無法達到這種題材應有的力度。我之所以固執己見,是我的性格使然。修改會使我重新走入潮濕陰暗的洞穴,會使我重新經歷那夢魘般的場景。因為我知道,無論土街還是吊莊,無論掌才還是莽魁,他們不是出自我的想像,他們是存在著的。他們存在於歷史或者未來,存在於陽世或者陰界,存在於人類意識的荒野之中。而我,已無力再次承受這種存在對於我靈魂造成的重壓。
在京十年,從北大到北圖,從北圖到文化部機關,從機關又到了一家出版社的編輯部,我像個患了夢遊症的病人,莫名其妙地走進了今天這種與過去設想相去甚遠的生活。一根神祕的纖繩牽引著我,使我在這樣年輕的年齡,也許過早地注定了以後的模式,這一點讓人悲哀。想來想去,自己無論如何都不會是個為了什麼目標而義無反顧的人。過去我也見過一些醉心寫作的人,他們拋家捨業,蓬頭垢面地背著厚厚的書稿來京找發表之門,言語激奮,心境傲遠,有的甚至徒步千里,衣食無著。他們總讓我想起印度那些苦難的聖僧,心中泛起一絲難言的情緒,不知道是敬仰還是同情。其實,精神的功名和物欲的滿足,都是讓人企慕的好事。我並非能超脫它的誘惑,但我卻無法如此執著、如此堅韌和如此充滿能包容一切苦難的寬厚。
男人們為了標榜自己更是個男人,便去炫耀自己滿身的創傷和疤痕,便去尋找甚至刻意製造各種各樣的艱辛和磨難。也許我並不算一個十分脆弱的人,但如果能讓我輕鬆地擺脫這一切,我寧願別人嘲笑我是個懦夫。過去那個貧困得幾乎難以維持的家和父母細微得近乎瑣碎的疼愛,使我的性格中充滿了對毫無個性色彩的世俗溫情的嚮往。這也許會妨礙我變得超脫和傲遠,但卻使我在清醒的時候,能永遠地保持朗晴的心境,而不會總是有那麼多的神聖感、使命感和無休無止的失落與孤獨。如果今生能活得輕鬆隨意,我現在是個庸人,以後也願意永遠是個庸人。比起那些或是蓄著凌亂的長髮、或是一味地憤世嫉俗、或是永遠想以反叛常情而標榜個性的所謂搞藝術或寫作的人們,我更喜歡在田間勞作的農人,更喜歡於摩肩接踵的市場上,反復比較著菜肉價錢的千萬個普通的平民。他們真實地貼近於自己的生命,貼近於我的生命,使我永遠感到自己沒有被遺棄。
大概從中學時代起,我就一直在幻想這樣的生活:自己有一間不大卻完全獨立的房子,屋內除了一些散亂的書籍外,便只有從闊大的窗戶中投射進來的溫暖的陽光。我隨意坐在地板上或一隻深得足以將我陷進去的沙發中,一個晌午一個晌午地漫想那許許多多或近或遠的事……十多年過去了,而我終究還是不能擁有這樣的空間、這樣的心態。寫作《媾疫》期間,我借住的原機關那間六平米的房子已經期滿。每日回去,門上都貼滿了催我搬離的各種通知和告示。但是春天來了,這一切都不足以破壞我溫暖的心境。我知道眼下最緊要的事是四處託人租房,並反復到機關去磨嘴皮以求十天半月的寬限。但這些事在我心中卻如同與己無關一般,總也難以讓自己方寸全亂。
春天已經清晰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柳樹、楊樹已經綻出新綠,各色耐不得寂寞的早春花兒已遍地開放。明媚的陽光照射下來,空氣中到處流蕩著一股令人酥癢的氣息。《媾疫》的惡夢已經醒來,我整日走在這個清晨般清新美麗的季節裡,想起過去苦難卻讓人懷戀的鄉居的日子,想起或近或遠的親人們,心中充滿了纏綿的溫情和世俗的快樂。
春天真好,活著真好。
亦夫
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於六鋪炕
你的聲音來自洞穴?
《媾疫》二十二萬餘字,是我在短短二十一天時間內草寫而就的長篇。熟悉我做事方式的朋友們,仍投來一片驚詫或疑惑的目光。
寫一部書對我而言,是壓在心頭的一塊黑色石頭。我無法忍受它帶來的漫長的沉重,只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卸掉重荷。已經過去的那二十一個日夜,我的靈魂漂游在吊莊袁家那座充斥著夢魘和災難的土院中,寢食不寧,晝夜難辨。我知道按每天一萬餘字的速度計算,這部小說必將在我能感覺到的時間內畫上最後一個句號。它是自己在流動,它會不容置疑地帶著我結束又一次充滿危險的精神之旅。三月十三日中午,我將沒有一處塗痕的草稿封進紙袋時,心中唯一的感覺是,我終於從惡夢中擺脫出來,又可以放縱地和朋友們胡侃亂聊、喝酒玩牌和到校園中去踢足球,又可以懶睡不起或坐在戶外明媚的陽光下慵倦地漫想往事或發呆。我知道我不會再去考慮有關《媾疫》的任何事情,即便付梓後也不會去翻看任何一頁,就如同《土街》一樣,它已經永遠地過去了。
寫故事是一個沉重的負荷,但同時也是一次在陌地的長旅。它使我輕易地體驗了我貧乏的閱歷難以體驗的人物和場景、情緒和心境,這是我何以無法將這種重荷徹底卸脫的原因。寫作是一種充滿危險的誘惑,我想我很難在忘記《媾疫》的同時,不再為新的誘惑所動心而又一次陷入這種精神苦役。但有一點我十分清醒,那就是在我能維持閒散、輕鬆甚至無聊的時候,我絕不願輕易地背起行囊--那支禿筆和一疊稿紙。
我的幾部長篇和中短篇小說,都是在沒有構思、沒有提綱,也不明確要表達什麼的狀況下,一筆而成的東西。厚厚的手稿沒有塗痕,乾淨得如同精心謄抄過一樣。我一次又一次拒絕了編輯及書商關於修改的要求,但這並非是因為自己認為作品已臻完美。恰恰相反,我的劣習使作品粗陋不堪,無法達到這種題材應有的力度。我之所以固執己見,是我的性格使然。修改會使我重新走入潮濕陰暗的洞穴,會使我重新經歷那夢魘般的場景。因為我知道,無論土街還是吊莊,無論掌才還是莽魁,他們不是出自我的想像,他們是存在著的。他們存在於歷史或者未來,存在於陽世或者陰界,存在於人類意識的荒野之中。而我,已無力再次承受這種存在對於我靈魂造成的重壓。
在京十年,從北大到北圖,從北圖到文化部機關,從機關又到了一家出版社的編輯部,我像個患了夢遊症的病人,莫名其妙地走進了今天這種與過去設想相去甚遠的生活。一根神祕的纖繩牽引著我,使我在這樣年輕的年齡,也許過早地注定了以後的模式,這一點讓人悲哀。想來想去,自己無論如何都不會是個為了什麼目標而義無反顧的人。過去我也見過一些醉心寫作的人,他們拋家捨業,蓬頭垢面地背著厚厚的書稿來京找發表之門,言語激奮,心境傲遠,有的甚至徒步千里,衣食無著。他們總讓我想起印度那些苦難的聖僧,心中泛起一絲難言的情緒,不知道是敬仰還是同情。其實,精神的功名和物欲的滿足,都是讓人企慕的好事。我並非能超脫它的誘惑,但我卻無法如此執著、如此堅韌和如此充滿能包容一切苦難的寬厚。
男人們為了標榜自己更是個男人,便去炫耀自己滿身的創傷和疤痕,便去尋找甚至刻意製造各種各樣的艱辛和磨難。也許我並不算一個十分脆弱的人,但如果能讓我輕鬆地擺脫這一切,我寧願別人嘲笑我是個懦夫。過去那個貧困得幾乎難以維持的家和父母細微得近乎瑣碎的疼愛,使我的性格中充滿了對毫無個性色彩的世俗溫情的嚮往。這也許會妨礙我變得超脫和傲遠,但卻使我在清醒的時候,能永遠地保持朗晴的心境,而不會總是有那麼多的神聖感、使命感和無休無止的失落與孤獨。如果今生能活得輕鬆隨意,我現在是個庸人,以後也願意永遠是個庸人。比起那些或是蓄著凌亂的長髮、或是一味地憤世嫉俗、或是永遠想以反叛常情而標榜個性的所謂搞藝術或寫作的人們,我更喜歡在田間勞作的農人,更喜歡於摩肩接踵的市場上,反復比較著菜肉價錢的千萬個普通的平民。他們真實地貼近於自己的生命,貼近於我的生命,使我永遠感到自己沒有被遺棄。
大概從中學時代起,我就一直在幻想這樣的生活:自己有一間不大卻完全獨立的房子,屋內除了一些散亂的書籍外,便只有從闊大的窗戶中投射進來的溫暖的陽光。我隨意坐在地板上或一隻深得足以將我陷進去的沙發中,一個晌午一個晌午地漫想那許許多多或近或遠的事……十多年過去了,而我終究還是不能擁有這樣的空間、這樣的心態。寫作《媾疫》期間,我借住的原機關那間六平米的房子已經期滿。每日回去,門上都貼滿了催我搬離的各種通知和告示。但是春天來了,這一切都不足以破壞我溫暖的心境。我知道眼下最緊要的事是四處託人租房,並反復到機關去磨嘴皮以求十天半月的寬限。但這些事在我心中卻如同與己無關一般,總也難以讓自己方寸全亂。
春天已經清晰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柳樹、楊樹已經綻出新綠,各色耐不得寂寞的早春花兒已遍地開放。明媚的陽光照射下來,空氣中到處流蕩著一股令人酥癢的氣息。《媾疫》的惡夢已經醒來,我整日走在這個清晨般清新美麗的季節裡,想起過去苦難卻讓人懷戀的鄉居的日子,想起或近或遠的親人們,心中充滿了纏綿的溫情和世俗的快樂。
春天真好,活著真好。
亦夫
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於六鋪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