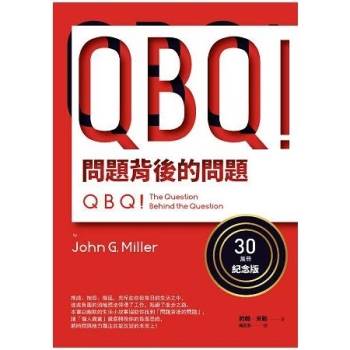前言
2022年10月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上,陳亞蘭以飾演嘉慶君遊台灣的男主角而獲獎,之後的新聞不是聚焦於陳亞蘭以女性身分得到視帝頭銜的跨性別意義,就是許多歷史學者批評嘉慶君根本沒來過台灣,這種戲劇誤導觀眾。這些學者似乎忘了,嘉慶君遊台灣本身是富有悠久歷史且眾多版本的民間傳說,且過去數十年來,多次改編成歌仔戲與電視連續劇。而此次得獎的電視劇,片尾曲由陳亞蘭及曹雅蘭穿著當代服裝合唱,歌詞內容是當代台灣的庶民美食,如「珍奶與雞排」。因此,此劇不是一般認知裡的歷史劇,而是有自身敘事傳統的民間故事、歌仔戲、電視劇之綜合。批評者的看法,顯然呈現了對「文化史」本身的無知或漠視。文化本身,包括經由敘事形成的文化,它就構成了歷史。同樣地,歷史小說經由其多變的敘事設計,本身就是書寫的歷史。
著名歷史哲學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就指出,「每個新的一代都必須以自己的方式重寫歷史;每一位新的歷史學家不滿足於對老的問題做出新的回答,就必須修改這些問題本身。」一般民眾對歷史小說的看法,可能很在意作者在史料上的正確度,或是走到另一個極端,忽視歷史小說的虛構性,把小說中的人物與情節都看成是真的。本書認為歷史小說乃作家以史料為基礎而提出的虛構與想像。虛構並非是假的,而必須利基於史料而寫出人物的內心情感,因之歷史小說具備人性與社會氛圍的真實性。上述柯林伍德的引文,不只適用於史學研究,對歷史小說的研究也同樣適用。對於上一世紀的歷史小說研究而言,其關切議題是:台灣各種外來政權的殖民主義,以及台灣人如何反殖民。面對二十一世紀以來的當代台灣歷史小說,筆者提
出的問題是:各種不同族群與性別的作家如何利用歷史小說來思考多元文化下的國族認同?小說家如何使用不同的敘事方式,讓外來者與本地人、不同背景、不同族群與性別身分的人物,展開對話?國族認同恆常處於流動與變化,並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其他身分—如族群與性別—互相協商。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雙重力量下,台灣作家經由歷史小說的各種不同背景的人,思索中國、西洋、日本、原住民之間的互動、混成、轉化。
本書的主題是「歷史小說」,既然稱為「歷史小說」,那麼比起民間傳說或是電視歌仔戲,是否應該用更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歷史小說的歷史正確度?筆者的想法相反,筆者維持第一段的主張,敘事與書寫本身就構成了歷史。例如:文學史、電影史、美術史、社會運動史。那為什麼文學史只與文學有關,台灣歷史的書籍不必提到文學,也不必提到美術?社會運動也許會出現在主流歷史書寫中,但文學、藝術、電影很難在台灣通史中出現。到底是什麼構成了歷史?歷史小說是否由兩項成分共存而不必考量二者的互相滲透、互相影響?換言之,我們通常認為歷史小說就是由「真實」的歷史與「虛構」的小說兩個成分構成。這種認知又導向另一個偏見:真實的歷史就是政權變遷、軍事、公共治理等公領域的事物:而作家在發揮虛構與想像時,經常以私領域為想像對象。特別是愛情故事,常被用來作為增加閱讀趣味的敘事策略。我們是否曾思考過,歷史小說可以對政權交替增添虛構與想像,而人民的情感狀態、屬於遙遠時代的親子關係與夫妻關係,則需要調度大量史料來考據?從作者、讀者、到研究者,有些人認為歷史由政治構成、需要考據,而愛情與私領域則可以任由作者與讀者馳騁其想像力。其實,情慾與親密關係也會隨時代變遷,甚至是引領時代變遷的力量。歷史小說的魅力,就在於公私領域交錯、虛實共構所產生的「更具真實力量的虛構」。
自國家文學館成立後,推出金典獎,國藝會也有長篇小說補助,我們可發現近年來在台灣,長篇小說幾乎可說大部分為歷史小說,其餘則是新鄉土或後鄉土小說。台灣的歷史小說作者依其性別、族群身分、世代、個人寫作生涯的際遇,一方面展現各自特色,卻又有部分重疊與共通處。歷史小說出版數目很多,此次專書寫作計畫,並不是一本全面介紹歷史小說的書,而是依據筆者的問題意識展開對特定小說作品的探討。這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意識就是,台灣當代歷史小說為何喜愛採用後設書寫?這些作家採用真實存在的日記與過去出版過的歷史、地理、旅遊素材,或是虛構書信讓讀者乍看下以為是真的書信,而其最終目的,則是讓讀者玩味虛實交錯下如何重新界定歷史、重新界定家族史、地方史、個人自我定位,並以此找尋某種認同—國族認同是其中一種,但不是所有歷史小說都在探討國族認同,又或者是以解構國族認同來建立另一種認同。這些對歷史再現的書寫,呈現作者處於全球化脈絡下,對「地方」提出更嶄新而細膩的描繪。
本書所欲探究的問題如下:
首先,筆者關切當代歷史小說為何偏好後設書寫?作者使用檔案、日記、書信、百年前的遊記,形成互文性,這如何影響我們對歷史的認知?例如謝裕民作品「安汶假期」,將敘事者我的旅遊與晚清遊記「南洋述遇」互相參照,似乎現在與過去類似,讓敘事者我感到自己的旅遊經驗已經被文本化,而非自己親自的體驗。
其次, 台灣的歷史小說似乎應該由台灣人的視角來書寫,所謂「台灣人」包含漢人與原住民。但是我們常可看到作者採取殖民者的觀點來敘事。例如曹銘宗以西班牙據有基隆為主題的《艾爾摩沙的瑪利亞》,是由西班牙軍官若望(虛構人物)的角度來展開故事。平路以荷治時期為題材的小說《婆娑之島》,則由荷蘭總督揆一(真實人物)的角度來鋪陳。如何評估這種使用殖民者為發言位置的書寫策略?使用「自我東方化」的批評固然有理,但無助於開發對文本更深入的詮釋,反而封閉了研究者與作者及其作品對話的可能性。
第三個問題是,台灣歷史小說使用跨種族互動固然為歷史事實之呈現,因為台灣歷史舞台上出現原住民、漢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等多重政權與多重種族的的交涉,而作者以跨種族羅曼史來呈現,讓我們對歷史想像增添了公私領域的互動,同時也激發我們省思過去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二元對立的反抗史觀,並認識親密關係與情慾本身就構成了歷史。但在某些小說如《艾爾摩沙瑪利亞》與《婆娑之島》,親密關係並未置放於歷史脈絡,而巴代與施叔青則可以將女性人物與兩性關係置放在歷史脈絡下來看。
由以上三個問題,呈現出從對立到對話的過程。曹銘宗、平路、施叔青等人採取殖民者觀視位置時,呈現對作家對他者的欲望。作家從台灣人的自我出發,想像西班牙、荷蘭、日本他者的處境,進而打破自我與他者的對立,也就是消解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與壓迫/被壓迫關係,從而製造自我與他者對話的可能性,讓他者得以自我反思殖民主義,進而贖回歷史的惡業,重新詮釋過去而能建立過去與現在的和解。
本書以「華語語系研究」為切入點,思考十七世紀以來離散華人來到台灣後,與殖民者及原住民的互動,以及對中國性的質疑與解構。《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由作者吳濁流在二戰末期書寫日本殖民以來台灣社會的變化。在他書寫當下,這部小說未必是歷史小說,但由於戰後的出版至今超過半世紀,書中所寫的殖民時期與二戰有助於我們對此段歷史的了解,因此我策略性地將之視為歷史小說。至於駱以軍的《西夏旅館》一書,通常也不會被視為歷史小說,但是駱以軍挪用十一世紀西夏歷史來喻說外省人處境,也具有另類歷史書寫。為了呼應華語語系的研究視野與比較方法,本書包括新加坡作家謝裕民的中篇小說〈安汶假期〉,此書同樣以後設書寫來質疑中國性並協商新加坡認同的可能性。本書兩個附錄,皆來自史書美教授的啟發,針對華語語系研究從事跨界思考。
本書各章並非以內容之歷史順序排排,而是分成三篇,每篇各有一個主題。第一篇主題是:地方史與世界史;第二篇是:解構與重構中國性;第三篇是:移動與認同的協商。本書每章都是歷年國科會研究成果,在此感謝國科會提供贊助。歷任助理王俐茹、邱比特、黃茂善、翁克勳、盧子樵協助校對,並在我文思枯竭時與我對話,激勵我持續下去。沒有助理的協助,這些論文無法以完整格式呈現。其中,黃茂善對我的協助特別多,我們也經常討論華語語系的議題。一本書的完成,必須依靠眾人的協助,而我的家人提供我充裕的寫作空間—物質上的與精神上的空間,也是我身為學者的福分。這些年來任教於台師大台文系,這裡的教學與研究環境,使我能結合教學內容與歷史小說之研究。希望本書經由歷史小說的分析,也能讓讀者回述自己的生命史,並與台灣社會對話。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是誰在說故事?當代台灣歷史小說的性別與族群的圖書 |
 |
是誰在說故事?當代台灣歷史小說的性別與族群 作者:林芳玫 出版社: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11-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40 |
中文書 |
$ 440 |
台灣研究 |
$ 450 |
華文文學研究 |
$ 450 |
文化評論 |
$ 47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是誰在說故事?當代台灣歷史小說的性別與族群
台灣歷經重層殖民史,經由西班牙、荷蘭、日本殖民,當代台灣歷史小說企圖經由跨文化角
度重新審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互動關係。本書從分析不同作家的敘事技巧,探討歷史小說中的性別與族群關係,並分析歷史小說如何成為建構與解構國族認同的論述場域。
作者簡介:
林芳玫
現職:台師大台文系教授
學歷:台大外文系學士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
專長:文學社會學與文化研究
專著:曾出版學術專書《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女性與媒體再現》、《永遠在他方》,並出版散文集 《權力與美麗》、《跨界之旅》,以及中篇小說《達文西亂碼》。
教學與研究領域:文化認同與國族主義、台灣歷史小說、性別與國族、文學社會學、台語電影。
章節試閱
前言
2022年10月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上,陳亞蘭以飾演嘉慶君遊台灣的男主角而獲獎,之後的新聞不是聚焦於陳亞蘭以女性身分得到視帝頭銜的跨性別意義,就是許多歷史學者批評嘉慶君根本沒來過台灣,這種戲劇誤導觀眾。這些學者似乎忘了,嘉慶君遊台灣本身是富有悠久歷史且眾多版本的民間傳說,且過去數十年來,多次改編成歌仔戲與電視連續劇。而此次得獎的電視劇,片尾曲由陳亞蘭及曹雅蘭穿著當代服裝合唱,歌詞內容是當代台灣的庶民美食,如「珍奶與雞排」。因此,此劇不是一般認知裡的歷史劇,而是有自身敘事傳統的民間故事、歌仔戲、...
2022年10月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上,陳亞蘭以飾演嘉慶君遊台灣的男主角而獲獎,之後的新聞不是聚焦於陳亞蘭以女性身分得到視帝頭銜的跨性別意義,就是許多歷史學者批評嘉慶君根本沒來過台灣,這種戲劇誤導觀眾。這些學者似乎忘了,嘉慶君遊台灣本身是富有悠久歷史且眾多版本的民間傳說,且過去數十年來,多次改編成歌仔戲與電視連續劇。而此次得獎的電視劇,片尾曲由陳亞蘭及曹雅蘭穿著當代服裝合唱,歌詞內容是當代台灣的庶民美食,如「珍奶與雞排」。因此,此劇不是一般認知裡的歷史劇,而是有自身敘事傳統的民間故事、歌仔戲、...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05
第一篇 地方史與世界史/11
第一章 《艾爾摩沙的瑪利亞》:書信體、擬仿殖民者、反思殖民…12
第二章 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36
第二篇 解構與重構中國性/79
第三章 《邊緣人三部曲》與另類鄉土文學:從離散到在地認同…80
第四章 《西夏旅館》與台灣人悖論:從「身為中國人」到「變成(不是)台灣人」…115
第三篇 移動與認同協商/145
第五章 沈默之聲:從華語語系研究觀點看「台灣三部曲」的發言主體…146
第六章 性別化的現代性體驗:《亞細亞的孤兒》及其恥辱...
第一篇 地方史與世界史/11
第一章 《艾爾摩沙的瑪利亞》:書信體、擬仿殖民者、反思殖民…12
第二章 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36
第二篇 解構與重構中國性/79
第三章 《邊緣人三部曲》與另類鄉土文學:從離散到在地認同…80
第四章 《西夏旅館》與台灣人悖論:從「身為中國人」到「變成(不是)台灣人」…115
第三篇 移動與認同協商/145
第五章 沈默之聲:從華語語系研究觀點看「台灣三部曲」的發言主體…146
第六章 性別化的現代性體驗:《亞細亞的孤兒》及其恥辱...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