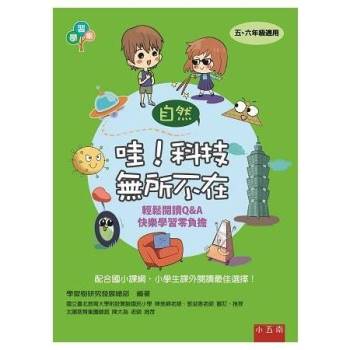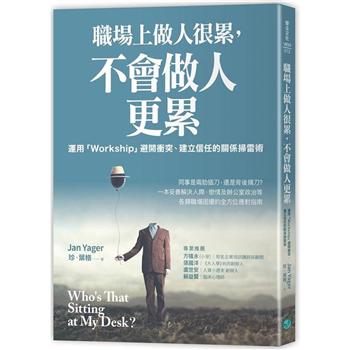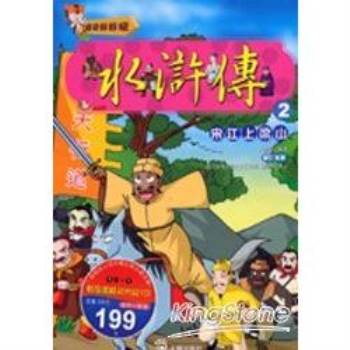監獄醫師才能告訴你的──監獄診間故事。
收容人詐病、藥物成癮、吞食異物…
在這個地方早已不足為奇,
然而,在大韓民國這塊土地上,
守護他們健康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監獄。
大多數醫學院生畢業後,壓根不會想到矯正機關(看守所和監獄)服務,作者崔世鎭卻選擇這裡作為他醫師生涯的第一站,成為1500名收容人的唯一醫生,將在監獄裡看到的一切記錄下來:
· 在這裡,詐病幾乎天天上演。為了多領藥、為了逃避勞役、為了搬到其他舍房、為了戒護外醫……我也因此練就了一身詐病判定功夫。
· 身上別著藍色號碼牌的,就是「煙毒犯」。他們要的不只是毒品,還有各式各樣的藥物。為了把藥拿到手,甚至威脅醫生也在所不惜。
· 為了達到目的,有些收容人會自殘、吞食異物。照了X光之後,我完全想不透他到底是怎麼把這麼大一顆警報器塞進喉嚨裡的。
然而監獄裡,也經常發生這樣的事:
· 許多人幼年時都沒接種過B型肝炎疫苗,他們成為犯罪者的機率之高,幾乎可以說是「天生的」。
· 因為自離開監獄起,醫藥費就不再由監獄負擔,許多收容人縱使已病入膏肓,但礙於經濟壓力,也只能等待死亡。
· 許多毒品成癮患者,多半都是生長在惡劣環境,從小開始跟著身邊的人吸食強力膠。監獄官們說:他們被關一次、兩次、三次,如果好一陣子沒再進來,不會認為他們戒毒成功,反而會覺得他們應該是自殺了。
透過書裡的故事,我們或許可以思考:
究竟是社會的灰色地帶催生了犯罪者,還是因為人性本惡?
「報應主義」真的能讓社會更好嗎?
「公共醫療」該如何發揮最大實質效益?
監獄這個地方,自成一個世界,是社會的縮影,
裡面的人,真的生病了。
本書特色
● 帶領讀者站在第一線,以醫師角度看收容人與其背後故事。其中,醫師該如何不受情感影響、保持專業,發人省思。
● 不僅點出監獄醫療的問題,也具體舉出他國矯正機關的方式、作者在體制內所做的新嘗試,亦能提供台灣借鏡。
● 作者崔世鎭:「如果因為對方是犯罪者,就無視他們的醫療需求,不僅是侵害人權,也會醞釀出更多的被害者。」引領你我一同思考個人與社會的健康是如何相互影響,又該如何降低再犯率,甚至預防犯罪,打造更安全健康的社會。
好評推薦
朱剛勇|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貧窮人的台北策展人
林啓嵐|羅東聖母醫院主治醫師、法務部頒定法醫師
林麗珊|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劉淑瓊|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戴伸峰|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哇賽心理學與鏡好聽合作主持人
謝松善(阿善師)|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主任
(依首字筆畫排序)
目前國內尚無以醫學的角度介紹監所的專書。日月文化出版社計畫將《我是醫生,在監獄上班》譯成繁體中文版並介紹給國內的讀者和社會。讓社會大眾對同在一個社會但被隔絕的監所收容人之醫療與生活能進一步瞭解;同時本書也是法律、獄政、警政、醫療相關人員體驗社會角落、豐富職業文化內涵的一本好書!──林啓嵐|羅東聖母醫院主治醫師、法務部頒定法醫師
杜斯妥也夫斯基說:「評價一個社會,不要看它如何對待良民,而是看它如何對待罪犯。」我們應該審慎評估罪與罰的對應與意義,悲憫社會邊緣人在監獄矯正與醫療的困境。──林麗珊|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健康監所」是國際趨勢。受刑人被剝奪人身自由是刑罰手段,但健康既是基本人權也牽動健保支出。本書從監所醫師視角,探討受刑人健康問題的社會成因與公衛風險,值得臺灣借鑑。──劉淑瓊|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