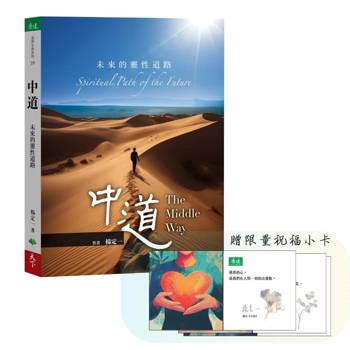年逾三十仍未婚的王秀安,情場工作兩失意的她正值人生的關卡。不料,一朝COVID-19疫情襲來,打亂了所有的步調,她原訂的人生計畫也被無情粉碎,意外讓她不得不宅居在家將近三年之久。人類與病毒的戰役方興未艾,世界另一端,人類之間交戰的烽火又悄悄點燃,俄羅斯大軍壓境烏克蘭,戰爭的波盪擴及全世界。
病毒蔓延,硝煙漫天,焦慮、不安瀰漫在秀安的生活中。正處於生命轉彎之處,遠有役情的陰影,近有疫情的威脅雙雙夾殺,徬徨不已的她,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疫情不可能一夕間停止的,但我要為此放棄生活裡所有的樂趣嗎?我要讓人生停滯在這裡打轉嗎?世界上又有誰能預料明天會怎樣?沒有!就算要頹廢,我也要在活力中頹廢!」
本書特色
★ 疫情、戰爭接踵而來,面對一團亂的生活、走樣的人生步調,徬徨中找回信心
★ 處於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30歲」必讀,一本專屬迷茫世代的成長小說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疫情蔓漫徬徨時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疫情蔓漫徬徨時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劉玉梅
◆ 1950年出生於彰化縣二林鎮。
◆ 1969年彰化女中高中部畢業。
◆ 1973年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
出生於一個偏遠貧困的小農村;小時候沒有米吃,希望世界有很多米,人類永遠不必挨餓,故以「多米」為筆名。大學畢業後一路從事國際貿易,直至2014年底退休。數十年的職場經驗,養成隨時觀察國際社會脈動的習慣;書寫的故事,大多是關於周遭市井小民的平凡生活,反映台灣社會變動的歷史軌跡,但也可以看見書中的人事物與世界的連結。已出版作品:《背著書包上田去》(2010年出版,2013年再版)、《漫步市井聽故事》(2019年出版)
劉玉梅
◆ 1950年出生於彰化縣二林鎮。
◆ 1969年彰化女中高中部畢業。
◆ 1973年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
出生於一個偏遠貧困的小農村;小時候沒有米吃,希望世界有很多米,人類永遠不必挨餓,故以「多米」為筆名。大學畢業後一路從事國際貿易,直至2014年底退休。數十年的職場經驗,養成隨時觀察國際社會脈動的習慣;書寫的故事,大多是關於周遭市井小民的平凡生活,反映台灣社會變動的歷史軌跡,但也可以看見書中的人事物與世界的連結。已出版作品:《背著書包上田去》(2010年出版,2013年再版)、《漫步市井聽故事》(201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