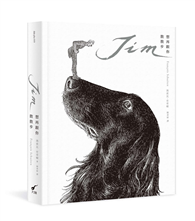序
濃濃小說味的散文
路寒袖
記不得何時認識陳漱意了,總之,鐵定在九○年前後,彼時我任職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那時陣台灣紙媒雖已巔峰將盡,但仍散發著輝煌盛世的餘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可是數一數二的副刊,與另一家競爭激烈的報社並稱「兩大報」。既是眾望所歸的副刊園地,稿件自然來自全球各地的華文作家,我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認識陳漱意的,而且一定是她的作品好,我才寫信給她,想必是我們頻率相通,很快的就互認好友。
不久時報舉辦第一屆百萬小說獎,副刊界此一文壇大事,我特地跟她通風報信,並軟硬兼施要她無論如何絕不可缺席這歷史性的一刻,陳漱意的筆又快又好,不僅投件參加,還獲得佳作獎,尤有甚者,後來我才知道,那獲獎之作《蝴蝶自由飛》,竟是她的首部長篇,果真,高手一出手便知有無。
算算我們的相識也超過三十年了,三十年來,我始終認定她是小說家陳漱意,可這次她卻寄來一本散文集,書名《口罩與接吻》,幸好有這本散文集,我才有機會一窺她在紐約的生活。
若要一言以蔽之,陳漱意屬人生勝利組,日子過得幸福美滿,先生事業有成,對她百依百順,三個優秀的兒子大山、大川、大印,各自獨立發展,尤其老大大山法學院畢業後,順利當上紐約的檢察官,韓裔的大媳婦艾琳更選上了州議員。媽媽雖然住西岸洛杉磯有點遠,但起碼同在美國。有「歐元之父」美稱的一九九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孟德爾教授是她多年的好友。
如此幸福的陳漱意是否該知足謝天?偏偏她的內心又躲著一個隨時騷動的文學靈魂,必須書寫再書寫才得以馴服它,否則豪宅、錦衣、美食一切的一切盡是夢幻泡影,不讓她寫,陳漱意可要跟上帝掀桌的,所有世俗令人欣羡的條件,無非就只為陳漱意舖設一張寫作的書桌。
《口罩與接吻》共四輯,分別是《在紐約的日子》、《愛恨情仇的日子》、《想吃的日子》、《出走的日子》,四輯皆以「日子」為名,其實就是陳漱意在美國的生活留影,再依內容題材分類之。
第一輯《在紐約的日子》,主要的篇章〈紐約避疫雜記〉、〈口罩與接吻〉、〈停止仇恨亞裔〉都圍繞著近年來的新冠疫情,陳漱意忠實的點出了紐約搶購、屯積食物的驚惶。住曼哈頓的小兒子大印不幸染疫,她竟衝去兒子家為他燒煮潤喉、潤肺的亞洲梨子水、香菜水,母愛果真無敵。
陳漱意在〈紐約避疫雜記〉一文開宗明義就說:眼前面對的戰爭,不是敵人轟炸機的掃射,不是隨時會從天上落下來的炸彈,很詭異的是一個握手,一個擁抱,一句寒暄,人跟人跟物跟空氣,最起碼的接觸—敵人是這樣陰森的借體還魂,我們正生活在一場無所不在卻無從捉摸,虛虛實實的慘烈戰爭之中。
誠然,新冠病毐是無形的超級炸彈,炸亂了世界原來的秩序,炸斷了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網絡,也炸出了廿一世紀人性的美麗與醜陋。
第二輯《愛恨情仇的日子》除了好友貝蒂(〈我也有憂鬱症〉)的女兒為憂鬱症所苦而自殺,令人感傷之外,其餘篇章都還溫馨,〈夜宴〉約略可見紐約上流社會的豪奢應酬。〈參加合唱團的日子〉是到紐約上城百老匯大道上的波多黎各大學參加合唱團,學唱拉丁文歌曲,還參與演出,想必是難以忘懷的經驗。
第三輯《想吃的日子》毫無疑問就是一輯飲食文學,〈幻想美食〉強調的是美食不光只是味蕾、胃口、食材的問題,最關鍵的提味乃是心理的想像,所以陳漱意下了一個結論:「所謂人間美味不是吃出來,而是幻想出來的。」〈早餐吃什麼〉滿有趣的一篇,洋洋灑灑寫了美國生活的諸多早餐,或許陳漱意下次返台,不妨重新品味一下台灣的早餐。因為台灣的早餐可是被公認為全世界第一名,豐富、多元、美味、銷魂,到時,漱意賢兄(她習慣喚我賢弟,自稱愚兄),妳就知道要回紐約有多難了。
第四輯《出走的日子》則是旅行文學,〈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從蘇菲亞到伊斯坦堡〉絕對是人人欣羡的行程,借由陳漱意生動的描述,讀者彷彿也身歷其境。
陳漱意的長子大山在紐約一家武術館學螳螂拳,每年耶誕節跟新年期間會出國練拳,陳漱意隨行過兩次,〈那日,在瀑布下〉、〈武學之旅〉記錄了委內瑞拉的馬里達之行,大山因身體微恙,險些沉溺於天使瀑布下的水潭,是一趟有驚無險的旅程,也讓讀者再次看到陳漱意的舐犢情深;〈溫柔的夜〉則來台灣高雄的內門練武,有趣的是,通篇跟武學之旅無關,反倒是著墨於陳漱意日常關懷的毛小孩,只是在紐約她餵野貓,到內門她依依不捨的是一群野狗。
陳漱意果真是小說家,寫起散文來依然散發出濃濃的小說味,人物總在你毫無察覺之時就登了場,情節亦在你仍然意猶未盡之際,已經轉了彎,最佳例證是〈真假皇后〉,簡直就是一篇跌宕起伏的小說。所以,陳漱意的散文不是自怨自艾、不是傷春悲秋,而是生活的體驗,生命的省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