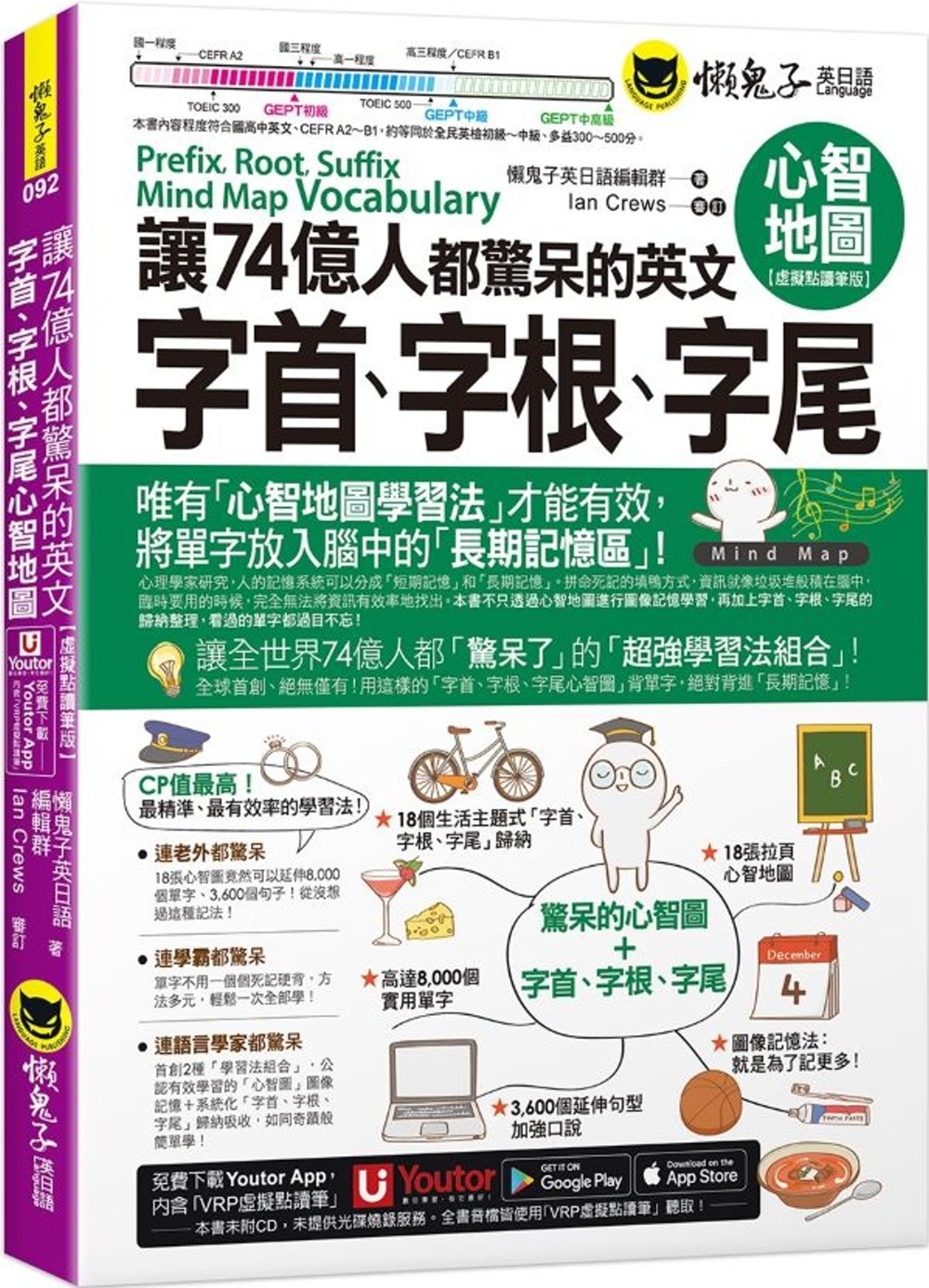東亞極權主義的起源:近代東亞史講義
第一講 近代史的結構
對於近代史的定義,我們往往因循西方學術界的普遍認知,認為「近代」的源自英國工業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這樣的認知雖然因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而普遍適用於全世界,但對於非西方地區的人來說,這套歷史發展的過程不僅有時差性,甚至在近代的發展過程中也往往有別於西方地區的發展模式。因此,當我們在觀察非西方地區的「現代化」發展時,不能只是把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產物(如工業化、都市化、現代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度、帝國主義)視為可靠的指標,而應該回歸到每個地方特有的脈絡情境,藉以說明究竟是什麼分裂了我們視為「古代」或「傳統」的那個時代,並且持續的宰制的我們現代人的那個「宿命」。這裡我們不得不採用義大利哲學家貝尼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的歷史認識論中的粗淺看法,將一切歷史知識的建構都視作「當代性」的產物,也就是說,那些促使我們重新爬梳歷史並將歷史帶入內在理解的過程都是由當代人藉由當代經驗加以重新尋找、重新理解且重新論述的。 當我們重這樣的歷史認識論出發時,便要如此問到,如今宰制著我們的現實宿命究竟為何?我們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去重新爬梳那些對我們來說充滿意義的過去事實?同時,有沒有一套有限但明確的架構可以幫助我們統整那些散亂在我們意識之內缺乏秩序和紀律的有關過去的知識?
要完成上述問題的定義,我們首先就要確認「我們」這一認知主體的範圍在哪。很明顯的,對於我們今天的這一堂講義的內容來說,我們的認知主體即是當代的台灣公民。然而,僅僅只說台灣公民或許會讓人誤以為是具有合法「中華民國」身分證的「國民」,卻忽略了在我們這一堂超越「純粹知」的課堂內,還具有認知主體的實踐意識對過去之知識有意義的組織和理解。因此,在這堂課程正式開始之前,我必須先為這一知識建構行動的基本「立場」作以下清晰的定義:我們這一「台灣人」的認知單位,不只是生活在台灣這塊地理上的人們,而是一群將台灣做為一追求獨立自治之共同體的理念而行動的人們所作出的各種知識層次上的行動主體。
有了對認知主體的清楚定義之後,我們就能更進一步通往對過去知識的統整、理解以及架構一有效認知範圍。正如同本課程的主題所揭示的,我們企圖從台灣人的角度來整理、理解及認識近代東亞的歷史知識和發展脈絡。如果從克羅齊的認識論出發,以及稍前我們對歷史認知主體的定義來做考量,那麼接著我們便要確認究竟近代東亞與當代台灣人(共同體的實踐)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現實與過去之連結。首先,我們要先意識到至今仍然困擾著台灣政治共同體實踐的乃是一種存在隨時將會覆滅的威脅,這一威脅則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以「至古以來之領土」宣稱擁有台灣之主權,並且以經濟和武力不斷侵擾著台灣人自日本殖民時代萌芽、中國國民黨獨裁時代明朗化乃至民主化以後逐漸奪取國家機器主權的「台灣民族共同體」。這樣一個從萌芽到漸漸成熟的民族共同體發展史同時也是我們做為實踐意義上的台灣人的「現代之宿命」。於是,這裡我們已經知道了台灣認知主體的「近代史之起點」,也就是從日本帝國殖民代台灣透過殖民地行政機器區分了「身為殖民者的日本人」以及「身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開始,而對於台灣人來說在近代東亞中的「主要他者」則有日本帝國以及來自東亞大陸上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和中國共產黨政權,台、日、中成為台灣人的東亞近代史上的三大主角,而作為「經典現代性」(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產物)的西方諸國成為了這部英雄史詩背後若隱若現,卻又充滿決定性的眾神。台灣共同體在這樣的近代環境中不斷地與外部進行鬥爭與融合至今,而對於「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樣的現實(當代)精神理念貫串了此一辯證過程,成為了台灣人認識近代東亞發展的「軸心」,並且成為了這場歷史知識建構立成背後的「終極因」,繼續主導著台灣共同體對此一信念的追求。
以上我們已經對近代東亞史這門學問所要處理的課題範圍和內容作了界定和描述,簡單總結,以台灣為中心的近代東亞歷史,其起源於日本帝國形成之時(約西元1860年代至1945年),同時歷經了大清帝國的覆滅、中國國民黨崛起、中國共產黨取得東亞大陸政權、冷戰時代以及蘇聯政權倒台後的東亞新變局,而鎖定的焦點主要在台、日、中三「者」之間的互動,而其餘的國家、世界局勢或者「非政治性」之因素則作為補充觀察或者視詮釋之必要而加入。
第二講 近代秩序在遠東的輸入
東亞走向近代化的契機乃在歐洲社會自十五、十六世紀以來的殖民運動,並在十八世紀以後走向帝國主義運動,然而不論是殖民主義還是帝國主義,西方向全球的擴張都都不是哪個強權打從一開始就對全世界所進行的「擘劃」。「殖民」與「帝國」並非西方世界獨有之產物,而是自人類有歷史以來,就不斷循環出現的一種人群組織與征服自然之模式。從原始社會的觀察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在某個時空之下的一個或數個部落,透過不斷遷徙以及人口在與環境鬥爭中順利成長為一個巨大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仍舊需要為了生存或過上好日子而不斷向外界征服,於是有的聯盟部落透過戰爭征服或外交合作殖民了原先非聯盟之部落或人群,而有些聯盟部落則在遠方某個物資充沛的角落選擇建立殖民據點,一方面將據點的剩餘物資送往聯盟所到之處以換取更多利益,另一方面也管理起了這塊「人跡」未至的新天地。從古至今,不論在世界的哪個有人群存在的角落,這樣的從部落到聯盟到帝國,不斷向外殖民的歷史事件時不時地上演,即便是現今的社會,那被我們稱之為「全球化」的經濟貿易與國際政治之活動,也依然依循著這一模式發展,只不過是將原本的部落聯盟改稱為「西方」、「文明」與「現(近)代」,而將非聯盟的人群或自然環境稱為「新大陸」、「野蠻」、「落後」與「第三世界」。
西方社會向世界各地的擴散與殖民過程可以視為是一個名為「西方」的部落聯盟在經歷了將近一千年從混亂到組織成熟,並從盤踞在亞洲的另一巨大部落聯盟中掙脫出來,透過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的路徑,找到了尚未被任何強大的部落聯盟或具有頑強抵抗力的人群所佔領的諸多新天地。於是全球各地的資源經由貿易或戰爭開始引入西方社會,同時也改變了西方社會從中世紀以來維持的組織型態:中央集權國家出現、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興起以及工業化─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三位一體的現代多國體系出現,成為了我們現今所熟知的「現代性」條件之基礎,也就是「近代秩序」的開端。
東亞社會的近代化不外也是西方近代秩序向外擴張發展的一個環節。在台灣,近代秩序的輸入首先由近代早期向海洋開拓的荷蘭與西班牙等國帶來,透過對殖民地的經營,將台灣帶進了歐洲的全球貿易網絡之中,即使在鄭成功殖民統治的時代,這條貿易線仍舊經由與日本及英國商隊公司的軍火貿易而維繫著,直到盤踞在東亞大陸上的大清帝國壟斷了台灣一切政治與經濟統治權為止,約有兩百年的時間被隔離於近代秩序之外。大清帝國在東亞大陸上的統治是另一種部落聯盟向外擴張進而形成帝國秩序的過程,徘徊在東亞大陸周邊的各民族部落聯盟透過佔領早在公元元年左右就已為秦、漢帝國所打造完成的中央集權國家官僚制度,來統治整個東亞社會及其周邊民族。十九世紀前半葉英國藉由一系列貿易戰爭將東亞大陸拉近近代秩序後,原先的東亞秩序連同清帝國也逐漸走向衰弱,同時台灣重新回到了近代秩序之中。日本社會則是在德川幕府作為部落聯盟共主所主宰的秩序中度過了兩、三百年的時光(僅留有部分藩國作為與近代秩序交流的窗口)後,隨著原本的東亞秩序開始崩解而有了「多藩」爭相加入近代秩序當中以擴張或保護其原先統治權力,最後才由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新秩序聯盟打倒了以德川家族為首的舊秩序聯盟,並走向了現代民主國家式的編戶齊名集權統治以及與西方帝國主義聯盟看齊的帝國主義運動,透過戰爭將朝鮮與台灣從清帝國秩序中抽離,納入到日本帝國的秩序之中,並開始了新一輪的殖民運動。
在東亞社會進入近代秩序的過程中,必須要注意的是,不論是清帝國還是日本,由西方擴張而來的近代秩序總是凌駕在她們之上,不論她們本身透過直接統治發揮了如何的「次秩序」統治,永遠也都逃離不了近代秩序的統治,近代秩序與全球其所能及的各地秩序都是「共時性」的。因此,在我們考察近代東亞社會時,如果膚淺的認為某一強權是能夠純粹地對其領地進行秩序輸出而不受近代秩序的影響,那就容易造成我們對東亞各方勢力所才取的博弈策略有錯誤的歸因,進而導致我們陷入了「只有『東亞』而無『近代』」的觀點,如「台灣只有殖民鬥爭」、「東亞大陸總是受近代帝國壓迫從沒與之和諧的可能」以及「日本只是近代帝國的成功仿效者」這種破碎而無法順利鑲嵌入「近代敘事體系」的歷史思維而已。
以上內容節錄自《人文與世界:當代人文科學的反思與嘗試》陳智豪◎著.白象文化出版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6267189832.pdf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人文與世界:當代人文科學的反思與嘗試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人文與世界:當代人文科學的反思與嘗試
◎本書涵跨文學、史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等主題,跳脫傳統學院派人文科學的專業化與瑣碎化之桎梏。
◎詮釋不需要學術權威的背書,重新回歸人類主體對其認知世界的直接詮釋。
◎只需要懷著一顆炙熱的心便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得到知識與樂趣。
人文是人類面對他自身所處的世界時所感受到的一種外在「規律」,
透過對這類規律的掌握,人類便漸漸發展出了
文學、史學、哲學與科學等等詮釋這些世界規律的「方法」,
這便是人文科學的起源。
然而,在現今學術圈幾乎壟斷了人文科學詮釋的合理性及認知結構的氛圍底下,
勢必會造成單一人文詮釋觀點壓制了社會上存在的一定數量的人文真理的詮釋,
那些詮釋即便不能融洽於學術圈的認知主體與結構,
但對於真心沉浸在這些論述的活生生的主體中,
卻是他們唯一能感受的真實的世界。
本書分文學篇、歷史篇、哲學篇、雜論篇,
透過對人文學術純粹愛戀的心情來寫作,
是以各種體裁文字來記錄自身思想、體驗的藝術作品,
希望那些被此書中文字所共鳴的讀者,
好好的享受閱讀人文寫作時的快樂。
◎代理經銷:白象文化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6267189832.pdf
作者簡介:
陳智豪
豐原社會科學高等專門學校校長兼東亞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專攻近代東亞史與人文基礎理論,將開發跳脫傳統學院派格式與偏見,重新找回研究人文科學世界之樂趣當作職志。
章節試閱
東亞極權主義的起源:近代東亞史講義
第一講 近代史的結構
對於近代史的定義,我們往往因循西方學術界的普遍認知,認為「近代」的源自英國工業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這樣的認知雖然因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而普遍適用於全世界,但對於非西方地區的人來說,這套歷史發展的過程不僅有時差性,甚至在近代的發展過程中也往往有別於西方地區的發展模式。因此,當我們在觀察非西方地區的「現代化」發展時,不能只是把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產物(如工業化、都市化、現代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度、帝國主義)視為可靠的指標,而應該回歸到每...
第一講 近代史的結構
對於近代史的定義,我們往往因循西方學術界的普遍認知,認為「近代」的源自英國工業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這樣的認知雖然因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而普遍適用於全世界,但對於非西方地區的人來說,這套歷史發展的過程不僅有時差性,甚至在近代的發展過程中也往往有別於西方地區的發展模式。因此,當我們在觀察非西方地區的「現代化」發展時,不能只是把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產物(如工業化、都市化、現代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度、帝國主義)視為可靠的指標,而應該回歸到每...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這一部嘗試在學術專業化越趨細密、破碎的時代,重新反省並建立古典人文學術的著作,這本著作並不講求任何學院向來引以為傲的學術技巧,而只在乎如何和當下的世界對話。我希望透過一種對人文學術純粹愛戀的心情來寫這本書,它並不是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更像是一種透過各種體裁文字來記錄自身思想、體驗的藝術作品。它不要求讀者在其中得到任何嚴謹的知識或現實的啟示,只求那些能被此書中文字所共鳴的讀者好好的享受閱讀人文寫作時的快樂。如果各位讀者中的任何一位能在閱讀本書時的某一小段落時能感到一點「感動」之情,那麼我想這...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