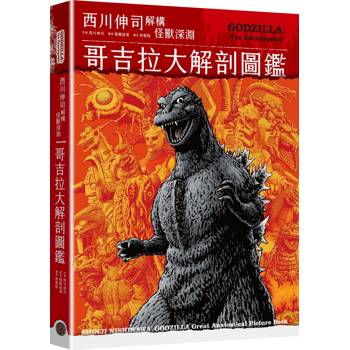英國BBC First熱門影集《菜鳥獸醫日記》原著
系列書籍長銷五十餘年,全球狂賣8000萬冊!
Amazon 4.8顆星 17000則讀者好評激推!
《時代雜誌》《紐約時報》《出版家週刊》《牛津郵報》等各大媒體共同盛讚!
獸醫文學巨作經典重現!全新翻譯版將讓讀者耳目一新!
跟著吉米‧哈利暢遊約克郡谷地,探訪那渺小卻又偉大的萬物生靈!
年輕的哈利收到面試邀請,希望他擔任獸醫助理一職,在那個考取獸醫執照等同失業的年代,他激動又滿懷希望地前往……
在這座英國鄉村小鎮,前景堪慮的菜鳥助手、刀子嘴豆腐心的獸醫老闆,面對大大小小的動物和純樸、善良又古怪的主人,等待他們的是層出不窮的「慘事」和讓人會心一笑的溫暖故事。
半夜穿睡衣出外診,被懷疑是逃獄;在冷風中幫母牛接生,被鄰居老伯揶揄經驗不足;盼了好久的單獨出診,卻遇上得當場殺掉馬兒的天人交戰;還被一隻哈巴狗認乾叔叔,除了送禮竟然還有簽名照?
哈利擁有非凡的講故事能力,他用敏銳又充滿愛的眼光觀察著動物和人類,用細膩、柔軟的筆觸描寫出英國鄉間怡人的風景,以及在那裡生活著的純樸而熱情的人們。他的人生故事既現實又奇幻,帶給現代讀者跳脫忙碌生活、被各種動物包圍的奇妙空間。
圖文作者│工作日誌 Daily_logbook Egan 誠摯推薦!
你會對獸醫工作好奇、有幻想嗎?是可愛的貓狗在身邊嬉戲?還是與珍奇異獸成為朋友?本書以第一人稱視角,告訴你獸醫師面對不同體型動物的生理與心理挑戰,以及生命的無常與飼主之間的人情冷暖。這是一本詼諧、幽默,又能了解獸醫產業真實面貌的好書。讓我們跟著吉米‧哈利的文字,一同體驗在約克郡谷地農家出外診的各種趣事!
│Amazon讀者溫暖推薦│
通過哈利的眼睛,我們看見了約克郡的簡單、安靜和美麗。他的同情心與我們現今這個冷酷無情的世界截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mjt
吉米‧哈利的獸醫生活展示了生命的全部──人類、動物和美麗的鄉村。他帶你經歷了艱苦的工作、對成就的渴望和害怕失去的狀態,但你還是可以放聲大笑,因為我們總是可以把日子過得幽默,這就是真實的日常。───G M.Larsen
吉米‧哈利帶領讀者回到了一個生活節奏較慢的時代,當時每一個人每天都有機會「聞到玫瑰花香」。我希望我可以回到那個時代,而哈利為讀者提供了這種旅行的最佳方式。───K.C
作者簡介:
吉米・哈利 James Herriot
吉米・哈利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出生,於格拉斯哥獸醫學院取得外科獸醫師資格。他在畢業不久後即前往北約克郡一家獸醫診所擔任助理,除了二戰期間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之外,直到一九九五年辭世前都在此執業。
他的系列書籍圍繞著獸醫工作與各式各樣有趣的動物,描述了北英格蘭約克郡鄉人與動物百態,以及獸醫業近代化的過程,使他大受歡迎。當時,英美出版界公認他是少數幾位能在英國和美國長期暢銷的作家之一。他的書籍今日已被拍成兩部電影和英國BBC頻道的熱門影集,並影響了後世的獸醫文學。
吉米哈利去世之後,英美文學界出版了數本與他相關的傳記。
關於吉米・哈利的生平事蹟,詳見網站:www.worldofjamesherriot.com。
譯者簡介:
王翎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所畢業,現專事筆譯。譯有《母親的歷史》《童話的魅力》《了不起的波力》《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塵之書》《惡作劇女孩》《雪山男孩與幻影巨怪》《聽不見的聲音》《暗黑孤兒院》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課本裡完全沒寫這種情況,我心裡暗想。此時雪花從大開的門口吹入,落在我光裸的背上。
我臉朝下趴在卵石地面上一灘無以名狀的汙泥裡,一隻手臂深入母牛拚命用力的體內,兩腳在卵石間隙胡亂踩踏想找到立足點,赤裸的上身盡是混了塵土跟乾涸血漬的雪水。農場主人在旁舉著一盞直冒煙氣的油燈,我的能見範圍僅限於油燈投出的一圈閃爍光暈之內。
沒有,課本裡隻字未提要怎麼摸黑尋找繩索和器具,沒說只有半桶溫水要怎麼保持乾淨,也沒說會有突起的卵石戳頂你的胸膛。課本裡也沒說手臂會逐漸陷入麻木,還有手指頭努力對抗母牛強勁的排出力道時,肌肉傳來的那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麻痺感。
課本裡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氣力會一點一滴耗竭,感覺徒勞無功,心底深處隱約傳來恐慌的聲音。
我的思緒飄回產科教科書裡的那張照片。發亮的地板正中央立著一頭母牛,一位時髦有型的外科獸醫師穿著一塵不染的產科手術服,將手臂伸入母牛體內時保持禮貌不會太過深入。他滿面笑容、一派輕鬆,農場主人和幫手群滿面笑容,就連母牛也滿面笑容。完全看不到一點塵土、一絲血漬,或一滴汗珠。
照片裡的男人剛剛享用完一頓美味的午餐,移步到隔壁鄰居家隨手幫忙接生小牛,單純是樂趣使然,像是飯後來份甜點。他可沒有凌晨兩點鐘渾身發抖爬出被窩,在積雪結凍的道路上顛簸了十二英里,撐著惺忪睡眼盯著前方,直到車頭燈照亮的範圍裡終於出現那座孤伶伶的農舍。他也沒有沿著白皚皚的山坡爬半英里山路,終於抵達病畜所在的那座連門都沒有的榖倉。
我奮力扭動,想朝母牛體內再多深入一吋。胎牛的頭在後面,我用五指指尖無比艱難地將打了活結的細繩推向牠的下顎。我的手臂一直被母牛的骨盆和胎牛夾擠,每次母牛一用力,手臂承受的壓擠力道大得讓人幾乎無法忍受,等她放鬆下來,我就再將繩套推進一吋。我在想自己還能撐多久,如果不趕快套住胎牛下顎,我就再也沒辦法拉牠出來了。我悶哼出聲,咬緊牙關,再次向前推進。
又吹來微微的一陣雪,我幾乎可以聽見雪花落在我滿是汗水的背上嘶嘶作響。我的額頭也滿是汗水,在我用力推時流進眼睛裡。
碰到小牛難產時,你總是會開始懷疑自己真能打贏這場仗嗎。我已經進入這個階段。
腦中一時之間雜念紛飛。「也許宰了母牛比較好,她的骨盆太窄小,我覺得胎牛根本出不來。」或是「這麼肥美,是適合當肉牛的類型,你不覺得叫屠夫來會更划算嗎?」或是「這個胎位很不正。如果母牛的骨盆夠大,很容易就能讓胎牛的頭轉過來,但就這個案例來說幾乎不可能。」
當然,我也可以用碎胎術將胎牛取出—用金屬線套住牠的脖子然後鋸掉頭。碰到這樣的情況,多半是以滿地支離破碎的頭部、四肢和成堆內臟收場,有一些厚重的教科書專門教你各式各樣切碎胎牛的方法。
但這回沒有一種方法適用,因為胎牛還活著。我將手指伸到極限時,已經能碰到牠的上下唇連合部,小傢伙的舌頭抽動讓我吃了一驚。情況出乎我的意料,因為這種胎位的仔牛通常是死胎,母畜宮縮的強勁壓擠會讓牠的頸部遭到急性拉扯,造成窒息。但這頭胎牛身上還有一絲生機,要出來就得讓牠整頭完好地出生。
我回到水桶旁,桶裡的水已經變成冰冷的血水,我默默用肥皂清潔雙臂。接著我再次趴下,感覺戳入胸膛的卵石比先前更硬了。我在卵石間隙踩穩,甩掉流到眼裡的汗水,第一百次將彷彿變成義大利麵的手臂伸進母牛體內。我將手伸到小牛乾巴細小的腿旁,感覺牠的腿像砂紙一樣磨撕我的皮肉,接著伸向牠的頸彎處,碰到耳朵,然後萬分辛苦地沿著牠的臉側伸向我當前的人生目標:牠的下顎。
真是不可思議,我已經花了將近兩小時做同樣的事:即使力氣逐漸耗盡,還是拚命想用繩套圈住那個下顎。其他能試的方法我都已經試過了,包括推牠的其中一條腿,還有用鈍鈎扣在眼眶內側凹處輕輕牽引,但我後來還是回頭嘗試繩套。
這場接生從頭到尾淒慘無比。農場主人丁斯岱先生個子瘦高、憂愁寡言,似乎一直在等待最糟的情況發生。他的兒子也在,跟他一樣個子瘦高、憂愁寡言,父子倆看著我奮力接生,陷入更深的愁雲慘霧。
最糟的,其實是老伯。最初進入山坡上的穀倉時,我就被這個舒服安坐於稻草捆上的小老頭嚇了一跳,他戴著一頂豬肉派帽,兩眼炯炯有神。那時他正朝菸斗裡填入菸草,明擺著準備來看好戲。
「我說啊,年輕人,」他用帶著濃重鼻音的西來丁腔大喊。「我跟丁斯岱先生是兄弟,我的農場在利斯頓谷地那邊。」
我放下手中器具,向他點頭致意。「您好,敝姓哈利。」
老頭上上下下打量我,眼光銳利。「我家的獸醫是布魯菲德先生。想來你一定聽說過—沒有人不認識他吧,我想。厲害得很啊,布魯菲德先生,尤其擅長接生小牛。你知道嗎,我從沒看過他吃癟。」
我勉強擠出一絲微笑。任何其他時候我都樂於聽說同行有多麼高明,但不知怎麼,我當下不想聽到,就是不想。事實上,他說的話敲響了我心中那座小小的喪鐘。
「恕我不認識布魯菲德先生。」我說,並脫下外套,然後不怎麼情願地將上衣也脫掉。「不過我是不久前才來到這一帶。」
老伯大驚失色。「不認識!看來天底下也只有你不認識他。我可以告訴你,在利斯頓谷地,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在震驚之下陷入沉默,劃了一根火柴點燃菸斗。接著他很快瞥了一眼我起滿雞皮疙瘩的身軀。「布魯菲德脫下衣服的身材簡直像個拳擊手,從沒看過哪個男人像他一樣渾身肌肉。」
一波疲軟無力的感覺緩緩席捲全身,我忽然覺得雙腳像灌了鉛一般沉重不聽使喚。我開始將繩索和器具擺開在一條乾淨的毛巾上時,老頭又開口了。
「容我問一句,你哪時拿到執照的?」
「喔,大約七個月前。」
「七個月啊!」老伯露出和藹的笑容,他壓平煙草,呼出一團難聞的藍色煙霧。「我老是說啊,啥都比不上經驗。布魯菲德先生當我家的獸醫當到現在十年囉,內行得很。抱著課本死讀書哪裡行啊,碰到問題,就看經驗夠不夠。」
我在水桶裡滴了幾滴消毒劑,仔細地搓出泡抹清潔手臂。接著我在母牛後方跪下來。
「布魯菲德先生每次都會先在手臂上抹一些特殊的潤滑油。」老伯說,心滿意足地抽著菸斗。「他說只用肥皂和水的話,會讓子宮發炎。」
我展開第一次探索。這是所有獸醫第一次伸手幫母牛內診時都會經歷的沉重時刻。幾秒鐘內就會揭曉,究竟我可以在十五分鐘內穿回外套,還是接下來會有好幾個小時的苦工等著我。
這一次我的運氣不太好;胎位很不理想。仔牛頭部在後,而且完全沒有空間;母畜比較像是沒生產過的女牛,不像生第二胎的母牛。而且她非常乾—羊水肯定是好幾個小時前就流乾了。母牛之前在高地上晃蕩弄得筋疲力竭,比預產期早了一週開始分娩,所以他們才會把她帶到這座半荒廢的穀倉。無論如何,下次再見到我的床鋪會是很久以後的事。
「怎麼樣呀,小伙子,有什麼發現?」老伯尖銳的話聲劃破寂靜。「頭在後面,是吧?那就沒什麼
大問題了嘛。我看過布魯菲德先生怎麼搞定的—他直接把小牛轉過來,先把後腿拉出來就成了。」
以前我就聽過這種廢話。執業不久後我就學到一課,所有飼主碰上別人養的家畜都會變成專家。自己家養的動物有狀況時,他們通常會立刻衝去打電話叫獸醫,但碰到鄰居家的動物有狀況,他們就顯得自信滿滿、見多識廣,提出各種高見。我觀察到的另一種現象,是當事人通常將左鄰右舍的建議看得比獸醫的建議還寶貴。例如眼前這個例子;老伯顯然是大家公認的賢者,丁斯岱父子畢恭畢敬聆聽他的每字每句。
「對付這種情況還有一個辦法,」老伯接著說,「就是叫幾個強壯的小伙子拿繩子把牠拉出來,別管頭在後面還是前面。」
我正在努力摸索,聽了之後倒抽一口氣。「裡頭空間這麼小,我想不可能讓小牛完全轉過來。而且不把牠的頭轉正就拉出來,可能會讓母牛的骨盆整個裂開。」
丁斯岱父子瞇起眼。他們顯然覺得,老伯傳遞了高深知識,我卻顧左右而言他。
如今,兩小時過去,眼看就要慘敗收場,我也瀕臨崩潰。在陰鬱沉默的丁斯岱父子注視之下,還有老伯沒完沒了的指點聲中,我在髒汙的卵石地面上以卑屈的姿勢翻來滾去。老伯紅潤的臉龐神采奕奕,一雙小眼睛閃閃發光,好多年沒碰上這麼歡樂的夜晚,大老遠爬上山坡來一趟真是值回票價。他的精力十足,每分每秒都樂在其中。
我趴在那裡,閉著雙眼,臉上泥汙乾硬,嘴巴半開。老伯手拿菸斗,坐在稻草捆上向前傾身。「年輕人,你快沒力了。」他說話時滿意極了。「我啊,從來沒看過布魯菲德先生沒力,他的經驗豐富得不得了。還有啊,他強壯得很,真的,什麼都累不倒他。」
怒氣流貫全身,讓我精神為之一振。這時該做的當然是站起身,將整桶血水倒在老伯頭上,衝下山丘開車走人;遠離約克郡,遠離老伯,遠離丁斯岱父子,還有遠離這頭母牛。
但我只是咬緊牙根,雙腿用力撐住,使盡渾身解數前推;連我自己都不敢置信,我竟然感覺到手中繩套滑過尖銳的小顆門齒,套住了胎牛的嘴部。我嘴裡喃喃祈禱,小心翼翼地用左手拉扯細繩,感覺活結收緊。成功套住胎牛的下顎了。
總算可以開始做正事。「丁斯岱先生,現在抓住繩子,稍微保持拉住就好。我現在要開始推小牛,你如果同時穩穩地拉,頭應該就會轉過來。」
「繩子要是鬆掉怎麼辦?」老伯滿心期盼地發問。
我沒答腔。我將手伸進去抵著胎牛肩頭,開始邊抗衡母牛宮縮的力道邊推動胎牛。我感覺到牠的小身體朝我遠離。「丁斯岱先生,現在穩穩地拉,不要急著用力。」然後心中暗道:「老天,千萬不要讓繩套滑掉啊。」
胎牛的頭正在轉過來。我可以感覺到牠的脖頸逐漸貼直我的手臂,然後是牠的耳朵碰到我的手肘。我放開牠的肩頭,抓住小小的口鼻部。我用手遮擋住牠的牙齒以免刮傷產道壁,引導牠的頭來到應該在的位置,也就是擱在前腿上。
我很快將繩套拉開向後套到雙耳後面,「現在趁母牛用力時拉出小牛的頭。」
「不對呀,你現在應該拉牠的兩條腿。」老伯大喊。
「聽我說,拉牠頭上那條該死的繩子!」我用最大音量吼出聲來,看到老伯悻悻然退回他的稻草捆上,心裡立刻舒坦多了。
小牛的頭在牽引之下被帶出來,身體也跟著順利地滑出來。小傢伙躺在礫石地上一動也不動,兩眼空洞無神,舌頭發青且嚴重腫脹。
「快死了,肯定沒命。」老伯嘟噥著,再次發動攻勢。
我清除小牛嘴裡的黏液,對著牠的喉頭用力吹氣,開始幫牠做人工呼吸,又在牠的肋骨上大力按壓幾下。小牛呼了一口粗氣,眼皮開始顫動。接著牠開始吸氣,一條腿大力抽動一下。
老伯摘下帽子,不敢置信地搔了搔頭。「老天爺啊,牠還活著。看你搞了那麼久,我還想著牠鐵定死翹翹了。」他先前的高昂興致已經失去大半,嘴裡叼著的菸斗燃盡空懸。
「我知道小傢伙要的是什麼。」我說。我抓住小牛的前腿,將牠拖拉到母親的頭旁邊。母牛伸長身體側臥著,頭部疲軟無力貼在凹凸不平的地板上。她的肋骨部位隆起,雙眼幾乎閉上,一副什麼都不想再管的模樣。但她感覺到小牛身軀靠近自己的頭臉時,卻變得大不相同:圓睜雙眼,口鼻開始嗅聞探索新事物。每聞一下,她的興致就愈發濃厚,她掙扎著立起上身,在小牛全身嗅聞探測,胸腔深處發出低沉轟鳴。然後她開始有條不紊地舔舐牛犢。母牛舌頭上粗糙的乳突拖曳過小生命的毛皮時,是大自然為這種時刻所提供最完美的刺激訊號,小牛弓起了背部。一分鐘內,小牛已經搖頭晃腦,試著坐直起來。
我咧嘴笑了。這就是工作中我喜歡的部分,小小的奇蹟,即使以後成了常見景象,但每次看到還是會覺得新鮮驚奇。我盡可能清理掉身上乾涸的血跡和髒汙,但大部分已經在皮膚上結塊,用指甲摳也摳不掉,得等回到家才能沖熱水洗掉。我將上衣套回身上,全身上下感覺好像被人用粗棍棒痛毆許久,每束肌肉都在痛。我口乾舌燥,嘴唇幾乎黏在一起。
愁苦的瘦長人影飄近。「能喝點什麼嗎?」丁斯岱先生問。
我可以感覺到自己滿是髒汙的臉在半信半疑中綻出微笑,腦海中浮現兌了威士忌的熱茶的景象。
「你人真好,丁斯岱先生,我很想喝點東西。整整辛苦了兩個小時。」
「不是,」丁斯岱先生沉著地望著我,「我是指母牛。」
我開始胡言亂語。「哦對,當然,那是一定的,絕對要讓她喝點什麼。她一定口很渴,對她有好處的。一定,一定要給她喝點東西。」
我收拾好用具,跌跌撞撞走出穀倉。荒野上依舊一片黑暗,雪地上颳起的刺骨寒風吹得我兩眼發疼。我拖著沉重步伐走下山坡,老伯盛氣凌人的聲音最後一次傳入耳裡。
「布魯菲德先生不會讓剛生產過的母牛喝東西,說會凍著腸胃。」
第二章
搖晃顛簸的巴士裡酷熱不已,七月驕陽直曬車窗,坐這一側真是選錯邊。我在座位上不舒服地挪動一下身體,身上是最好的一套西裝,我伸出手指鬆了鬆勒住脖子的白色領口。在這種天氣穿這套服裝實在愚蠢,但我未來的僱主就在數英里外等我登門拜訪,我得留下好印象。
這次應徵會有什麼結果很難預料;在一九三七年新拿到外科獸醫師執照,就跟抽號碼牌等領失業救濟金沒有兩樣。由於政府十年來不聞不問,農業一蹶不振,農民主要依賴的輓馬消失得很快。當年輕人寒窗苦讀五年終於畢業,面對的卻是一個對他們的熱誠和滿腹知識冷漠無感的世界,這時候當個烏鴉嘴真是再容易不過。《獸醫誌》期刊通常每週會刊登兩到三則徵人啟事,每個職缺平均有八十人前去應徵。
收到從約克郡谷地的達洛比寄來的通知信時,感覺好不真實。皇家獸醫學院成員齊格菲.法農先生希望於本週五下午與我會面;對方希望我於午茶時間抵達,晤談後如雙方皆認為適合,我即可獲聘成為助理。我在不可置信中緊抓這一線生機;有許多跟我一樣取得執照的友人,不是待業中,就是去當店員或船廠工人,我原本對未來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巴士駛入另一段陡峭彎道,司機再次換檔不順,變速箱發出嘰嘎怪聲。目前車子已經穩定爬坡十五英里左右,逐漸接近遠方藍霧氤氳的本寧山脈。我以前從沒來過約克郡,但是一聽到這地名,總會聯想到與約克夏布丁類似,一吃就飽、毫不浪漫的場景;我已經作好心理準備,未來要面對一個樸實單調、缺乏魅力的地方。但在巴士爬坡時發出的嘰嘎怪聲中,我開始浮想聯翩。原本形狀模糊的高地逐漸成形,高聳翠綠的山丘和寬闊的河谷陸續現身。在河谷谷底,田地、樹林和灰色岩石砌建的農舍錯落分布,河川蜿蜒流過其間,水流環繞的田地彷彿自成島嶼,綠油油的凸角朝著如暗潮自峰嶺往下蔓延的石南荒原突伸。
我看到圍柵和樹籬已經被乾砌石牆取代,無論與道路相鄰、環繞田地或周圍山丘上無盡綿延的皆是石牆。石牆無所不在,不斷延伸,在翠綠高地上縱橫刻畫。
隨著巴士愈來愈接近目的地,恐怖故事也在我腦中盤旋不去;故事是由學長們傳回學院,執業數個月讓他們心如鐵石,滿腔怨憤。助理不過是沙粒草芥,在惡毒無良的獸醫老闆奴役之下挨餓賣命。戴夫.史蒂文斯顫抖著手點燃一根菸:「沒有一個晚上能休息,也沒放過半天假。他吩咐我洗車、除草、到院子挖土、採買他全家要用的東西。但後來他叫我去掃煙囪,我就離職了。」或是威利.約翰史東說:「我接下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幫一匹馬插胃管。該插進食道,卻插進了氣管。快速打氣幾下,那匹馬就轟然倒地—死透了。我就是那時候開始冒白頭髮。」或是弗雷.普林格碰到的慘事,傳得沸沸揚揚。弗雷幫一隻鼓脹症的母牛插入套針管,飼主對於從牛腹嘶嘶排出的氣體很感興趣,而弗雷跟著得意忘形,拿著打火機靠近套管。烈焰霎時席捲而來,火舌吞噬旁邊的乾草捆,把牛棚燒得精光。弗雷隨後立刻接受某個在殖民地的工作—─那地方叫什麼來著?
第一章
課本裡完全沒寫這種情況,我心裡暗想。此時雪花從大開的門口吹入,落在我光裸的背上。
我臉朝下趴在卵石地面上一灘無以名狀的汙泥裡,一隻手臂深入母牛拚命用力的體內,兩腳在卵石間隙胡亂踩踏想找到立足點,赤裸的上身盡是混了塵土跟乾涸血漬的雪水。農場主人在旁舉著一盞直冒煙氣的油燈,我的能見範圍僅限於油燈投出的一圈閃爍光暈之內。
沒有,課本裡隻字未提要怎麼摸黑尋找繩索和器具,沒說只有半桶溫水要怎麼保持乾淨,也沒說會有突起的卵石戳頂你的胸膛。課本裡也沒說手臂會逐漸陷入麻木,還有手指頭努力對抗母牛強勁的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