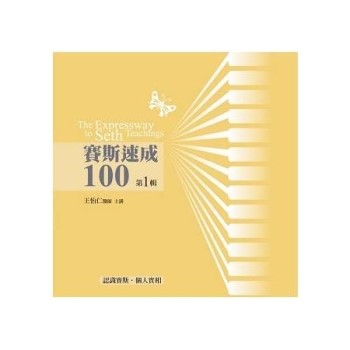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目前評分: 評分:
圖書名稱:臺灣文化造形(一) 內容簡介:
與其說李喬是為了撰寫文學與文化評論而長期廣泛大量地閱讀,不如說剛好相反,他是「凝視現實有感——大量閱讀,深化思考——論述問題,提出解方」。李喬的知識飢渴症,是因為他有持續關心,想要釐清、解釋、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攸關他所生存的島嶼,以及與他一起共頻呼吸的島嶼子民。
這些問題不是一本書、一種主義、一類思潮可以釐清與解答。
那個被怪獸追趕的惡夢,既是指涉「生命是痛苦的符號」,也是臺灣命運的隱喻,惡夢纏繞的時間有多長,李喬閱讀、思考與寫作的時間就有多長。這不只是隱喻,這是李喬的生活現實與生命實體。
這個生命實體,從青年時期思索「痛苦的符號」開始。他所遇到的老師博學者眾,帶領他進入知識海域,如中國文字學、西方哲學、佛學、易學、心理學……等等,而他所自學的各種文藝思潮與文學理論,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魔幻寫實、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後設理論,無所不包,
還有各種歷史書籍、符號學、語言學、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
1990 年代開始,臺灣現實與臺灣命運的課題開始纏繞李喬,他的閱讀更積極更廣泛了:「約在1990 年之後十多年,我才始於自我強迫,終而狂熱投入,苦讀文化人類學的書籍,旁及現代民族、國家、權力、殖民、生態的論述,都是自修苦學(當然也向多位行家請益),顯然所學不完整。但我努力思索探索,追求體系性理解——這是我中老年後最美好的一部分。」
如此這般,李喬建構了一張幅員遼闊的閱讀地圖,地圖上密密麻麻註記了無數閱讀旅棧,每一個旅棧都幻變成無數評論,「雜學家李喬」誕生。所有的跨界閱讀都成為「雜學家李喬」的脊骨血肉,織就他的思考紋理與思想體系,更成為他的靈魂底色。我認為,李喬的評論甚至比他的小說更貼近「李喬本尊」,更能彰顯「思想家李喬」的整體面貌。
李喬以廣博雜學,試圖探索、描繪、解釋這個世界的紛繁現象,試圖揭露這個世界(特別是臺灣)的問題與困境,尋求解決的路徑與方法,成就了近二百萬字的評論文字,「雜學家李喬」、「思想家李喬」幾乎可以說是《評論卷》十冊最精簡最精準的註腳。
作者簡介:
李喬,本名李能棋,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勤於涉獵各類知識,形成作品豐富內涵,創作包括小說、詩、散文、戲劇、雜文、評論等。精擅多樣類型,講究形式變化,主張「文學志在反抗」和「臺灣主體意識」,作品已有多國語言外譯。寫作之外,另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及公共事務。曾獲吳三連獎、國家文藝獎、臺灣文學金典獎、行政院文化獎等。
李喬全集主編:
黃美娥,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另亦擔任國家藝術基金會董事、漢學研究中心指導委員、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諮詢委員等,曾任臺灣大學臺文所所長、臺灣文學學會理事長。長期從事臺灣文學研究與史料編纂,著有《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及論文百餘篇,另編有《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目錄暨選集1603-1945》、《世界中的臺灣文學》等十餘種。曾獲竹塹文學評論獎首獎、巫永福文學評論獎、國家圖書館「臺灣各大學學術資源能量風貌」文學研究專書高被引排序第一。
評論卷主編:
楊翠,1962年生,臺中人,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自立晚報》副刊編輯、《自立週報》全臺新聞主編、《臺灣文藝》執行主編、臺中縣社區公民大學執行委員、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著有散文集《最初的晚霞》、《壓不扁的玫瑰:一位母親的318運動事件簿》、《年記1962:一個時代的誕生》,傳記文學《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學術論文《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少數說話:臺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並與施懿琳合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與廖振富合著《臺中市文學史》。
目次:
向反抗的哲學家致敬
為臺灣而寫:李喬的文學、哲學與行動
為臺灣文學「做膽」
編輯凡例
告白與道別──李喬自序
春暉版《臺灣文化造型》序
我怕哭聲
藝術之「膽」
愛經三句
宗教與我
說感恩
談性說愛
現代婚姻
我看離婚
知識.學問.智慧
不是的父母
速度與壽命
速度與歷史
生病之益
文化的省思
《臺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代序
臺灣文化體質檢討
「文化」是什麼?
文化的四層面
「文化學」的認識
臺灣人的覺醒
柔軟的心
幾個重要觀念
臺灣的「飲食文化」
臺灣文化的淵源
臺灣人「歷史發展」之困境
宗教在臺灣反對運動中的角色意義
小論臺灣文化的危機
從文化層面看「二二八」的影響
創造具有主體性的臺灣文化
從臺灣人自主性立場看「二二八」──兼評戴國煇著《臺
灣》第四章第三節
臺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
恍惚人世間
「中國現象」的教材意義
一刀的兩刃
「臺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
腥風血雨天安門──臺灣立場的觀感
臺灣人自救與救中國──黃文雄著《中國的沒落》讀後
臺灣人的成長史──介評《許曹德回憶錄》
臺灣新文化素描
「旅鼠」的悲劇
「以臺制臺」說
臺灣人的新造形
臺獨分子、關公與媽祖娘
暴力怎麼形成的?
誰「不道德」?
臺灣人何時長大?──讀蘇曉康談話有感
學術與狗屁之間
反抗是最高美德──「反抗哲學」簡說
虛幻中國之害
尊重生命
說「臺奸」
生命的創新
臺灣的大與小
莫為閒置而投入―― 提醒老康及時回頭
客家人的政治立場
一九九二年後的臺灣運動
絕對不要相信「他們」―― 臺灣的「二二八圖像」
牛的變貌──謝里法「牛的系列」個展
反抗的哲學基礎
脫出輪迴與好雪片片―― 敬致證嚴法師
【內文】
臺灣的大與小
臺灣是一個亞熱帶的小巧海島。在人為景觀上卻出現唐突不協調的「比大比高」現象。這個現象背後是有其複雜深刻的文化意義的——它,正是臺灣的文化病症之一。
由北到南,我們可以看到十丈大佛塑像,十二丈大關公,二十丈大濟公、大彌勒……這些塑像一律是顏色俗豔,塑造粗糙;除了多少公噸水泥與鋼筋的聯想外,再無任何精神面的感應了。遠東最大機場、十萬公頃國家公園、十公尺大國旗,這是政府誇示之大;幾百公斤大粽子、大紅龜,十樓到地的大領帶,一百公尺的竹骨布面巨龍,這是民間展示之大。凡此有一共同點:大而粗糙、大而低
俗、大而空洞、大而無當、大而虛假……。
大小都有其象徵意義。大,象徵崇高、超越、力量、氣勢、權力等;小,象徵親密、濃縮、精緻、實際、活潑等。然而,大小的呈現,必須與整個空間形成和諧自然的配合,才能呈現其大其小的正面象徵意義。臺灣明明是小而美的島嶼,勉強求大,便是不和諧便是不自然,其大的象徵是負面的:膨脹浮濫、虛誇不實、外表偽裝、欠缺自信、特權怪制突兀存在……。
至於臺灣朝野何以「實小而強求大」?深言之不外兩大因素造成:一是臺灣人的精神世界裡,仍然不脫「中原中心——地方邊陲」的文化魔咒的侷囿;卑小邊陲只好迎駕巨大的中原以大量水泥鋼筋了。二是不合民主程序的外來統治者,以崇高宏偉的圖騰鎮壓蕞爾島民,企圖壓垮島民。當然彼政權也成為虛飾空洞的「水泥鋼筋」,與人塑的景觀形成「互為象微」的絕佳時代場景!
臺灣本來就小,首先要追求充實而精緻的小;臺灣也可以也應該追求大,但不是基於「地大物博」而來的大,而是通過充實精緻的小而純的精神世界之大,亦即文化宇宙之大!
小即是美,小即是可以掌握的真實。見微知著,一沙見世界,一葉知天下,所以小是濃縮、是豐富;小可以藏大,袖裡乾坤,知小識大。小的最大優越點有二:一是從精緻、充實可以掌握的小出發,可以享有絕大絕廣的想像空間;無論是藝術創造、科學發明都享有無窮大的空間,不被「大」壓制而翱翔於天外之天,深入於無底之深密。二是「小的範圍內」,彼此具備私祕性親密關係;彼此利害禍福因「小」而自然是一致的,於是「小的範圍內」,一體感產生,「命運共同體」便在雨夕風晨、在茶餘飯後凝聚形成了!因為小,所以外人不能離間!然則,這是多麼美好圓滿的「小」啊!問題是:這種「小」是要大家共同來創造的。
臺灣有了「美好圓滿的小」,是時臺灣海峽是我們的排水溝,大陸是我們的後花園,太平洋是海浴場,而歐美扶桑都是我們生活
的空間;是時人人精通兩種以上外國語言,各有專業長才。這就是臺灣「由小而大」的時日了。朋友:我們不要怕自己「小」,怕的是不知「小」的可貴,不肯從「小」開始創造!
|
|
|
|
|
 | 作者:許添盛 出版社:賽斯文化 出版日期:2017-04-05 66折: $ 660 |  | 作者:許添盛醫師主講 出版社:賽斯文化 出版日期:2015-11-20 66折: $ 660 |  | 作者:YUKIJI 出版社:春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11-09 66折: $ 6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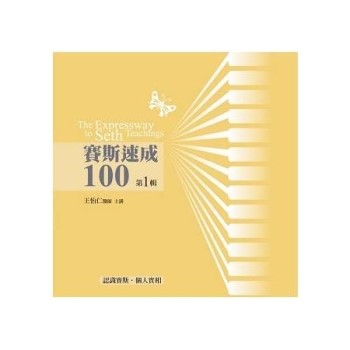 | 作者:王怡仁 出版社:賽斯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10 66折: $ 858 | |
|
|
 | 作者:詹姆斯.克利爾 出版社:方智出版 出版日期:2019-06-01 $ 260 |  | 作者:九井諒子 出版社: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1-22 $ 395 |  | 作者:葉向林Noah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1-14 $ 410 |  | 作者:蔡康永 出版社:如何出版 出版日期:2024-08-01 $ 316 | |
|
|
 | 作者:高松美咲 出版社: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25-02-06 $ 105 |  | $ 252 |  | 作者:希行 出版社: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2-12 $ 269 |  | 作者:新井すみこ 出版社:台灣角川 出版日期:2025-02-06 $ 750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