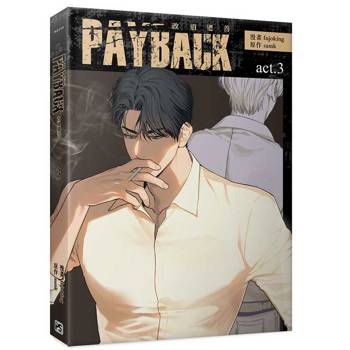大浪淘沙,一粒沙掉進貝殼中
日積月累形成一粒珍珠
文青時代,是那粒不起眼的沙
卻也是一顆珍珠的起點
本書特色
★收錄蔣勳青年時期短篇小說、散文以及最初的文字創作
★萬言自序,回望文青時代創作軌跡,深深眷戀、緩緩告別
★青少年、文青時代珍貴成長影像與速寫作品,特別公開
「文青時代我們如此孤獨,不想溝通,或不屑溝通。如果最終溝通只是誤解,不妨就冷笑著看這荒謬的一切吧。我的文青時代延續很久,從初中到高中、大學,一直延遲到巴黎讀書,彷彿不想從文青的夢裏醒來,可是卻可以在卡繆、卡夫卡、齊克果等的文學作品中找到自己內心最無法被理解的孤獨……」
陰鬱的文青、叛逆的文青、虛無的文青……中學以後的蔣勳,瘦削蒼白,一頭天生捲髮。他逐漸偏離正軌教育的航道,走向自己迷戀的文青夢想中。
不被世界理解也無妨,躲在角落也不孤獨,因為文學的世界、美術的世界,有許多同行伴侶,像暗夜裡仰望的繁星,不管多麼遙遠,又似乎都近在身邊。
《我的文青時代》回溯蔣勳創作生涯的零座標,也許所有隨手撕碎在風中散去的文字和圖繪,才是真正文青的夢。如果留著,有不同的意義嗎?文青時代,再見面,是否只剩啼笑皆非?
作者簡介:
蔣勳
多年來以文、以畫闡釋生活之美與生命之好。寫作小說、散文、詩、藝術史,以及美學論述作品等,深入淺出引領人們進入美的殿堂,並多次舉辦畫展,深獲各界好評。
著有散文《五行九宮:母親的料理時代》《龍仔尾‧貓》《萬寂殘紅一笑中:臺靜農與他的時代》《歲月靜好:蔣勳日常功課》《雲淡風輕》《說文學之美:品味唐詩》《說文學之美:感覺宋詞》《池上日記》《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此生:肉身覺醒》《此時眾生》《夢紅樓》《微塵眾》《吳哥之美》等;藝術論述《漢字書法之美》《新編美的曙光》《美的沉思》《天地有大美》《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等;詩作《少年中國》《母親》《多情應笑我》《祝福》《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等;小說《新傳說》《情不自禁》《欲愛書:寫給Ly’s M》;有聲書《孤獨六講有聲書》;畫冊《池上印象》等。
蔣勳:https://www.facebook.com/chiangxun1947
章節試閱
希望我能有條船
「我一直希望能有條船。」
天氣很熱,身上曬脫了皮的地方又隱隱作痛,以致我根本沒注意他在說些什麼,反正也不會是重要的話。我們在一起好像從來也沒說過什麼嚴肅的話,只有一次他說如果全世界的女孩子都能像我這樣不讓人煩心就好了。我想那也不見得是什麼頂重要的話,不過我後來就一直沒忘掉,而且想起來就有點開心。
事實上,除了這句話之外,也沒有什麼可以使我記起的。每次跟他出去他總是稱讚一聲妳的衣服好好看,或者妳今天頭髮梳得很漂亮這些話。而這些話又是每一個跟我一塊玩的男孩子都說過的,所以我就覺得有些煩厭。
不讓男人煩心。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發現這麼新穎的一句話的。那天回家之後,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這句話,我從前是一上床就睡著的。
我不太懂得怎麼去分析自己,那比如何去打扮自己要難得多。我們班上有一個叫喬蔓春的,就好會分析自己,她常跟我說她好寂寞,因爲她的自尊和自卑都太強;又說她常想自殺,活著太痛苦。我覺得她簡直了不起,我是從來不會想那麼多的。同學都說我好快樂,我想實在沒有什麼能讓人不快樂的嘛。
有一次我把成績單拿回去,上面有六科不及格,爸爸甩我一個耳光,我跑回房間捂著枕頭好好大哭了一場,後來就睡著了。睡了不知多久,又被一陣雜亂的擂門聲和叫嚷聲吵醒,打開門一看,爸媽弟妹全擁在門口,一臉焦急慌張的樣子。後來弟弟告訴我,那次爸爸以爲我在房裡自殺了。我覺得真是好玩,捧著肚子笑彎了腰,剛歇了口氣看見弟弟站在一邊嚇呆了的樣子,又忍不住大聲笑了起來。
我並不是覺得自殺有什麼好笑,相反地我一直認爲那是天下頂可怕的事,我只是笑爸爸這種想法太傻。我六科不及格的成績單,本來可以不要拿給他看的,只是我覺得那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而且我本來就不想念書。可是拿給他看了他又要發脾氣,最後又怕我自殺,這實在矛盾得好笑。
我說起這件事就是證明人本來是可以快快樂樂的,那些人不快樂大概就因爲他們都像爸爸一樣想的太多,而想的偏又全是些矛盾古怪與活下去沒干係的事。
喬蔓春也一樣,有時候我勸她好好打扮打扮,她反而說我嫌她邋遢就不要跟她玩好了,我就得趕緊跟她陪不是。我不願意爲這種小事得罪人,可是事實上我實在看不慣她那副德性:洗臉永遠只洗前頭一個平面,耳窪裏的泥垢可以孵豆芽菜了。她卻說只要別人欣賞她的思想就夠了,那才是永恆真實的,外形遲早要腐朽。
這個思想。我就覺得那些成天思來想去的傢伙,全是第一號的大傻瓜,死了還談什麼永恆真實的。
喬蔓春這種人我也真服她,我一直認爲女孩子第一要件就是打扮,也並不是要濃妝豔抹得像唱歌仔戲,能讓男人看著喜歡就夠了,否則像喬蔓春那樣成天蓬頭垢面的無人問津,要我三天就悶死了,說不定她想自殺就因為這個原因。不過我也沒辦法,有回我叫小強替她介紹一個,小強舌頭伸得老長,扮個鬼臉,跑了。
小強現在不知道跟誰玩,大概是黑貓。
我認得他之後就沒有再跟班上那些男孩子在一起玩了。黑貓說我可攀上了一個大學生。我倒覺得大學生也沒什麼了不起,有時候還覺得盡愛講些怪話。
有一次,在田園裡坐得好好的,他忽然嘰嘰咕咕地唸了一大串怪東西。我問他在說什麼,他說忽然想起一個法國詩人叫史蒂芬什麼赫梅的幾句詩。我根本沒興趣聽什麼詩呀詞呀的,好好的話全給他們搞糊塗了。不過我很懂得怎樣能讓別人跟我在一起感到和諧和快樂,而且當時在田園裏我實在也悶得無聊。我就說我不懂法文,要他翻譯給我聽,他興奮得在襯衫口袋裏掏出了一張皺皺的紙寫了起來。他的字很漂亮,看起來很秀氣的。可是他字寫得很慢,一筆一劃都勻勻整整地寫。我在旁邊一面看他寫一面就背了起來。現在還記得:
於陌生的泡沫和天空之間
沒有什麼能留住那迷醉於海的心
夜呵!月光裏反映的古老花園不能
被純白遮掩的空白紙張
寂寞的燈光也不能
給嬰兒哺乳的少婦也不能。
我將離去,搖曳著桅杆的小舟呵!
啟碇吧,向異邦的自然
煩倦,因殘酷的祈望而感傷的
依然迷信於揮巾的告別。
我根本不懂裏面在說些什麼,不過我還是耐心地低聲唸了幾遍給他聽。他說我的聲音好美,又說不知道像我這樣開朗又無拘束的女孩子,也能讓他有寂寞和憂鬱的感覺,我就低低地應了一聲:「是嗎?」其實我心裡好想大大地笑幾聲。
他們這些大學生都有點神經兮兮的,成天說些寂寞呀、憂鬱呀、蒼白呀的話。又喜歡到這種烏漆墨黑的地方聽那種一下子喪裏喪氣、一下子又轟隆轟隆的怪曲子。
有時候我想還是跟小強他們在一塊兒玩的好,那樣在西門町大街上逛來逛去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拾掇今天的頭髮跟服飾不至於全派不上用場的糟蹋了。而且小強他們去的地方總是熱熱鬧鬧的,不像田園這樣陰森鬼氣。
我喜歡猴子舞那樣快節拍的曲子,瘋狂得讓人不會打盹,我一靜下來就想瞌睡。上次帶他去維納斯想學兩手剛上市的阿哥哥舞,偏他就淨揀三步四步的跳,磨來磨去的膩死人。跟小強他們在一起我從來就沒覺得膩過,他們總會發明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去玩的。
不過小強他們也有些怪毛病,老愛動手動腳的。有一回,一個傢伙才跟他一起玩過兩次就不規矩起來。我很想學電影上女明星對付色狼那樣狠狠摑他一個巴掌,可是又覺得那樣他一定會很難過,說不定就會去自殺或做和尚,那我一定也會傷心的,所以我就沒理他。誰知這傢伙愈來愈猖狂。我就用腳一勾把前面的小茶几絆倒,嘩的一聲,所有的人全往這邊看,他也著實嚇了一大跳。服務生來收拾東西的時候,我盯著他瞧了半天,他臉一直紅到脖子根,滿頭都是汗珠子。後來他就再也沒來找我。
其實他們這些十六、七歲的男孩子,都沒什麼壞心眼,只是太毛裡毛氣吧了。
還有一次,我跟小強去看電影。看完了我說時間還早再去趕另一家的,小強怪裡怪氣地答應著,然後說他去買點吃的叫我在戲院門口等他。我站著無聊,就老遠跟著他走,誰知道這傢伙竟然跑到當鋪裏去了。他出來的時候,我看他口袋裡的鋼筆不見了。我在他身上找到了那張當票幫他贖了回來,然後請他看了那場電影。他不好意思地說我真好。
他們這種年紀的男孩子,就這麼傻氣得好笑又可憐。
跟他在一起我是從來不操這麼多心的。他比我大,而且他說他喜歡別人什麼都順著他,我就什麼都順著他了。
我跟他在一起很少講話,因為他老是靜靜的,我總不好意思緊纏著他說東說西呀。
就那一次在田園,他跟我說了好多。說他好希望有一條船,那怕是極小的。他一直夢想著有一天能到海上去流浪,載著畫架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畫那裏天的顏色、水的顏色。還有一個乖乖的小女孩在每個清晨把他吻醒。
他說他爸爸罵他在發瘋,我覺得那實在是句好話。不過他當時把我的手捏得好疼,所以當他問我是不是願意做那個乖乖的小女孩時,我就答應了他。可是那時候我是沒有想到真會跟他跑到海濱來住的。
這個夏天,他有四個月的假,而我聯考落了榜。雖然我不在乎,可是爸成天拉長著臉,媽是嘮叨不完的話,所以我想還是跟他來這海濱住愜意些。不過我給家裏講是說我到黑貓家住的,爸如果知道我跟一個大男人在一起渡假,一定會氣得暈倒。
他們就是那樣大驚小怪,其實我還不至於那麽呆瓜。雖然我並不認爲跟一個男人睡在一張床上有什麼關係,那是遲早總得來的事。不過我也很清楚那玩意兒就是女孩子的本錢。
我跟他來的時候就在擔心他如果只租一個房間的話怎麼辦。我就跟他說我有肺病需要隔離?不行,他一定不相信,我這麼壯。就說我習慣了一個人住一間房的好了,我想他會聽我的。
結果我根本什麼都沒說,他就租了兩間房。跟他在一起真的什麼也不用操心,他想得比我多得多。
第一天晚上,他帶我到一個小水灣的地方去玩。那天晚上的星星又多又乾淨,一顆顆都是白爍爍的,望久了覺得竟像有好多紛亂的聲音在聒噪,像一樹蟬鳴。
漁船出海的時候好美,船底招魚的燈黃溶溶的光暈在水面灘成一片,好像,好像⋯⋯我不知道好像什麼,就是很迷人就對了。
我穿了一件紅皺紋的兩截泳衣,身上披了一條大毛巾,可是還是覺得有點涼颼颼的。
他一直沒開口,我以為他睡著了。後來才發現他的頭是豎著的,而且眼睫毛眨一下。他爬在沙灘上下顎墊著肘,好像一點也不冷。我把毛巾愈圍愈緊了,冷得縮成了一團。
他只穿了一條白色的平腿泳褲。我第一次看他穿得這麼少。他的腰很好看,扁扁平平的,一點都沒有別的男人那種贅肉太多的感覺。我告訴他說他的腰看起來很性感,他轉過頭來一直盯著我瞧,好可怕的樣子。我記得電影上男人要動粗之前,好像就是這個樣,我就趕緊跳了起來沒命地跑,然後把房門鎖得牢牢的。
第二天一早他來敲門的時候,我還睡在床上。他說帶我去看日出,其實太陽早爬得老高了。昨晚的事他一句也沒提,好像根本沒那回事,我也很快就忘了。
早上的太陽暖絨絨的。我把頭枕在他的臂彎上抓著沙子玩。他身上有一種很濃重的氣味,好像是菸味跟汗臭混合的味道,不過還蠻好聞的。他抽菸抽得凶,可是他抽菸時的樣子很好看,有點中年人的穩重。我有時候躲在房裏也抽抽菸,嗆死人,一點味道也沒有,男人實在很怪。
他心血來潮地說要幫我畫張畫,我說好呀,他就跑回去拿畫畫的東西去了。
我從前沒看過他畫畫。有一次他帶我到海天畫廊的五樓去看什麼現代美術展,滿房子全是怪怪的東西,把人的臉都畫得好長好長,還淨題些少女呀、詩之圓舞曲呀這樣美麗的名字。有一幅叫《作品A》的畫塗著一圈又一圈的紅螺紋,他站在那幅畫前面看了半天都不走,我也照他那樣子歪著頭看。可是愈看愈頭昏,我就乾脆跑到走廊上去看台北的街景了。
我在那兒站了好久他還沒出來,進去一看他在跟一個頭上戴一個黑髮箍的女孩子指著那幅叫《作品A》的畫聊天。後來我問他那個女孩是誰,他說是他從前的一個女朋友。我覺得這倒蠻有意思的,就問他從前是不是有很多女朋友,他說是的,又說他從前的女朋友都是喜歡詩呀詞呀的那種乖女孩,可是每個都玩不久。
「她們太彆扭、太拘謹、太造作,跟她們在一起只能感染到痛苦和不幸,不像妳這樣灑脫,不讓人煩心。」
這是他說的。就是那一次,他說如果全世界的女孩子都能像我這樣不讓人煩心就好了,我真的很高興,不過我也有點爲那些女孩子難過。我想我一定要把這件事告訴喬蔓春,叫她不要再這樣愁兮兮的了,男人不欣賞這樣的女孩子。
我在太陽底下坐了好幾天,他才完成了那幅畫。還好沒有把我的臉畫得好長好長,不過我已經沒有心情去欣賞了。我渾身的皮脫得像頭梅花鹿,我問他我現在是不是好醜,他說一點也不,不過我還是不相信,我自己看了都噁心。以後我上海灘就戴一頂大大的大甲蓆草帽,抹好多橄欖油,然後再披上大毛巾。
這以後他就開始了做船的工作。他在附近村民那兒買了一塊一尺長的木頭樁子,用刀削尖了一頭,再用雕刻刀在中間挖了一個槽,然後用砂紙把裏外磨得油光油光的。我記起了他從前說他一直都希望有艘船的話,可是這船那麽小,所以我想他是做著玩的。
現在他坐在我腳前給船身上彩色。他說要塗上白色和紅色的斜紋,在船尾上裝上一面小旗,用藍色寫上他的名字:項南。
「項南。我們回去好不好?我簡直要被烤焦了。」
我這說的是真話,我把身上撕下來的皮捲搓著玩的時候都覺得有些糊味了。
「我一直希望有艘船。」
「老天,你已經說好幾遍了。」
「那怕是條極小的。」
這也講過好幾遍了,從開始做船的那一天起就說個不停,我才發現他這個人實在有些健忘。
我把嚼苦了的口香糖吐在掌心上揉成一個小疙瘩,朝他後腦門上扔去。他一樣不理不睬。我實在有些火大了,乾脆不理他一個人跑回旅社去了。
旅社裏有我一封信,是黑貓的。拆開來一看,頭一句話就像一聲巨雷一樣擊下來,半晌都還嗡𠾐嗡𠾐地響。
喬蔓春自殺了,割腕。
「天,多可怕。」
我把信紙捂到臉上。彷彿嗅到了濃濃的血腥,又看了那翻捲開來汩汩出血的蒼白手腕。
「怎麼會?怎麼會?」
(內文節選)
希望我能有條船
「我一直希望能有條船。」
天氣很熱,身上曬脫了皮的地方又隱隱作痛,以致我根本沒注意他在說些什麼,反正也不會是重要的話。我們在一起好像從來也沒說過什麼嚴肅的話,只有一次他說如果全世界的女孩子都能像我這樣不讓人煩心就好了。我想那也不見得是什麼頂重要的話,不過我後來就一直沒忘掉,而且想起來就有點開心。
事實上,除了這句話之外,也沒有什麼可以使我記起的。每次跟他出去他總是稱讚一聲妳的衣服好好看,或者妳今天頭髮梳得很漂亮這些話。而這些話又是每一個跟我一塊玩的男孩子都說過的,所以我就...
作者序
文青時代
母親講的故事
童年時記憶最深的是母親講的故事。
母親喜歡看戲、讀很多演義小說,《封神榜》、《七俠五義》等等。她也愛聽民間說書,「武松打虎」、「白蛇水漫金山」,都是她童年和文青時代聽來的。她說:「西安城城門口有說書的瞎子,說武松打虎,一個拳頭要打下去,講了好幾天。」
所以,那時代的文青,或蹲或站,在城門口,丟一兩個銅板,聽一晚上的「水滸」、「三國」。
聆聽來的故事,是聲音的記憶。我最早的文青故事,伴隨著母親的聲音。聲音有抑揚頓挫,有許多激動或平靜的呼吸,有敘述一個故事時人的溫度。
我現在記得白蛇許仙在斷橋告別,敘述那一段,母親的聲音裡有多少白素貞的委屈,有多少對法海的厭恨。
母親是愛說故事的,她在戰亂裡東奔西走,其實很受顛簸磨難,然而,她說起故事來,儼然又是那個站在城門口聽瞎子說「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文青少女。
人類的古老文明裡,好像一開始都是聽覺的傳唱。還沒有文字,所以,荷馬史詩「特洛伊」的故事是傳唱,印度教《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的故事也是傳唱,連最早的《詩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也是傳唱。
還沒有文字,所以聲音可以那麼好聽。沒有文字,所以學會了聆聽。也把聆聽來的故事,再重複傳唱出去。
詩的歷史,文學的歷史,文明的故事,都靠著口口相傳,傳唱在山邊海域,傳唱在大街小巷,傳唱在窮鄉僻壤。
我在南王部落,卑南的男男女女唱歌都好聽。或許是因為部落傳統沒有文字,他們的歷史就是歌聲。
一代一代的文青接力,把美麗的故事傳唱下去。
我識字以後,學習慢慢閱讀。漢字的閱讀,需要一點時間,比較累。我還是依賴著母親的聲音,央求她說故事給我聽。
小學五年級,我開始獨自閱讀了,在學校圖書館閱讀一本《愛的教育》,內容全忘了。
為什麼母親用聲音講述的故事到現在我都清晰就在腦中?聲音的委婉跌宕起伏,似乎比視覺文字更讓我迷戀。
小學五年級,母親知道我喜歡聽故事,就帶我到衡陽路,買了一本《希臘羅馬神話集》。
我很喜歡讀那本書,讀維納斯從海洋的泡沫裡誕生,讀宙斯化身成天鵝,愛戀美女麗妲,生下兩個天鵝蛋。
那似乎是我閱讀形式文青的開始,但是沒有母親的聲音,到現在,希臘神話的故事似乎都像默片。
我後來學著用母親講「白蛇傳」的聲音講伊卡洛斯(Icarus)飛起來的夢想,他是少年,像所有的文青,都夢想飛起來。然而他的羽毛翅翼是用蜂蠟黏合的,愈靠近太陽,封蠟融化愈快。羽毛飛散,他從高空墜落,摔死了。
我總覺得伊卡洛斯是第一個摔死的文青,摔死在自己過度的夢想裡。
他的翅翼其實無法承載那麼沉重的夢想。
保安宮廟口的文學、音樂、美術與戲劇
我從大龍國小畢業,但是,回想起來,小學時影響我最大的,不是學校,而是保安宮這座廟宇。
大龍峒是同安人移民建立的社區,同安人從故鄉帶來大道公的信仰,信奉保生大帝,保護同安人,因此有一座傳承久遠的保安宮。
大龍國小在保安宮的東側,每天走到國小上課,一定經過保安宮。有時是直接從廟宇後門進入後殿,後殿一排,祀奉神農、文昌、武聖,東北角落還有一幽暗空間,據說是祀奉最早從故鄉帶來的保生大帝的像。神像很小,據說是移民來台,揹在身上,一路護佑。
後殿往前走,東、西兩側各有一條長廊。長廊圍繞正殿,隔著大約兩公尺距離,剛好可以瀏覽正殿東、西、北,三面的壁畫。壁畫的內容與宗教信仰無關,多是野台戲演出的人物,有「花木蘭從軍」,有「徐庶的母親用硯台擲打勸說兒子叛節降曹的使者」,有虎牢關「三英戰呂布」的三國故事,也有民間家喻戶曉的「八仙過海」。
小學時很喜歡這些壁畫,喜歡藍采和、何仙姑、韓湘子的俊美優雅,很有文青氣質。但不很了解為什麼跛腳的李鐵拐,駝背佝僂倒騎毛驢的張果老,大肚便便的漢鍾離也可以位列「八仙」。
文青畢竟有文青的限制吧,當時也曾看著畫師坐在木梯上,一筆一筆勾畫人物眉眼,手法熟練,回頭問我:「愛繪圖啊……。」我點點頭。後來畫完成了,畫師走了,看到他在畫上留的名字:台南潘麗水。
我最早的美術功課無疑是保安宮的壁畫,雕刻的石柱、獅子,屋簷下栩栩如生的交趾陶「呂布戲貂蟬」,還有燦爛陽光下閃閃發亮的彩瓷剪黏的龍鳳,都在高高屋脊上振翅欲飛。
一九五○年代,廟宇的西廂住了很多家戰爭難民。在廟檻下簡陋拉幾條布,就住著一家人。
我同班同學也有住在裡面的,陰暗狹窄。早上去學校,也會竄進去找同學,叫他們的名字「羅金!」「羅英」,或是外號「白狼!」
難民遷走以後,那些同學就星散了,其中有人成為詩人,也有人參加幫會,成為頗有名的大哥。
西廂整理乾淨,重新安置神龕神像,就是現在香火頗盛的「註生娘娘」殿。
保安宮有南管的班子,黃昏時三三兩兩,在榕樹下彈唱,聲音悠揚。老樂師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曲牌〈泣顏回〉,下面是我看不懂的工尺譜。
笛簫琵琶吹奏,有人站起來,清一清嗓子,委委婉婉吟唱起來。
那是我童年記憶最美麗的聲音,要在好多年後,去了巴黎,聽到一張法國文化部出的CD,是台南南聲社蔡小月主唱,封面上用字母拼音:NanGuan。
比南管更讓兒童蜂擁向廟口的是亦宛然的布袋戲,那時候沒有人認識李天祿何許人,但是唱詞、道白、動作都讓人迷戀。孩子們很快學會了,也在家扮演起來,用吃完的芒果核,切成兩半,畫了臉,手指套在中空處,咿咿啞啞,開始成為亦宛然的粉絲。
保生大帝壽誕前後,廟口大戲台會連演一兩個月的野台戲。
最重要的節日,總是三台戲班聯演,一樣的戲碼《陳三五娘》、《武家坡》,三個戲班同時演同一齣戲。我們在台下跑來跑去,真是好看。大家都不服輸,聲腔愈飆愈高。那一個戲班喝采最多,立刻放鞭炮,貼出一人高的賞錢。三台戲班如此競賽,觀眾也忙壞了,東看西看,目不暇給。
那是我文青時代最早最早的記憶,看著扛神轎的壯漢,赤足走火,火炭熊熊,大約一百公尺,不斷有人撒鹽,火焰爆出火花,四名赤膊男子,扛神轎起伏升降,踏步若在雲端。後面跟著乩童,用鯊魚劍擊打背部血跡斑斑,「啊……」我認識那乩童,比我年長,六年級,已經有落腮鬍,深目濃眉,常常無緣故跑來緊緊抱我,又一溜煙跑走。
「陳俊雄」,我記得他的名字。
我考取初中,穿著制服,走過廟口。
一個粗粗男人聲音叫我的名字,我回頭看,「陳俊雄」。
他騎著腳踏車,幾串剛肢解的豬肉,掛在把手上。「我在市場幫爸爸賣豬肉。」隨手拿了一串,用姑婆芋葉子一捲,塞在我手裡,又騎著車一溜煙走了。
我們好像沒有再見過面,或者,見過,在廟口或市場擦肩而過,可是容顏改換,還會認出彼此嗎?
走過保安宮,還是會習慣站在兩隻守門石獅子前,回想童年夏天,光著上身,趴在石獅子背上午睡,胸口都是石頭的沁涼。
廟會最熱鬧的幾天,會有其他鄉鎮的乞丐,或盲或跛,一身癩痢,坐在泥汙地上,一個破碗,咿啞唱著《陳三五娘》或《秦香蓮》,哀怨委屈,是長大以後在世界輝煌的劇院都再也聽不到的。
保安宮入口那幅正門兩邊的楹聯都還記得:
保世極其誠,誠以真而無妄。
安人盡乎道,道至大而皆亨。
這是嘉慶年間大龍峒讀書人留下的詩句,在文化移民的邊陲,知道信仰萬世不移的基礎是「保世」、是「安民」。文青刻意做作,不容易讀懂這些平實的文字。長大以後讀《易經》,有些深奧難懂處,回想廟上聯語說的「無妄」,「亨」,生活裡,無非希望「無災無妄」,希望事事「亨通順利」。到現在,易經卜卦,還是祈求「無妄」,祈求一個「亨」字。
文化若是貼近萬民的哀樂,也就沒有文青的矜持,恭恭敬敬在「大道公」門口合十敬禮。
木柵的師大附中
中學時,我成為很徹底的文青,寫詩,讀小說,辦壁報,編校刊,無端憂愁。距離「陳俊雄」在市場幫父親賣豬肉愈來愈遠。小學同班的同安人同學升學的不多,走入生活,成為菜販、漁民或勞工,階級懸殊,見面尷尬,也慢慢淡忘了。
我考上的初中是師大附中,但是不在台北本部上課,每天要從當時北區的大龍峒到最南邊的木柵鄉下上課。
這件事現在沒有人了解了,連師大附中的師生可能也甚少人知道師大附中在木柵有一個「分部」。
五○年代,台灣還在做隨時戰爭的準備。台北的學校,可能因為戰爭爆發,要遷校到鄉下。所以師大附中有「木柵分部」,北一女有「新店分部」等等。
「分部」都選在偏僻有山有水的地方。記得木柵分部四野都是農田,遠處盡頭是連綿不斷的山,進校門有一段沿著溪水的竹林,幽靜而美麗。
「分部」的學生,只有星期一週會要到校本部,一起唱校歌:
附中,附中,我們的搖籃。
滿天烽火,創建在台灣。
玉山給我們靈秀雄奇,
東海使我們闊大開展。
我們來自四方,融匯了各地的優點……
因為每週一次回校本部,我至今還可以唱起附中校歌。
我們每學期也會收到《附中青年》,裡面許多詩和散文是我文青時代的養分,後來《附中青年》出事,據說有老師是「匪諜」被逮捕。白色恐怖的年代,這樣的事,像小石子丟進汪洋大海,很快就無聲無息。
然而我很懷念木柵那個沒有圍牆的「分部」。美術老師是杭州藝專的李文漢,看我畫的人像,一節課站在我身邊和我講敦煌莫高窟的藝術,同班同學一一溜走,跑到戶外玩耍。以後每次美術課,同學都央求我給李老師看畫。
國文老師芮霞,新婚,很美,課外教我填詞,〈虞美人〉、〈相見歡〉。
忘了名字的歷史老師是我的偶像,講到宋朝,可以一口氣背誦好幾首蘇東坡的詩詞文章,口才流利,也是性情中人。
英文老師朱詩蘋,每堂課逼我背五個單字。這麼簡單的事,可我不願意就範,文青叛逆,常被罰站。
我數學一直不好,小學算雞兔同籠,兩隻雞一隻兔在籠裡,問有幾隻「腿」,我反問老師:「為什麼要把雞和兔關在籠裡?」數學因此不及格。
數學老師是教務主任兼任,一個廣東口音的婦人,長年穿黑旗袍,外號「鐵公雞」。
我的母親家長會到學校總是質問「鐵公雞」:「我兒子為什麼數學不及格?」
我很喜歡這個在山水環抱裡的木柵分部,戰爭一直沒有發生,雖然發生了八二三砲戰,還是覺得戰爭很遙遠。
八二三砲戰那年,我出車禍,住在醫院。同病房有一個少年,全身燒傷,用紗網蓋著,呻吟氣息微弱,護士說是「八二三」受傷從金門送回。我第一次聽到「八二三」,戰爭對「文青」如此遙遠,痛苦呻吟戰爭燒傷的身體卻近在咫尺。
沒有圍牆的學校,天空常有鷹隼盤旋,或者俯衝而下,叼起長蛇,電光火石,迅如閃電,即刻遠颺成一小點。
另外一個愛上木柵分部的理由是離家很遠,要從底站的大龍峒做2號公車到衡陽路,再轉零南公車到木柵。專車的衡陽路站下車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我如獲至寶,每天下課後,都要在附近書店逗留看書,逗留最多的是重慶南路衡陽路口轉角的「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
五○、六○年代的重慶南路書店一家接一家,真是喜歡閱讀的文青的祕密花園。
好像當時學校和縣市的圖書館都還不發達,喜歡閱讀,只有靠書店。
小學時候,班級導師王什麼財,就在蘭州街派出所旁搭一個違建的篷子,租漫畫書給小朋友看。每個星期三是新的《漫畫大王》出刊,小朋友就等著矮小瘦黑的王老師騎車帶剛出爐的《漫畫大王》回來。一本五毛錢。看完收回,還有人在等。那是葉宏甲「諸葛四郎」、「真平」的年代。派出所警察有時也過來看,不多久,王老師的自行車也換了摩托車。
「諸葛四郎」,現在想想,是頗受日本文化影響的漫畫。裡面的「哭鐵面」造型也直接來自日本傳統能劇面具。
五○年代末到六○年代初,重慶南路的書店風景和蘭州街口的《漫畫大王》不一樣了。
記憶裡,很多從大陸遷台的老書店,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開明書局、商務印書館、東方出版社……。
因為從大陸遷台,帶來很多三○年代中國新文藝思潮翻譯的西方著作。
三○年代許多優秀的作家左傾,國民政府遷台,這些作家「陷匪」,著作多成禁書。那個年代,魯迅、沈從文、巴金……都看不到。但是,書店經營者,改頭換面,會大量出版翻譯作品。巴金翻譯過不少法文小說,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有《約翰·克利斯朵夫》,有《巨人三傳》。記得是素白封面,一條黑底反白字書名,風格很強,素樸平實,到現在還是覺得是值得懷念的美學設計。
重慶南路書店街,一家一家逛,很有看頭。
當時詩人周夢蝶在靠近重慶南路的武昌街擺書攤,一襲黑衫,瘦骨嶙峋,像在冥想,也像在打盹。強烈的城市風景,看了一生都難忘。
那是我青少年時的台北。戰爭結束十幾年了,我的身體正在發育。有自己不知道的焦慮苦悶,在書店亂翻書,翻久了,被老闆罵:「買不買啊……。」
他說到重點,那時候真的沒有買書的錢。這家老闆給了臉色,只好到下一家。最後經常看書的地方是「東方出版社」,老闆不趕人,可以安心看書。
《簡愛》、《咆哮山莊》、《傲慢與偏見》,從英國浪漫主義的小說,看到法國的《基督山恩仇記》、《鐘樓怪人》、《悲慘世界》,再看到俄國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一本一本看,下了課就坐車到衡陽路重慶南路口,鑽進書店,站著看,看到忘了時間,知道再不回家要挨打了,趕緊在書頁上折一個角,放回書架。
第二天沒心思上課,總想著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車上遇到軍官,電光火石,不知會如何。
小說這麼迷人,學校的課程如此無聊。每次月考成績都一塌糊塗,家裡責備,學校處罰,可是上了癮,還是戒不掉去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拆除了,重慶南路許多書店消失了。
我站在東方出版社前哀悼過,曾經有一個地方讓「文青時代」的我滿足夢想。
學校或家庭的責備處罰都不算什麼。浪漫主義文學裡都在說人的抗爭,磨難挫折、被世界遺棄、孤獨出走,每一本小說的人物都不屑與世俗妥協。
「文青」的核心價值就是「叛逆」吧……。
這麼容易向威權屈服,這麼容易走大家都走的路,這麼趨炎附勢,哪裡有資格說自己是「文青」?
木柵分部是一所升學率極高的初中。三年成績夠好,直接保送進師大附中高中部,其他參加聯考,也都考進省立高中。
記得我畢業那一屆,只有我和四名同學落榜,去考私立中學。
我因此進了一個奇怪的高中「強恕中學」。
(內文節選)
文青時代
母親講的故事
童年時記憶最深的是母親講的故事。
母親喜歡看戲、讀很多演義小說,《封神榜》、《七俠五義》等等。她也愛聽民間說書,「武松打虎」、「白蛇水漫金山」,都是她童年和文青時代聽來的。她說:「西安城城門口有說書的瞎子,說武松打虎,一個拳頭要打下去,講了好幾天。」
所以,那時代的文青,或蹲或站,在城門口,丟一兩個銅板,聽一晚上的「水滸」、「三國」。
聆聽來的故事,是聲音的記憶。我最早的文青故事,伴隨著母親的聲音。聲音有抑揚頓挫,有許多激動或平靜的呼吸,有敘述一個故事時人的溫度。
我...
目錄
【自序】文青時代
【輯一】夢裏青春
希望我能有條船
歲月女人
勞伯伯的畜牧事業
荷
藤蔓
好鼓聲!—記雲門舞集春季公演
相親
青青河畔草
【輯二】一餉貪歡
告別自己的文青時代:當我把愛當成了習慣
齊克果速寫
卡夫卡速寫
卡繆速寫
相尋夢裏路,飛雨落花中
【特別收錄】
詮釋
蔣勳作品
一顆小石子
一朵小花
【自序】文青時代
【輯一】夢裏青春
希望我能有條船
歲月女人
勞伯伯的畜牧事業
荷
藤蔓
好鼓聲!—記雲門舞集春季公演
相親
青青河畔草
【輯二】一餉貪歡
告別自己的文青時代:當我把愛當成了習慣
齊克果速寫
卡夫卡速寫
卡繆速寫
相尋夢裏路,飛雨落花中
【特別收錄】
詮釋
蔣勳作品
一顆小石子
一朵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