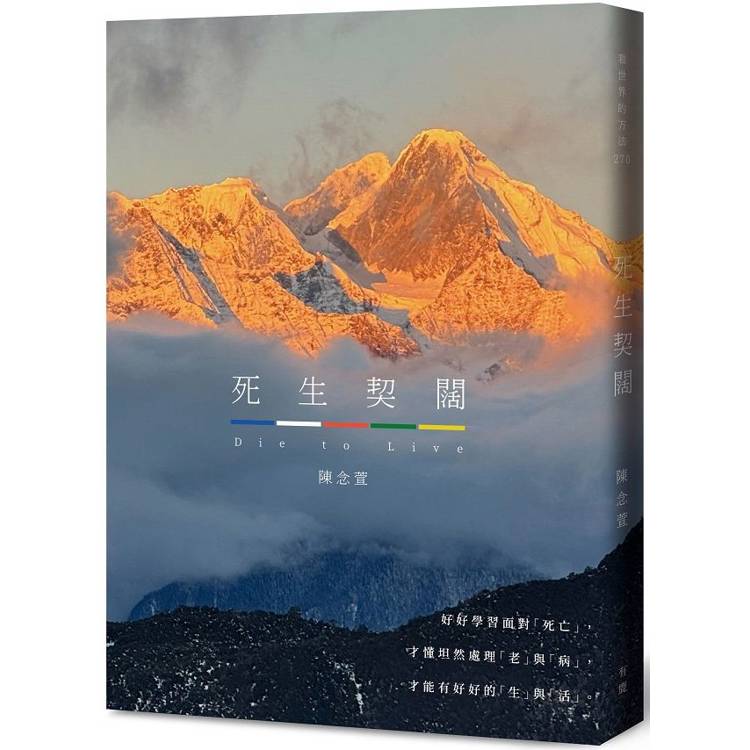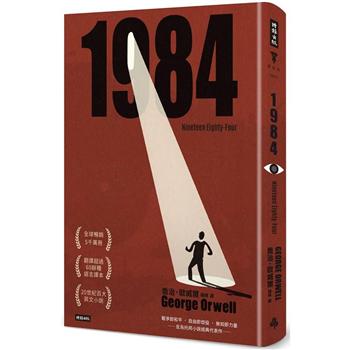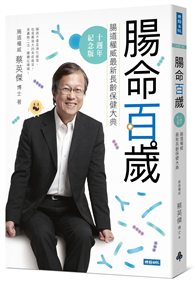好好學習面對「死亡」,
才懂坦然處理「老」與「病」,
才能有好好的「生」與「活」。
生死,是人最珍貴的禮物。
因為死亡終將來臨,我們得以為此思索:
「我還能為自己與他人的生命做些什麼?」
因為死亡終將抵達,我們得以在有限的時間內,
為自己創造「生」之甜美的最大值。
★作家陳念萱全新動人書寫,覺知「生」的剎那與恆常,直面「死」的溫柔與慈悲
★許悔之(有鹿文化社長.詩人.藝術家)專文感動推薦
屍體的靈魂真的不在,那是空殼子──
在死亡面前,我們只能保持純粹的信心
才懂坦然處理「老」與「病」,
才能有好好的「生」與「活」。
生死,是人最珍貴的禮物。
因為死亡終將來臨,我們得以為此思索:
「我還能為自己與他人的生命做些什麼?」
因為死亡終將抵達,我們得以在有限的時間內,
為自己創造「生」之甜美的最大值。
★作家陳念萱全新動人書寫,覺知「生」的剎那與恆常,直面「死」的溫柔與慈悲
★許悔之(有鹿文化社長.詩人.藝術家)專文感動推薦
屍體的靈魂真的不在,那是空殼子──
在死亡面前,我們只能保持純粹的信心
作家陳念萱全新動人書寫,記敘自己在一甲子的歲月裡,如何與至親好友的死別中看見生機。來回尼泊爾三十三年,她走過印度、不丹,於信仰中穿越,藉由修行翻解佛法,體悟「生」與「死」之瞬息萬變、之雋永恆常。
「經常有朋友問我,該如何面對瀕臨死亡的親友?常年駐居紐約的師父曾經告訴我,「相信」,是最重要的質素,信什麼都好,不必然一定相信佛,只要信,相信本身會帶來救贖⋯⋯」—陳念萱
「我看《死生契闊》,生起一種信心:死亡之終將必來,使我們此生願意或可能去學會不以世間「相對而有」的態度和價值觀去活,因此能夠『心莊嚴,得自在,常喜悅』。」—許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