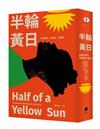當新生的國家被戰火碾碎,他們仍然渴望著愛……
橫掃國際大獎,翻拍同名電影
非裔天才女作家阿迪契書寫祖國內戰的史詩之作
★★全球女性作家最高殊榮「女性小說獎」得主(2007)★★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作品(2007)★★
★★「麥克阿瑟獎」得主(2008)★★
★★《時人》雜誌、《紐約時報》年度好書★★
「比亞法拉共和國或許消失了,可是幸好有阿迪契,比亞法拉不會被遺忘。」
一九六七年爆發的奈及利亞內戰,將這個國家撕裂成了兩半。在戰爭前,厄格烏是一名來自貧窮村莊的男孩,他在大學講師歐登尼伯的家裡擔任僕人;歐登尼伯的戀人歐拉娜出身奈及利亞的上層階級,她卻拋下優渥生活,和抱持革命思想的歐登尼伯同居;而理查,一位內向的英國人,則深深為歐拉娜神秘的雙胞胎姊妹凱妮內所吸引,並一步步建立了對伊博族的認同。
隨著豪薩族和伊博族的衝突愈演愈烈,伊博族宣布從奈及利亞獨立,成立比亞法拉共和國,內戰頓時爆發。他們的生活被徹底顛覆,分崩離析,只能在殘缺的愛中尋找希望……
《半輪黃日》是阿迪契在世界文壇奠定地位的代表作,她以細膩無比的洞察力,宏大且充滿野心的架構,將這場被世人遺忘的戰爭,和比亞法拉的國家命運,編織到她筆下栩栩如生的角色和故事中,使讀者為他們的處境時而揪心,時而感動。
這部小說精彩描繪出奈及利亞內戰中不同階級、種族、宗教、族裔、性別的人們的樣貌,也觸及後殖民、傳統文化、道德責任等議題。阿迪契不僅用文字讓比亞法拉重現世人眼前,隨之重生的還有人性和愛。
作者簡介:
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1977年生於奈及利亞埃努古市,在恩蘇卡的奈及利亞大學校園裡長大。19歲時到美國,並拿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耶魯大學碩士學位。她是當代最知名的非洲作家之一,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三十種語言。她的小說《紫色木槿花》(Purple Hibiscus)榮獲不列顛國協作家獎(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以及赫斯頓/賴特遺產獎(Hurston/Wright Legacy Award);《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獲得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贏家中的贏家」獎(Winner of Winners);《美國佬》(Americanah)獲得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她還著有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文集《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以及《親愛的伊傑亞維萊》(Dear Ijeawele, or A Feminist Manifesto in Fifteen Suggestions)。她是2008年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得主,2015年入選《時代雜誌》的百大人物。目前在美國及奈及利亞兩地生活。
譯者簡介:
葉佳怡
台北木柵人,曾為《聯合文學》雜誌主編,現為專職譯者。已出版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有非虛構作品《向獨裁者說不》、《永遠的蘇珊》;小說作品《消失的她們》、《聲音與憤怒》、《寂靜的緯線》;人類學作品《卡塔莉娜》、《尋找尊嚴》等。
章節試閱
第一部 六○年代初期
一
主人的腦子有點不正常。他有太多年的時間在海外讀書、常在辦公室裡喃喃自語、不見得每次都回應別人的招呼,毛髮也太過旺盛。厄格烏的姑姑在他們一起走上小徑時低聲這麼說。「但他是個好人,」她補充。「只要好好工作,你就能吃得很好,甚至能每天吃肉。」她停下腳步吐口水,那抹唾液伴隨著一陣咂嘴聲飛離她口中,落到草地上。
厄格烏不相信有誰可以每天吃肉,就連他即將一起住的這位主人也不可能,不過他沒反駁姑姑的說法,因為他已滿懷期待地說不出話,腦中也忙著想像自己離開那座村莊後的全新人生。此刻的他們自從在轉運站步下卡車後已經走了一陣子路,午後陽光灼熱地燒著他的後頸。可是他不在意。他甚至已經準備好要在更炎熱的陽光中走上好幾小時。自從他們經過大學大門後,他看到以前從未見過的街道出現在眼前,這些街道如此光滑,還鋪著瀝青,他真的好想把臉頰貼上去。他永遠無法向他的妹妹雅努利卡描述這裡的獨棟平房是如何漆上了天空的顏色,而且還像衣著體面的禮貌男人站成一排,也無法描述分隔這些房子的樹籬頂端修剪得多平整,看起來就像包上葉片的桌面。
姑姑走得更快了,她的涼拖鞋在安靜街道上發出啪、啪的聲響。厄格烏心想,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能透過薄薄的鞋底感覺到地面的煤焦油越來越熱。他們經過一個路標,路標上寫著歐丁街,厄格烏用嘴型安靜讀出街名,他每次只要看到不會太長的英文字都會這麼做。他們走進一座住宅區,他聞到某種香甜、猛烈的氣味,確定是入口處一叢白花散發出來的。這些花叢的形狀就像一座座細瘦的山丘、草坪閃閃發亮,許多蝴蝶正在上方盤旋。
「我告訴主人,你什麼事都學得很快,osiso-osiso,」他的姑姑說。這件事姑姑已經跟他說過好幾次,但厄格烏聽了還是專注地點點頭,她也常說他能獲得這份工作有多幸運:她一週前在掃數學系走廊的地板時,聽見主人說需要一名家務男僕來幫忙處理清潔工作,於是立刻趕在他的打字員及辦公室收發員還來不及開口表示可以介紹人之前,就先說她可以幫忙。
「我會學得很快,姑姑,」厄格烏說。他盯著車庫裡的車子看,有條金屬鍊子如同項鍊一樣環繞著藍色車體。
「記得,只要他叫你,你就要說是的,先生啊!」
「是的,先生啊!」厄格烏重複了一次。
他們站在玻璃門前。厄格烏努力克制自己不去伸手去摸水泥牆,但他好想知道摸起來跟母親小屋因為鋪泥時留下隱約手印的泥牆有什麼不同。有那麼一個短短的片刻,他希望自己回到那裡,就在他母親的小屋裡,頭頂上是光線微弱但陰涼的茅草屋頂;又或是身處在他姑姑的小屋裡,那是村裡唯一有波浪鐵皮屋頂的小屋。
他的姑姑輕敲玻璃。厄格烏可以看見門後的白布簾。有人說話,用的是英文,「嗯?進來吧。」
他們脫下拖鞋後走進去。厄格烏從沒見過如此寬敞的室內空間。儘管屋內有看起來幾乎圍成一整圈的棕色沙發、沙發間的幾張邊桌、塞滿書的書櫃,以及放著插有紅白塑膠花花瓶的中央桌子,這個空間也不顯得擁擠。主人坐在一張扶手椅上,身上穿著一件無袖汗衫和短褲。他沒有坐直的身體斜靠著,整張臉埋在書裡,就彷彿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剛剛有叫人進來。
「午安,先生啊!這就是那個孩子,」厄格烏的姑姑說。
主人抬眼望向他們。他的膚色很深,像老舊的樹皮,覆蓋在他胸口和腿上的毛髮是一種更為深邃且豐美的黑色。他拿下眼鏡。「那個孩子?」
「那個男僕,先生啊。」
「喔,對,你已經把男僕帶來了。I kpotago ya。」主人的伊博語在厄格烏聽來就像羽毛般輕盈。那是沾染上英文滑溜發音色彩的伊博語,也是常說英文的人說的伊博語。
「他會努力工作,」他的姑姑說。「他是個非常好的孩子。告訴他該做什麼就行。謝謝你,先生啊!」
主人咕噥著回應了,他望著厄格烏及他姑姑的表情有點分心,就彷彿他們的出現讓他想不起某件要緊事。厄格烏的姑姑拍拍他的肩膀,低聲表示他要把工作做好,然後轉向門口。在她離開後,主人重新戴上眼鏡,望向那本書,他放鬆的身體變得更斜了,雙腿也往前伸長,就連在翻頁時,緊盯書本的他也維持著同樣姿勢。
厄格烏站在門邊,他等著。陽光從窗戶流瀉進來,時不時會有輕柔的微風掀起門簾或窗簾。室內除了主人翻頁的紙張摩擦聲外一片安靜。厄格烏就這樣站了一陣子,然後開始慢慢朝書架靠近,就彷彿想要躲進去,接著,又過了一陣子後,他已經坐到地板上,把他那只用酒椰葉纖維做的袋子抱在膝頭之間。他抬頭望向天花板,多刺眼的白啊。他閉上雙眼,試圖用完全不同的家具重新想像這個寬敞的空間,但沒辦法。他打開雙眼,再次遭到全新的讚嘆情緒淹沒,然後為了確保這一切都是真的,他四下張望,同時想著自己之後有機會坐在這些沙發上、需要擦亮這些滑溜的地板,還要清洗那些薄紗似的簾子。
「Kedu afa gi?你叫什麼名字?」主人開口問,他嚇了一跳。
厄格烏站起身。
「你叫什麼名字?」主人坐直身體又問了一次。他的身體充滿那張扶手椅,濃密的頭髮聳立在頭頂,他的手臂滿是肌肉,肩膀寬闊;厄格烏本來想像他是個更老的男人,是個病弱的男人,而現在他突然害怕自己或許無法取悅這個看起來很有能耐的年輕男子,他看起來什麼都不需要。
「厄格烏,先生啊。」
「厄格烏。你是從奧布帕來的?」
「從奧皮來的,先生啊。」
「你的年紀有可能是十二歲到三十歲之間。」主人瞇起眼。「大概十三?」他用英文說「十三」。
「是的,先生啊。」
主人繼續回頭讀書。厄格烏就站在那裡。主人翻了幾頁後又抬頭看他。「Ngwa,去廚房,那邊的冰箱裡應該有你能吃的東西。」
「是的,先生啊。」
厄格烏小心翼翼走進廚房,每一步都踏得很慢。他一看到那個幾乎跟他一樣高的白色東西就知道是冰箱。他的姑姑跟他說過。根據她的描述,冰箱就是個冰冰的穀倉,作用是不讓食物腐壞。他打開冰箱,因為撲面而來的冰涼空氣倒抽了一口氣。橘子、麵包、啤酒、非酒精飲料,許多袋裝和罐裝的食品排列在不同層架上,最高那層上還有一隻閃閃發亮的烤雞,那是只缺了一條腿的完整烤雞。厄格烏伸出手碰了碰那隻雞。冰箱對他的耳朵吐出沉重氣息。他再次碰了那隻雞,舔了一下手指,然後把另一隻雞腿扯下來,一直吃到手上只剩被他吸乾淨的一片片碎骨。接著他撕下一塊麵包,如果有親戚來家裡拜訪並帶這樣一塊麵包當禮物,他一定會非常興奮地跟其他手足分享。他吃得很快,就怕主人進來看見後會改變心意不讓他吃。而當主人進來時,他已經吃完那些食物,站在水槽旁,嘗試回想姑姑曾跟他說過要如何打開這東西,才能讓水像泉水一樣噴出來。主人已經穿上印花襯衣和長褲。他那些從皮拖鞋冒出的腳趾看起來很女性化,說不定是因為實在太乾淨了,而這種腳趾應該屬於一雙總是穿著包鞋的腳。
「怎麼了?」主人問。
「先生啊?」厄格烏用手指向水槽。
主人走過來轉開金屬水龍頭。「你該在屋內到處走走,然後把袋子放進走廊旁的第一個房間。我要去散步,讓腦子清醒一下,i nugo?」
「是的,先生啊。」厄格烏看著他從後門離開。他不高,走路的姿態俐落、活力充沛,模樣看起來就像埃斯古。埃斯古是在厄格烏村子裡蟬聯摔角第一名紀錄的男人。
厄格烏關上水龍頭,然後打開,又關上。他就這樣開了又關、開了又關,最後終於因為神奇的流動水及躺在肚子裡的芳香雞肉及麵包笑了出來。他走過客廳進入走廊。那裡有許多書堆放在三間臥房的書架上及桌上,廁所裡的洗手台和櫥櫃上也有,書房內的書更是從地板堆到天花板,至於儲藏室內,在一個個板條箱裝的可樂和紙箱裝的「首相牌」啤酒旁也堆著許多舊期刊。有些書被打開後內頁朝下放著,就彷彿主人還沒讀完卻又匆忙決定改讀別本書。厄格烏嘗試唸出書的標題,可是大部分都太長、太難了。《非參數化方法》、《一份非洲調查》、《存在鎖鏈》,還有《諾曼第人對英格蘭的衝擊》。他走過每一個房間時都踮著腳,因為覺得自己的腳很髒,而在他這麼做的同時,他逐漸下定決心要取悅主人,為的是能待在這個有肉以及涼爽地板的屋子內。他仔細看過廁所,用手撫摸過黑色的塑膠坐墊,然後聽見主人說話的聲音。
第一部 六○年代初期
一
主人的腦子有點不正常。他有太多年的時間在海外讀書、常在辦公室裡喃喃自語、不見得每次都回應別人的招呼,毛髮也太過旺盛。厄格烏的姑姑在他們一起走上小徑時低聲這麼說。「但他是個好人,」她補充。「只要好好工作,你就能吃得很好,甚至能每天吃肉。」她停下腳步吐口水,那抹唾液伴隨著一陣咂嘴聲飛離她口中,落到草地上。
厄格烏不相信有誰可以每天吃肉,就連他即將一起住的這位主人也不可能,不過他沒反駁姑姑的說法,因為他已滿懷期待地說不出話,腦中也忙著想像自己離開那座村莊後的全新人生。此刻的他...
作者序
譯者序 阿迪契的書寫開端:《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葉佳怡
二○一五年,出生奈及利亞的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被美國《時代雜誌》(Time)評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
此時的她已出版了備受歡迎的長篇小說《紫色木槿花》(Purple Hibiscus,二○○三)、長篇小說《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二○○六)、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二○○九),以及長篇小說《美國佬》(Americanah)(二○一三)。除此之外,她於二○○九年的首場TED演說〈故事單一化的危險〉(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也在美國造成轟動,其中陳述了白人將非洲世界刻板化的問題;二○一二年為TED進行的〈人人都該成為女性主義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演說同樣獲得廣大回響,相關內容在二○一四年以同名隨筆集出版。奈及利亞與英國共同製作的《半輪黃日》翻拍電影也在二○一三年上映。至於她拿的文學獎項更是多到難以在此列舉。
不過在二○一五年之後,除了一些單篇發表文章、兩部隨筆集,以及一本童書之外,阿迪契的創作似乎進入了沉潛期。她以名人之姿做了很多演講、在上BBC受訪時被迫與川普支持者辯論、為奈及利亞的LGBTQ群體發聲,但也因為支持J.K.羅琳的發言捲入恐跨爭議。她曾提到,「我不認為所有作家都必須是政治角色,可是作為一位書寫背景設定在非洲的寫實小說家,幾乎是自動就有了一種政治角色。」直到最近,我們才終於得知她的新小說《夢想清單》(Dream Count,暫譯)計畫在二○二五年出版,根據書介,那是四個奈及利亞女人在疫情期間經歷的跌宕人生。
於是從此刻回望二十多年前,阿迪契的出道小說《紫色木槿花》可說記錄了她作為作家最純真的起點。
阿迪契於一九七七年出生在奈及利亞的埃努古,兒童時期就在此地名為恩蘇卡的大學城長大,她的爸爸是數學教授,媽媽是行政人員,而她高中畢業後也同樣在奈及利亞大學讀醫學。可是為了追尋作家夢,她終究放棄醫學,在十九歲時去了美國修讀傳播與政治學。在康乃狄克州讀書的她在鄉愁催化下寫出《紫色木槿花》。她在多年後表示,因為太想家了,事後回想,那是一部「將家鄉浪漫化的小說。」「但現在的我已經完全不是當時寫小說的那個人了。」
於是讀者在閱讀《紫色木槿花》時,勢必會發現其中的許多細節都反映了阿迪契的成長背景。這部小說紀錄了十五歲女主角凱姆比利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折事件,其中融合了天主教與傳統伊博文化的衝突、家庭及社會中的性別暴力問題,以及奈及利亞這個國家在建國後遭遇的後殖民處境。雖然這些都是非常犀利的主題,但在此同時,阿迪契採取的切入角度並不尖銳。因為女主角凱姆比利在一個天主教家庭長大,這種殖民造就的處境讓她跟美國讀者一樣對伊博文化感受到一種迷人的陌生感,因此即便許多出版社聲稱「大家不會對奈及利亞的故事有興趣」,《紫色木槿花》仍獲得很好的評論及銷售成績。
若真要說這部小說中最「激進」的部分,應該是阿迪契始終堅持在小說中使用她的母語之一:伊博語。本來她的編輯認為這不是個好策略,覺得伊博語會讓讀者分心,但阿迪契反駁表示,「如果索爾.貝婁可以因為角色設定在小說中使用大量法語,沒道理我不能用伊博語。」而且唯有這樣做,才能傳遞「我的故事的情感真實性(emotional integrity of my story)」。若是從評論者的角度看,由於奈及利亞曾被英國殖民,這種書寫也反映出作者受到後殖民文化的影響,於是在阿迪契的小說中,我們總能讀到標準英文、奈及利亞英文、混雜著當地語言的破碎英文(pidgin)、伊博語,以及為了小說書寫不得不翻譯成英文給讀者看的伊博語。
為了忠實呈現阿迪契的態度,我在翻譯時也留下了伊博語原文。原文故事中的伊博語有些有再用英文重複一次,有些沒有。雖然為了給讀者多一些輔助,我替所有伊博語做了中文註釋,不過原文小說中的伊博語都沒有另外解釋,而根據阿迪契的說法,「讀者似乎也沒遇到什麼問題嘛。」這就是阿迪契在進行批判時的一貫風格:務實、溫和、堅定,並帶有一絲幽默感。
*
若說《紫色木槿花》是以一個青少女的成長蛻變為主軸,並將各種奈及利亞的現實議題穿插其中,因此可說是以小歷史為前景,大歷史為背景,《半輪黃日》可說完全相反。與其說《半輪黃日》的主角是人,倒不如說是奈及利亞在一九六七─一九七○年間發生的「比亞法拉戰爭」。事實上,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許多奈及利亞人,可能都是因為這部小說才真正知道、或開始談論這場戰爭。
這是一場發生在奈及利亞內部的種族及信仰之戰,以穆斯林豪薩人為主的群體跟以天主教伊博人為主的群體之間長久以來的矛盾一次爆發出來,而阿迪契父母及祖父母所在的東部地區在當時成立了「比亞法拉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的國旗中央圖案就是正在升起的「半輪黃日」。阿迪契的兩位祖父都在這場戰爭中死於難民營,因此即便她在戰爭結束的七年後才出生,卻始終在戰爭的陰影下成長。她從父親口中聽到了許多戰爭的故事,因此以父親的故事為核心,加上閱讀所有可找到的戰爭資料,最終寫出了《半輪黃日》。
這是一個龐大的寫作計畫,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更為多樣。之前《紫色木槿花》的主角是十五歲的奈及利亞女孩,其他大部分重要角色也是奈及利亞人,但在《半輪黃日》中,為了呈現出殖民者或所謂西方白人世界可能將非洲故事單一化的視角,阿迪契將其中一個主角設定為英國白人男子,導致她遇到很大的寫作困難,「我一開始把他寫得很像亨利.詹姆斯筆下的角色,講話很浮誇」,可是後來她轉念一想,理查是一個試圖追尋某種夢想的人,而她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於是轉換心態後,這個角色也不再是她的阻礙。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細看阿迪契筆下的主要角色,他們幾乎都有著很強的生命驅動力。有讀者問阿迪契在《半輪黃日》中最有共鳴的角色是誰,她說雖然可能有點奇怪,但她最有共鳴的是出生奈及利亞貧窮村莊的男僕厄格烏。「我知道我跟他很不一樣,我是女性、出生中產階級,而且受過完整教育。可是厄格烏很好學、有夢想,就跟我一樣。」
因此,如果要我從阿迪契的小說中挑選出一些關鍵詞,我想第一個或許就是「夢想」,畢竟就連她二○二五年即將出版的新書都在談此一主題。《紫色木槿花》的凱姆比利夢想著擺脫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壓迫、夢想著能真正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半輪黃日》則有著夢想建立自己國家的人們、夢想靠學習脫離貧窮的人、夢想靠著美好異國文化擺脫失敗過往的人……這些夢想的核心都跟人的尊嚴有關,而這些尊嚴往往受制於各種權力結構,而且可能在不同座標下遭遇各種翻轉。
在此同時,阿迪契本身的處境也可以反映這種複雜狀況,比如她身為女性,當然有在面對男性時的劣勢,但作為知識中產階級,她又擁有物質及文化資本上的優勢,而在阿迪契之後的《美國佬》當中,她更是經歷了「我是來到美國才發現自己是黑人」。奈及利亞無法成就她的作家夢,但美國又為她的寫作設下了許多侷限。於是她的角色總在追尋什麼、在突破什麼,又或是反映出那些阻礙自己及他人追尋目標的人性限制。
此外若是要另外挑選一個關鍵詞,我想應該是「創傷」無誤。《紫色木槿花》裡的女主角面對的是父親的家暴及殖民文化壓迫,《半輪黃日》更是書寫了戰爭帶來的各種創傷。阿迪契說自己在讀跟難民營有關的資料時常感到痛苦,書寫過程中也備感壓力,彷彿是祖先希望她把這部小說寫完。而等她終於寫完後,本以為能放鬆下來,卻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憂鬱。畢竟實在有太多人在那場戰爭中死去了,而作為一種溫和的控訴,《半輪黃日》中有一本由厄格烏創作的戰爭故事,其書名也反映了這種憂鬱:世界在我們死去時保持沉默。
在《紫色木槿花》及《半輪黃日》之後,阿迪契延續這些書寫核心,寫了將美國設定為重要故事背景的《美國佬》。關於成長、追夢、後殖民處境、創傷、女性困境、身分認同的複雜性,我們一次次在她的作品裡看見不同的演繹方式。不過除此之外,阿迪契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人,還在於她深入探討「愛」的複雜性。在《紫色木槿花》中,女主角想獲得自主性,但對於總是用殘忍暴力傷害她的父親、那位勇於贊助民主運動的父親,她卻仍懷抱著複雜的孺慕之情。《半輪黃日》中的歐拉娜確實愛著歐登尼伯,凱妮內也確實愛著理查,但她們選擇愛人的方式,也各自反映出她們想要追求的自由或務實價值觀,而這些對價值觀的追求跟奈及利亞的歷史交纏,在故事中呈現出相當立體的層次。當然,在《美國佬》中,來自奈及利亞的女主角又愛上了美國男孩,其中又牽扯到新的向度,但同樣的核心卻早在《紫色木槿花》及《半輪黃日》就已打好地基。
因此,《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是認識阿迪契的原點,閱讀這兩本書,我們可以看見阿迪契從二十多年前如何一路走來,她首先把奈及利亞帶到美國及世界讀者面前、把比亞法拉戰爭帶到讀者面前,然後再從奈及利亞作為起點,展開她對於一個人如何在美國以及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探索。由於她畫出了各種複雜的座標,因此除了提供具有普遍性的人性情感,同時也在邀請讀者思考:我的位置在哪裡?我的文化跟其他文化之間的關係?我的語言如何能表達我的「情感完整性」?我對他人付出的「愛」如何能讓我照見自己、理解自己的尊嚴所在?
譯者序 阿迪契的書寫開端:《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葉佳怡
二○一五年,出生奈及利亞的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被美國《時代雜誌》(Time)評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
此時的她已出版了備受歡迎的長篇小說《紫色木槿花》(Purple Hibiscus,二○○三)、長篇小說《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二○○六)、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二○○九),以及長篇小說《美國佬》(Americanah)(二○一三)。除此之外,她於二○○九年的首場TED演說〈故事單一化的危險〉(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
目錄
譯者序 阿迪契的書寫開端:《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葉佳怡
推薦序 一場內戰的創傷裂痕,用世代生命去撫平與和解/陳之華
第一部 六○年代初期
第二部 六○年代晚期
第三部 六○年代初期
第四部 六○年代晚期
後記
譯者序 阿迪契的書寫開端:《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葉佳怡
推薦序 一場內戰的創傷裂痕,用世代生命去撫平與和解/陳之華
第一部 六○年代初期
第二部 六○年代晚期
第三部 六○年代初期
第四部 六○年代晚期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