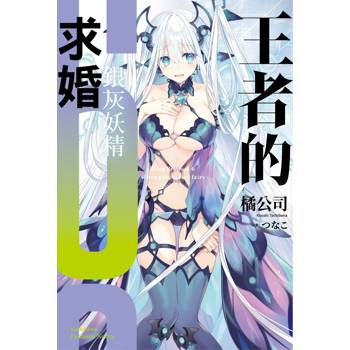我在孤獨的生活中寫下下面這些文字。在麻塞諸塞州的康科特城,瓦爾登湖的堤岸上,在森林中我親手蓋的木屋裏,在與任何鄰居距離一英里遠的地方,我在靠著雙手勞動,養活著自己。我在那裏生活了兩年零兩個月。現在,我已經回到城裏,重新開始了城市中的生活。
要不是有人到處打聽我的生活情況,我本不願將個人的情況公諸於眾,像是嘩眾取寵,是非常荒唐的。有人說我的生活方式怪異,但我認為他們是錯誤的,相反,我覺得非常自然,並且合情合理;有人問我吃什麼、是否感到寂寞和害怕等等問題。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湖畔沉思:瓦爾登湖畔散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1 |
歐美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英美文學 |
$ 252 |
世界古典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湖畔沉思:瓦爾登湖畔散記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
美國作家、詩人、哲學家、廢奴主義者、超驗主義者,也曾任職土地勘測員。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散文集《湖濱散記》(又譯為《瓦爾登湖》)和《論公民的不服從》。《湖濱散記》記載了他在瓦爾登湖的隱逸生活,而《論公民的不服從》則討論面對政府和強權的不義,為公民主動拒絕遵守若干法律提出辯護。
梭羅的全部書本、散文、日記和詩集合起來有二十冊,其中他闡述了研究環境史和生態學的發現和方法,對自然書寫的影響甚遠,也奠定了現代環境保護主義。他的文體風格結合了對大自然的關懷、個人體驗、象徵手法和歷史傳說,善感敏銳,且富饒詩意。他非常關注在險惡環境底下如何生存,同時他也提倡停止浪費、破除迷思,這樣才能體會生命的本質。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
美國作家、詩人、哲學家、廢奴主義者、超驗主義者,也曾任職土地勘測員。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散文集《湖濱散記》(又譯為《瓦爾登湖》)和《論公民的不服從》。《湖濱散記》記載了他在瓦爾登湖的隱逸生活,而《論公民的不服從》則討論面對政府和強權的不義,為公民主動拒絕遵守若干法律提出辯護。
梭羅的全部書本、散文、日記和詩集合起來有二十冊,其中他闡述了研究環境史和生態學的發現和方法,對自然書寫的影響甚遠,也奠定了現代環境保護主義。他的文體風格結合了對大自然的關懷、個人體驗、象徵手法和歷史傳說,善感敏銳,且富饒詩意。他非常關注在險惡環境底下如何生存,同時他也提倡停止浪費、破除迷思,這樣才能體會生命的本質。
序
前言
我在孤獨的生活中寫下下面這些文字。在麻塞諸塞州的康科特城,瓦爾登湖的堤岸上,在森林中我親手蓋的木屋裏,在與任何鄰居距離一英里遠的地方,我在靠著雙手勞動,養活著自己。我在那裏生活了兩年零兩個月。現在,我已經回到城裏,重新開始了城市中的生活。
要不是有人到處打聽我的生活情況,我本不願將個人的情況公諸於眾,像是嘩眾取寵,是非常荒唐的。有人說我的生活方式怪異,但我認為他們是錯誤的,相反,我覺得非常自然,並且合情合理;有人問我吃什麼、是否感到寂寞和害怕等等問題。還有一些人很好奇,想知道我捐給慈善機構的那些東西是怎樣來的,還有一些家庭負擔沉重的人,想知道我收養了幾個貧困的孩子,所以本書在回答這一類問題的時候,請一般讀者原諒我對這些特殊問題的一一答覆。
很多書避免用第一人稱的語氣進行寫作,而本書則多採用這種方式表達,「我」這一辭彙出現的頻率比較高,實際上,無論什麼書都是以第一人稱的口氣來表達的,這一點都經常不被我們注意。假如我對別人瞭解得像瞭解自己那樣,也就不會反復地說自己的事了。無奈自己閱歷有限,就只能談談自身的情況,但我希望每個作家都不局限於只寫道聽塗説的東西,他應當準確而誠懇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像寄給遠方親人的家信那樣進行創作。在我看來,假如一個人生活得很誠懇,他一定是生活在別處的。以下這些文字或許適合清貧的學生閱讀。至於其他讀者,他們自會有所取捨。因為誰也不會削足適履,委曲求全,只有穿合乎自己尺寸的鞋,才會感到適得其所。
我將說到的事物,不一定局限於只與中國人和桑威奇島人有關,而與你們息息相連,這些文字的讀者,在新英格蘭生活的人們,特別是在此世生活的本地土著,關於你們及其所處的環境。你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度過了怎樣的生活啊;你們是否真的有必要使自己的生活變得如此糟糕呢?這種生活能否改善呢?在康科特的時候我曾去過許多地方;無論在店鋪、公房裏,還是在田野上,我到處看到這裏的人們像是在贖罪那樣,幹著種種令人震驚的苦活。我曾經聽說過婆羅門教的教徒,坐在火堆中間,眼睛直盯著太陽,或把身體倒掛在烈火之上;或偏著頭看著天空,「直到他們無法恢復原狀,脖子歪曲了,除了液體,別的食物根本無法流入胃中」,或用一條鐵鏈,把自己終生鎖在一棵樹下;或像毛毛蟲那樣,用他們的身體去丈量帝國的廣袤土地;或單腿獨立地站在柱子頂上——而就是這種有意識的贖罪苦行,也沒有我所看見的景象那麼令人難以置信,令人膽戰心驚。赫拉克勒斯的十二苦役與我的鄰居幹的活一比較,就實在算不了什麼,因為他只有十二個,做完就完了,可是我從沒有見到過我的鄰居殺死或捕獲過任何怪獸,也沒有看到過他們完成了沒完沒了的苦役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依俄拉斯這樣的赫拉克勒斯的忠實奴僕,用一塊火紅的烙鐵,去烙那九頭怪獸。它被割去一個頭,就會長出兩個頭來。
我看見年輕人,我的市民同胞,不幸的是,他們一生下來就繼承了土地、房屋、糧倉、牛羊和農具;得到它們容易,而把它拋棄可就難了。他們不如生在空曠的原野上,喝狼奶長大,這樣他們也許能夠看到自己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賣命地幹活。誰使他們變成了土地的奴隸?為何有人能夠擁有六十英畝土地,而更多人卻註定只能下地幹活呢?為何他們剛出世,就得自掘墳墓?他們不能不過人的生活,不能不推動這一切,一個勁兒地幹活,盡力使生活過得好一點。我曾遇見過多少可憐、永生的靈魂啊,幾乎被壓死在生命的負擔下面,他們無法呼吸,他們在生命線上掙扎,推動他們前面的一個長七十五英尺、寬四十英尺的大穀倉,一個從未打掃過的奧吉亞斯的牛圈,還要推動上百英畝土地,鋤地、拔草,他們還要放牧和護林!而另一些沒有繼承產業的人,雖然沒有這種代代相傳的、無謂的磨難,卻也得為他們幾英尺的軀體而委屈地生活,拼命地幹活。人是在一個很大的錯誤之下勞動著。人健美的身體,大多很快地被犁頭耕了過去,變成泥土中的肥料。就像一本古書中說的那樣,人被一種無可明狀的被稱為「必然」的命運所支配,他們積累起來的財富,腐蝕於飛蛾和鏽黴,招來了盜賊。這是一個愚蠢的生命,活著的時候或許不明白,到臨終的時候,人們最終會明白這一點。據說,杜卡利安和比爾把石頭往背後扔,就創造了人類。有詩歌為證: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歷盡千難萬阻,而明瞭來自何處,人類由此變得堅強)。
羅利後來曾寫了兩句響亮的詩:「從現在開始,人的內心變得堅硬,任由勞怨,證明我們本身就是岩石。」
盲目地遵從本身就錯誤的神示,把石頭從頭頂向後扔,也不管它落在什麼地方。
大部分人,即使是在這個比較自由的國度裏的人們,也因為愚昧無知,因為莫須有的焦慮、永遠幹不完的粗活,而永遠無法去採集生命的美好果實。過度勞累使他們的手指變得粗笨和顫抖,無法採集。確實,操勞者操勞了一天又一天,永遠沒有時間停下來,以使自己真正休閒;無法保持人與人之間最純潔的交往;而他的勞動果實,在市場上卻總是掉價。他沒時間來做別的,除了做一架機器。他怎麼知道自己是無知的呢——他恰恰是靠這種無知活下來的——他不也經常傷筋費神嗎?在評論他們之前,我們先要解決他的溫飽問題,並用我們神奇的藥劑使他恢復健康。我們生命中最可貴的品質,就像果子上的細粉一樣,需要小心呵護,才能保全。而人與人之間卻很少能如此溫柔地相處。
我們都知道,有的讀者是貧窮的,覺得生活艱辛,有時甚至可以說連喘口氣都困難。我知道這本書的讀者中,有人無法為吃了的飯和穿破了的衣服付出錢來,好不容易忙裏偷閒,從雇主那裏偷來點時間,才能讀這幾頁文字。許多人過的是何等卑微、奔波輾轉的生活啊,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的眼睛已經被我的閱歷磨得鋒利無比了;你們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欲做成一筆生意以償清債務,你們陷在一個非常古老的泥沼不能自拔,aes alienum——他人的銅幣中,有些錢幣不是用銅鑄成的嗎?就在他人的銅幣中,你們出生,死亡,被埋葬;你們承諾明天償清債務,明天後還有另一個明天,直到死在了今天,債務還是沒有償完;你們乞求開恩和憐憫,請求照顧,使盡了法子總算沒有被送進大牢;你們編造謊言,拍馬溜鬚,縮進一個安分守己的硬殼裏,或者自我吹噓,作出一副清高和大度的樣子,才獲得了你們的鄰人的信任,允許你們為他們做鞋製帽、縫衣修車,或者讓你們替他們買吃的;你們在一隻破箱籠裏,或者在灰泥後面的一隻襪子裏,塞進了一把錢幣,或者塞在銀行的磚屋裏,那裏是要安全一些;無論塞在何處,塞多少,也不管數目是多是少,為了怕生病而拼命賺錢,卻反而被賺錢累得病倒在床上。
我有時感到很奇怪,我們為什麼這樣輕率,我甚至認為,我們是在過著臭名昭著的、從國外「舶來」的奴役制度下的生活。有那麼多殘暴而熟練的奴隸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隸。一個南方奴隸主的監工是狠毒的,而一個北方奴隸主的監工也許更加糟糕,但你們自己做起監工來是最壞的。說什麼——人是神聖的!看大路上的趕馬人,晝夜不分地趕向市場,在他們的內心裏,會有什麼神聖的思想呢?他們的最大任務是伺候好驢馬!與馱運的利益相比較,他們的命運算得了什麼?他們不過是在為一位繁忙的貴族趕馬,有什麼神聖可言呢?你看他們卑微地趕著,整天戰戰兢兢的,毫無神聖可言,更遑論不朽了,他們知道自己只能歸屬於奴隸或囚徒這類人。和我們的自知相比,大眾輿論這個暴戾的君主也顯得微不足道。正是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決定了這個人的命運,決定了他的歸宿。要在西印度各州談論靈魂的自我拯救,是不可能有一個威伯爾牧師來宣講的。請再想一想,大地上的女人們,編織著臨死之日梳妝用的軟墊,她們對自己的命運也非常漠視!彷彿得過且過才不會傷害永恆。
人類在平靜地過著絕望的生活。所謂按照老天的意思行事,其實就是一種徹底的絕望。從絕望的城市到絕望的村莊,你必須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來鼓勵自己。在人類的遊戲與消遣中,隱藏著一種凝固而無法知覺的絕望。遊戲與消遣中並不存在娛樂,因為娛樂是下班之後的事情。不做絕望之事,乃智慧之一種。
如果把我過去關於如何度日的打算告訴大家,或許有些熟悉我的實際情況的讀者會感到奇怪,而那些對我不熟悉的人則會感到驚訝。所以,我在這裏略述幾件小事。
無論如何,我都希望能夠立即改善我當前的狀況,並在手杖上刻下記號;過去和未來的交叉點正是現在,我就站在這個交叉點上。請原諒我說得晦澀難懂。因為我所從事的工作比大多數人在幹的活更加神秘;並非我故意保密,而是我的這種工作有這種特點。我很願意把我所知道的都說出來,而非有意讓公眾不知其所以然。
很久前我丟失了一頭獵犬、一匹栗色的馬和一隻斑鳩,到現在我還在尋找它們。我對很多過路人描述它們的情況、蹤跡以及它們會回應怎樣的叫喚。我曾遇到過少數幾個人,他們曾聽見獵犬的吠聲和馬奔跑時的蹄音,甚至還看到斑鳩隱入雲中。他們也急著想把它們找回來,彷彿是他們自己丟失的。
要看太陽初升和黎明降臨,如果可能,還要閱盡大自然本身!在多少個冬天和夏日的清晨,在鄰居們還沒有起床為他們的生計奔波之前,我已經忙碌了很久了!很多鎮子裏的人都曾看到我幹完活後歸來,包括一大早趕往波士頓的農夫,或去上山打柴的樵夫都曾經遇到過我。是的,我不可能在太陽升起時助它一臂之力,但毫無疑問,我是日出的見證者。
多少個秋天和冬天的日子,我在鎮外度過,傾聽著風吹奏的聲音,然後又把它們播撒出去!我在這裏投注了幾乎所有的資金,為這筆生意而迎著寒風,連喘氣都很困難。如果風聲中有政黨鬥爭的消息,一定會在報上刊登出來。另一些時候,我在高崗或樹梢的觀察臺上守望,向每一個新來的客人發出信號,或守候在黃昏的山頂上,等待夜的來臨,好讓我抓到一些東西。我抓到的從來就不多,這不多的卻彷彿「天糧」一般,都會在太陽下消融殆盡。
我在一家報紙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記者,報紙發行量很差,而編輯也一直認為我寫的一大堆東西是無用的。所以,作家們都有同感,忍受了巨大的困難,收穫卻微乎其微。然而在這件事上,苦難本身就是一筆不菲的報酬。
很多年來,我自認為是一個暴風雪和暴風雨的監護人,我忠職守則;我還是一個測量員,我的腳雖不測量公路,卻測量森林中路徑,並保證它們暢通。我還測量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岩石橋樑,偶爾有人在上面走過,證明了它的便利。
我也曾守護過鎮子裏的動物,它們經常跳過籬笆,為忠於職守的牧人增添不少的麻煩;我對很少有人涉足的田邊地角也很感興趣,儘管我不大知道約那斯或所羅門今天在哪塊田地中幹活;因為這已不是我分內的事了。我為紅越橘、沙地上的櫻桃樹和蕁麻、紅松、白葡萄藤和黃色的紫羅蘭花澆水,以避免它們在天氣乾燥的季節中枯萎死去。
總之,我這樣幹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絲不苟地做著這些事,直到後來越來越明白了,鎮子裏的人們是不願把我包括在公務員中的,也不願給我一點微小的薪水。我記的賬,我可以發誓是很仔細的,但確實從未被查對過,更不用說核准了,結清賬目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好在我的心思也不放在這上面。
不久前,一個印第安人到我的鄰居、一位著名的律師家裏去兜賣籃子。「買籃子嗎?」他說。律師回答:「不,我們不要。」「為什麼?」印第安人出門罵道,「你們是想把我們餓死嗎?」看到他的勤勞的白種人鄰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為律師只要把辯論的語言編織起來,就像耍魔術似的,金錢和地位都會接踵而至——這個印第安人曾自言自語:「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編製籃子;這是我能幹的。」他以為編好籃子就算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等著白種人向他購買了。但他卻不知道,他必須使人感到購買他的籃子是值得的,至少得使別人相信,購買這只籃子是值得的,要不然他就應該編製一些別的讓別人感到值得購買的東西。我也曾編製過一隻精巧的籃子,但我並沒有編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購買它。在我看來,編製籃子是我該去幹的事情,根本就不用去研究怎樣編製得使人喜歡。我倒是研究過怎樣才能避免這種買賣的勾當。人們努力追求並且認為成功的生活,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種。我們為何要誇耀一種生活而貶低另一種生活呢?
我在孤獨的生活中寫下下面這些文字。在麻塞諸塞州的康科特城,瓦爾登湖的堤岸上,在森林中我親手蓋的木屋裏,在與任何鄰居距離一英里遠的地方,我在靠著雙手勞動,養活著自己。我在那裏生活了兩年零兩個月。現在,我已經回到城裏,重新開始了城市中的生活。
要不是有人到處打聽我的生活情況,我本不願將個人的情況公諸於眾,像是嘩眾取寵,是非常荒唐的。有人說我的生活方式怪異,但我認為他們是錯誤的,相反,我覺得非常自然,並且合情合理;有人問我吃什麼、是否感到寂寞和害怕等等問題。還有一些人很好奇,想知道我捐給慈善機構的那些東西是怎樣來的,還有一些家庭負擔沉重的人,想知道我收養了幾個貧困的孩子,所以本書在回答這一類問題的時候,請一般讀者原諒我對這些特殊問題的一一答覆。
很多書避免用第一人稱的語氣進行寫作,而本書則多採用這種方式表達,「我」這一辭彙出現的頻率比較高,實際上,無論什麼書都是以第一人稱的口氣來表達的,這一點都經常不被我們注意。假如我對別人瞭解得像瞭解自己那樣,也就不會反復地說自己的事了。無奈自己閱歷有限,就只能談談自身的情況,但我希望每個作家都不局限於只寫道聽塗説的東西,他應當準確而誠懇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像寄給遠方親人的家信那樣進行創作。在我看來,假如一個人生活得很誠懇,他一定是生活在別處的。以下這些文字或許適合清貧的學生閱讀。至於其他讀者,他們自會有所取捨。因為誰也不會削足適履,委曲求全,只有穿合乎自己尺寸的鞋,才會感到適得其所。
我將說到的事物,不一定局限於只與中國人和桑威奇島人有關,而與你們息息相連,這些文字的讀者,在新英格蘭生活的人們,特別是在此世生活的本地土著,關於你們及其所處的環境。你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度過了怎樣的生活啊;你們是否真的有必要使自己的生活變得如此糟糕呢?這種生活能否改善呢?在康科特的時候我曾去過許多地方;無論在店鋪、公房裏,還是在田野上,我到處看到這裏的人們像是在贖罪那樣,幹著種種令人震驚的苦活。我曾經聽說過婆羅門教的教徒,坐在火堆中間,眼睛直盯著太陽,或把身體倒掛在烈火之上;或偏著頭看著天空,「直到他們無法恢復原狀,脖子歪曲了,除了液體,別的食物根本無法流入胃中」,或用一條鐵鏈,把自己終生鎖在一棵樹下;或像毛毛蟲那樣,用他們的身體去丈量帝國的廣袤土地;或單腿獨立地站在柱子頂上——而就是這種有意識的贖罪苦行,也沒有我所看見的景象那麼令人難以置信,令人膽戰心驚。赫拉克勒斯的十二苦役與我的鄰居幹的活一比較,就實在算不了什麼,因為他只有十二個,做完就完了,可是我從沒有見到過我的鄰居殺死或捕獲過任何怪獸,也沒有看到過他們完成了沒完沒了的苦役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依俄拉斯這樣的赫拉克勒斯的忠實奴僕,用一塊火紅的烙鐵,去烙那九頭怪獸。它被割去一個頭,就會長出兩個頭來。
我看見年輕人,我的市民同胞,不幸的是,他們一生下來就繼承了土地、房屋、糧倉、牛羊和農具;得到它們容易,而把它拋棄可就難了。他們不如生在空曠的原野上,喝狼奶長大,這樣他們也許能夠看到自己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賣命地幹活。誰使他們變成了土地的奴隸?為何有人能夠擁有六十英畝土地,而更多人卻註定只能下地幹活呢?為何他們剛出世,就得自掘墳墓?他們不能不過人的生活,不能不推動這一切,一個勁兒地幹活,盡力使生活過得好一點。我曾遇見過多少可憐、永生的靈魂啊,幾乎被壓死在生命的負擔下面,他們無法呼吸,他們在生命線上掙扎,推動他們前面的一個長七十五英尺、寬四十英尺的大穀倉,一個從未打掃過的奧吉亞斯的牛圈,還要推動上百英畝土地,鋤地、拔草,他們還要放牧和護林!而另一些沒有繼承產業的人,雖然沒有這種代代相傳的、無謂的磨難,卻也得為他們幾英尺的軀體而委屈地生活,拼命地幹活。人是在一個很大的錯誤之下勞動著。人健美的身體,大多很快地被犁頭耕了過去,變成泥土中的肥料。就像一本古書中說的那樣,人被一種無可明狀的被稱為「必然」的命運所支配,他們積累起來的財富,腐蝕於飛蛾和鏽黴,招來了盜賊。這是一個愚蠢的生命,活著的時候或許不明白,到臨終的時候,人們最終會明白這一點。據說,杜卡利安和比爾把石頭往背後扔,就創造了人類。有詩歌為證: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歷盡千難萬阻,而明瞭來自何處,人類由此變得堅強)。
羅利後來曾寫了兩句響亮的詩:「從現在開始,人的內心變得堅硬,任由勞怨,證明我們本身就是岩石。」
盲目地遵從本身就錯誤的神示,把石頭從頭頂向後扔,也不管它落在什麼地方。
大部分人,即使是在這個比較自由的國度裏的人們,也因為愚昧無知,因為莫須有的焦慮、永遠幹不完的粗活,而永遠無法去採集生命的美好果實。過度勞累使他們的手指變得粗笨和顫抖,無法採集。確實,操勞者操勞了一天又一天,永遠沒有時間停下來,以使自己真正休閒;無法保持人與人之間最純潔的交往;而他的勞動果實,在市場上卻總是掉價。他沒時間來做別的,除了做一架機器。他怎麼知道自己是無知的呢——他恰恰是靠這種無知活下來的——他不也經常傷筋費神嗎?在評論他們之前,我們先要解決他的溫飽問題,並用我們神奇的藥劑使他恢復健康。我們生命中最可貴的品質,就像果子上的細粉一樣,需要小心呵護,才能保全。而人與人之間卻很少能如此溫柔地相處。
我們都知道,有的讀者是貧窮的,覺得生活艱辛,有時甚至可以說連喘口氣都困難。我知道這本書的讀者中,有人無法為吃了的飯和穿破了的衣服付出錢來,好不容易忙裏偷閒,從雇主那裏偷來點時間,才能讀這幾頁文字。許多人過的是何等卑微、奔波輾轉的生活啊,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的眼睛已經被我的閱歷磨得鋒利無比了;你們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欲做成一筆生意以償清債務,你們陷在一個非常古老的泥沼不能自拔,aes alienum——他人的銅幣中,有些錢幣不是用銅鑄成的嗎?就在他人的銅幣中,你們出生,死亡,被埋葬;你們承諾明天償清債務,明天後還有另一個明天,直到死在了今天,債務還是沒有償完;你們乞求開恩和憐憫,請求照顧,使盡了法子總算沒有被送進大牢;你們編造謊言,拍馬溜鬚,縮進一個安分守己的硬殼裏,或者自我吹噓,作出一副清高和大度的樣子,才獲得了你們的鄰人的信任,允許你們為他們做鞋製帽、縫衣修車,或者讓你們替他們買吃的;你們在一隻破箱籠裏,或者在灰泥後面的一隻襪子裏,塞進了一把錢幣,或者塞在銀行的磚屋裏,那裏是要安全一些;無論塞在何處,塞多少,也不管數目是多是少,為了怕生病而拼命賺錢,卻反而被賺錢累得病倒在床上。
我有時感到很奇怪,我們為什麼這樣輕率,我甚至認為,我們是在過著臭名昭著的、從國外「舶來」的奴役制度下的生活。有那麼多殘暴而熟練的奴隸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隸。一個南方奴隸主的監工是狠毒的,而一個北方奴隸主的監工也許更加糟糕,但你們自己做起監工來是最壞的。說什麼——人是神聖的!看大路上的趕馬人,晝夜不分地趕向市場,在他們的內心裏,會有什麼神聖的思想呢?他們的最大任務是伺候好驢馬!與馱運的利益相比較,他們的命運算得了什麼?他們不過是在為一位繁忙的貴族趕馬,有什麼神聖可言呢?你看他們卑微地趕著,整天戰戰兢兢的,毫無神聖可言,更遑論不朽了,他們知道自己只能歸屬於奴隸或囚徒這類人。和我們的自知相比,大眾輿論這個暴戾的君主也顯得微不足道。正是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決定了這個人的命運,決定了他的歸宿。要在西印度各州談論靈魂的自我拯救,是不可能有一個威伯爾牧師來宣講的。請再想一想,大地上的女人們,編織著臨死之日梳妝用的軟墊,她們對自己的命運也非常漠視!彷彿得過且過才不會傷害永恆。
人類在平靜地過著絕望的生活。所謂按照老天的意思行事,其實就是一種徹底的絕望。從絕望的城市到絕望的村莊,你必須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來鼓勵自己。在人類的遊戲與消遣中,隱藏著一種凝固而無法知覺的絕望。遊戲與消遣中並不存在娛樂,因為娛樂是下班之後的事情。不做絕望之事,乃智慧之一種。
如果把我過去關於如何度日的打算告訴大家,或許有些熟悉我的實際情況的讀者會感到奇怪,而那些對我不熟悉的人則會感到驚訝。所以,我在這裏略述幾件小事。
無論如何,我都希望能夠立即改善我當前的狀況,並在手杖上刻下記號;過去和未來的交叉點正是現在,我就站在這個交叉點上。請原諒我說得晦澀難懂。因為我所從事的工作比大多數人在幹的活更加神秘;並非我故意保密,而是我的這種工作有這種特點。我很願意把我所知道的都說出來,而非有意讓公眾不知其所以然。
很久前我丟失了一頭獵犬、一匹栗色的馬和一隻斑鳩,到現在我還在尋找它們。我對很多過路人描述它們的情況、蹤跡以及它們會回應怎樣的叫喚。我曾遇到過少數幾個人,他們曾聽見獵犬的吠聲和馬奔跑時的蹄音,甚至還看到斑鳩隱入雲中。他們也急著想把它們找回來,彷彿是他們自己丟失的。
要看太陽初升和黎明降臨,如果可能,還要閱盡大自然本身!在多少個冬天和夏日的清晨,在鄰居們還沒有起床為他們的生計奔波之前,我已經忙碌了很久了!很多鎮子裏的人都曾看到我幹完活後歸來,包括一大早趕往波士頓的農夫,或去上山打柴的樵夫都曾經遇到過我。是的,我不可能在太陽升起時助它一臂之力,但毫無疑問,我是日出的見證者。
多少個秋天和冬天的日子,我在鎮外度過,傾聽著風吹奏的聲音,然後又把它們播撒出去!我在這裏投注了幾乎所有的資金,為這筆生意而迎著寒風,連喘氣都很困難。如果風聲中有政黨鬥爭的消息,一定會在報上刊登出來。另一些時候,我在高崗或樹梢的觀察臺上守望,向每一個新來的客人發出信號,或守候在黃昏的山頂上,等待夜的來臨,好讓我抓到一些東西。我抓到的從來就不多,這不多的卻彷彿「天糧」一般,都會在太陽下消融殆盡。
我在一家報紙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記者,報紙發行量很差,而編輯也一直認為我寫的一大堆東西是無用的。所以,作家們都有同感,忍受了巨大的困難,收穫卻微乎其微。然而在這件事上,苦難本身就是一筆不菲的報酬。
很多年來,我自認為是一個暴風雪和暴風雨的監護人,我忠職守則;我還是一個測量員,我的腳雖不測量公路,卻測量森林中路徑,並保證它們暢通。我還測量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岩石橋樑,偶爾有人在上面走過,證明了它的便利。
我也曾守護過鎮子裏的動物,它們經常跳過籬笆,為忠於職守的牧人增添不少的麻煩;我對很少有人涉足的田邊地角也很感興趣,儘管我不大知道約那斯或所羅門今天在哪塊田地中幹活;因為這已不是我分內的事了。我為紅越橘、沙地上的櫻桃樹和蕁麻、紅松、白葡萄藤和黃色的紫羅蘭花澆水,以避免它們在天氣乾燥的季節中枯萎死去。
總之,我這樣幹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絲不苟地做著這些事,直到後來越來越明白了,鎮子裏的人們是不願把我包括在公務員中的,也不願給我一點微小的薪水。我記的賬,我可以發誓是很仔細的,但確實從未被查對過,更不用說核准了,結清賬目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好在我的心思也不放在這上面。
不久前,一個印第安人到我的鄰居、一位著名的律師家裏去兜賣籃子。「買籃子嗎?」他說。律師回答:「不,我們不要。」「為什麼?」印第安人出門罵道,「你們是想把我們餓死嗎?」看到他的勤勞的白種人鄰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為律師只要把辯論的語言編織起來,就像耍魔術似的,金錢和地位都會接踵而至——這個印第安人曾自言自語:「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編製籃子;這是我能幹的。」他以為編好籃子就算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等著白種人向他購買了。但他卻不知道,他必須使人感到購買他的籃子是值得的,至少得使別人相信,購買這只籃子是值得的,要不然他就應該編製一些別的讓別人感到值得購買的東西。我也曾編製過一隻精巧的籃子,但我並沒有編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購買它。在我看來,編製籃子是我該去幹的事情,根本就不用去研究怎樣編製得使人喜歡。我倒是研究過怎樣才能避免這種買賣的勾當。人們努力追求並且認為成功的生活,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種。我們為何要誇耀一種生活而貶低另一種生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