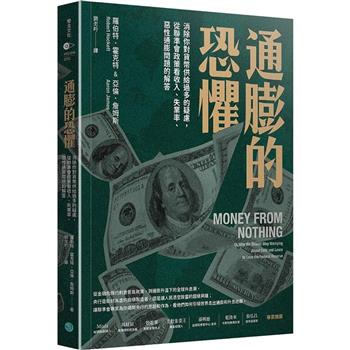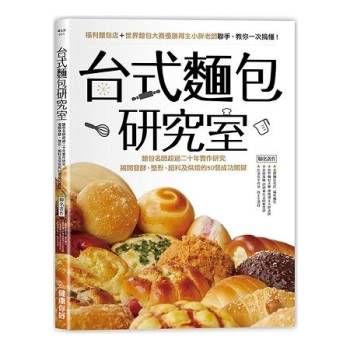1920年代,時值全球罷工潮。英國有大罷工;美國有一連串紡織、煤礦及鐵路工潮;亞洲各地亦有反資反殖的抗爭。香港,在時代洪流之中發生的三大工運──香港機器工人罷工(1920年)、香港海員罷工(1922年)和省港大罷工(1925-1926年)──也成為全球矚目的國際事件。
所謂「機器工人」就是操作機器的工人,集中在船塢、工廠中工作,因為薪資相對較高,而被稱為「工人貴族」。當時,數萬機工罷工18天,成功爭取增加工資,並開創了「上廣州」的先河,返回老家、投靠親友,堅持不回港──長期罷工,自此成為早期「港式罷工」的特色,機工罷工也成為其後海員罷工和省港大罷工的重要前傳。
本書名為《邁向現代工運第一炮──1920年機工罷工百年紀念文集》,其實內容範圍不限於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而是還原香港歷史上重大勞工事件的原貌。其中,作者觀察到,由於機器工人識字、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水準,知道自己受到剝削,受到「洋老闆」的歧視和欺凌,明白團結抵抗的重要性,故而敢於爭取自己應有的勞工和政治權利;他們對自己勞動權利和工人身分的認定,以及組織模式從傳統的「行會」轉變為「工會」的過程,是20世紀初香港工運進入現代工運模式的演進。此外,作者還生動描繪了港人在中國工人與政黨支持下開展的反殖抗英民眾運動,不僅點名了機器工會在辛亥革命和抗戰時的重要角色,也闡釋了香港工人在中國近代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本書同步收錄4篇作者恩師、已故華南地區工運史學者陳明銶教授的紀念文章,介紹其治史特色、生平傳略以及學術藏書,供研究者及後進按圖索驥、接續鑽研。
本書特色
★名為《邁向現代工運第一炮──1920年機工罷工百年紀念文集》,實際上內容範圍擴及香港歷史上幾次重大勞工事件,致力於還原事件原貌,也突顯香港工人及工運在中國近代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同步收錄已故華南地區工運史學者陳明銶教授的紀念文章,介紹其治史特色、生平傳略以及學術藏書,為後進研究者提供指引。
各界推薦
溫柏堅(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麥德正(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邁向現代工運第一炮:1920年機工罷工百年紀念文集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邁向現代工運第一炮:1920年機工罷工百年紀念文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梁寶龍
中文中學畢業,業餘香港歷史研究者,主攻工人運動史,近日亦撰寫社會保障文章。八十年代協助陳明銶教授編寫《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和《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兩書。1990年參與《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編輯工作。現定期在網上發表工運史研究文章,刊於個人博客:「香港工人的故事」、「惟工新聞」、工業傷亡權益會的Facebook等。
2017年與香港中華書局合作出版《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及編輯出版《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回顧論文集》。2018年出版《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同年協助香港職工會聯盟編譯《成功組織者的八堂課》。2020年協助編寫《走不完的工會路──新巴職工會的古往今來》。2021年,與台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政府內部的吶喊──香港公務員工運口述史》。
2019年協助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開辦陳明銶學術藏書。
現為香港個人及社區服務業工會副主席,香港社會保障學會理事等。
梁寶龍
中文中學畢業,業餘香港歷史研究者,主攻工人運動史,近日亦撰寫社會保障文章。八十年代協助陳明銶教授編寫《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和《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兩書。1990年參與《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編輯工作。現定期在網上發表工運史研究文章,刊於個人博客:「香港工人的故事」、「惟工新聞」、工業傷亡權益會的Facebook等。
2017年與香港中華書局合作出版《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及編輯出版《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回顧論文集》。2018年出版《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同年協助香港職工會聯盟編譯《成功組織者的八堂課》。2020年協助編寫《走不完的工會路──新巴職工會的古往今來》。2021年,與台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政府內部的吶喊──香港公務員工運口述史》。
2019年協助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開辦陳明銶學術藏書。
現為香港個人及社區服務業工會副主席,香港社會保障學會理事等。
目錄
推 薦 序 龍少:出身草根,心繫中華的歷史學家/溫柏堅
推 薦 序 從前,有人行路上廣州……/麥德正
前 言──機工罷工百年感言/梁寶霖
龍少爺導讀──機器工人的故事/龍少爺
【工運第一炮篇】
第一部分 社會新力量
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簡史/梁寶龍
1920年香港機工大罷工史/梁寶龍
機工元老──馬超俊/梁寶龍
辛亥革命與香港機工/梁寶龍
遠東機工工運/梁寶龍
第二部分 華機式微
華機會前理事曾常訪問/梁寶龍
【獨領風騷篇】
從工運至粵港澳城市群──陳明銶教授治史特色/區志堅
陳明銶教授傳略/林浩琛
介紹與工運史研究有關的陳明銶學術藏書/梁寶龍
機工工運有關的書籍及資料評介/梁寶霖、梁寶龍
鳴謝
推 薦 序 從前,有人行路上廣州……/麥德正
前 言──機工罷工百年感言/梁寶霖
龍少爺導讀──機器工人的故事/龍少爺
【工運第一炮篇】
第一部分 社會新力量
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簡史/梁寶龍
1920年香港機工大罷工史/梁寶龍
機工元老──馬超俊/梁寶龍
辛亥革命與香港機工/梁寶龍
遠東機工工運/梁寶龍
第二部分 華機式微
華機會前理事曾常訪問/梁寶龍
【獨領風騷篇】
從工運至粵港澳城市群──陳明銶教授治史特色/區志堅
陳明銶教授傳略/林浩琛
介紹與工運史研究有關的陳明銶學術藏書/梁寶龍
機工工運有關的書籍及資料評介/梁寶霖、梁寶龍
鳴謝
序
推薦序
龍少:出身草根,心繫中華的歷史學家
溫柏堅
國內同胞對港人一向有兩大「意見」,一是他們不愛國、對國內發展完全不感興趣,二是他們愛錢、可以為了個人利益而出賣同胞。如此偏見持續多年,直到梁寶龍先生以詳實的學術研究為港人正名,「誤解」才得以消除──這是梁寶龍先生對香港學術界的重大成就之一,作為一名心繫中華的歷史學家,他憑著滿腹經綸與一腔熱血,傳神地刻畫了香港工人為20世紀的中國工運所作出的貢獻。
梁寶龍先生,被業內尊稱為「龍少」,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既是工會運動領導者,又是史海鉤沉的不懈耕耘者。他少年時扎根工廠,後又成為了香港工會運動的先鋒;至於在歷史學的鑽研上,更是自學成才,雖未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其對史學之熱愛、文筆之流暢、運用史料之審慎,不遜色於諸多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龍少在學術界擁有著不可撼動的「江湖地位」,從周奕先生等人對他的尊崇中,便可見一斑。
筆者曾多次推薦龍少的大作,以供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博士生等群體作為嚴謹的學術參考,如《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一書。「海員大罷工」的成功,得益於孫中山領導下的廣州政府,在廣州政府的支持下,海員們逃去廣州、接受庇護,從而擺脫港英當局的壓迫。龍少以筆詮心,致力於還原香港歷史上重大勞工事件的原貌,他在書中不僅生動描繪了港人在國內工人與政黨支持下開展的反殖抗英民眾運動,也呈現了香港工人與國內革命力量同奮鬥、同建設的休戚與共──1920年機器工會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1925-1926年省港大罷工等等皆是如此,部分國內同胞對香港歷史瞭解不深,而近幾年發生的幾起社會衝突,更是令兩地關係頗為緊張。在特區民眾看似對北京缺乏信心、內地同胞對香港存有些許懷疑之際,龍少的著作,或許可以為香港和內地在精神世界重新搭建起信任的橋梁。
龍少的史學啟蒙,得益於陳明銶教授(Ming K. Chan)。1980年代,龍少結識陳教授後,便常常去香港大學旁聽陳教授的課程。一位是求知若渴的進步青年,一位是誨人不倦的史學大家,兩人結下亦師亦友的緣分,彼時的龍少雖入世未深,但陳教授慧眼識人、給予厚望,不僅幫助龍少取得出入圖書館的便利,還帶著龍少參與了《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和《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兩書的編撰工作。龍少當時負責總結記錄其他學者的學術成果,這是件苦差,但也是他與學術打交道的第一份差事,更為他日後的史學成就奠定了基礎。陳教授不僅鼓勵龍少完成了他的第一本書《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更出席了該書的新書發布會。陳教授素來是位鑽研學術的清高學者,既與龍少交情深厚,又為其史學新著做宣傳,可見龍少在陳教授心中的地位之高,亦可見龍少的學術含金量之高。筆者的師叔、陳教授的好友李培德教授,常常稱讚陳教授是一個「有分量的學者」,我想,龍少亦是如此。
陳教授桃李滿天下,但真正繼承他衣缽、專心研究華南地區工運史的,只有龍少。這位工人出身的歷史學家將其畢生精力匯於這一領域,也為之填補了諸多空白,1920年機器工會領導的罷工,打響了華南地區工運潮的第一炮,也使得當地的機器工人愈發團結,無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陳教授雖在博士論文中有所提及,但因此次勞工運動不是他的研究重點,終究未多筆墨。龍少悉此,便與兄長梁寶霖先生編寫了這本關於機器工會罷工的大作,不僅描繪了機器工會在辛亥革命和抗戰時的重要角色,也點明了香港工人在中國近代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是龍少的第三本著作,意義非凡,既呈現了香港工人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也是對陳明銶教授最好的紀念。龍少師承陳教授,他的學術生涯可以說是陳明銶教授重要的學術遺產,師恩難酬、銜草難報,龍少同陳教授生前的幾位好友一道,將其藏書從美國輾轉運至香港,在嶺南大學成立了「陳明銶教授學術藏書」,並將藏書內的資源整理編目以供學者使用。本書中,龍少對「陳明銶教授學術藏書」內的資源加以介紹,他深知恩師生平最珍視之物,也以恩師最希望的方式,令其學術大義得以延續、發揚。
龍少此作,史料詳盡、文采斐然,吾輩從中得以瞭解香港機器工人對國家、對城市的貢獻,也得以窺見龍少對史學的熱愛。這本書,值得作為國內頂尖大學的學術教材,筆者迫不及待想帶回南京大學,與學生們共進這一場學術盛宴,萬分期待。
溫柏堅
南京大學
17/11/2023
*溫柏堅任職於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中國歷史系。
推薦序
從前,有人行路上廣州……
麥德正
時興懷舊,不少香港人對於幾十年前,以至百多年前的事物都很感興趣,回顧當年衣食住行一類的歷史掌故,津津有味,可是鮮有留意工運。這也難怪,雖然香港百多年前已經有豐富的工運歷史,但香港人多數都不會留意,知道省港大罷工的大概,已屬難得。
原來,香港人開玩笑說的「戇兜兜,行路上廣州」,據說就是源起於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當時很多香港工人響應罷工號召,抗議英國政府在上海租界射殺爭取權益的工人,乾脆離開香港,返回廣州。雖然當時政府下令九廣鐵路停駛,但數以萬計罷工工人鬥志昂揚,堅決「行路上廣州」,場面壯觀,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可知當年罷工規模之浩大。原來,省港大罷工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非常重要的「前傳」,就是1920年的「機器工人罷工」。所謂「機器工人」就是操作機器的工人,集中在船塢、工廠中工作,當時近萬工人罷工18天,成功爭取增加工資。機器工人開創了「上廣州」的先河,返回自己在內地的老家,投靠親友,堅持不回港,長期罷工,成為早期「港式罷工」的特色。
機器工人罷工期間,電車工會受到鼓舞,也發動罷工,得到資方答應全部要求。香港機器工人罷工勝利後,廣東機器工人也罷工三天,得到加薪。罷工之後,香港和廣州工人紛紛成立自己的組織,提出加薪和改善待遇要求:香港有120間新成立的行業組織;1920年廣州有工會從26間增至100間,翌年再增至130間。受機器工人罷工影響,1922年海員大罷工爆發,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建築業工潮。
本書名為《邁向現代工運第一炮──1920年機工罷工百年紀念文集》,其實內容範圍不限於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而且是20世紀初的香港工人,如何認定自己的勞動權利和工人身分,組織模式從傳統的「行會」轉變為「工會」,進入了現代工運的模式,就是工人集體透過工會,向資方提出訴求,並在必要時發動罷工,逼使資方談判。當時中國外憂內患,民生艱難,政局風起雲湧,工人一方面要求合理的勞工待遇,另一方面反對國際列強壓逼,以罷工作抗爭手段,十年之間,風潮迭起,發動了機器工人罷工、省港大罷工和海員大罷工。這些罷工的規模和影響力很大,影響了香港以至中國歷史。把香港1920年代理解為工運和罷工的時代,十分貼切。
話雖如此,但這一系列罷工畢竟發生了百年,縱使當年如何波瀾壯闊,一切已事過境遷,當中涉及大量人物、團體和事件,錯綜複雜,而且與今天社會環境沒有直接關聯,一般讀者都會感到陌生,一時之間也不易消化。就算我作為工運中人,有時亦感到難以理解。
每當我墮入香港工運近代史的五里雲霧中,為了入寶山而不空手回,會採取一個「角色扮演」的方法,令自己成為「第一身」(編按:即第一人稱),去理解當時的工運,有點像玩第一身視角的電子遊戲,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進行探索。我會想像自己是一個百多年前的香港工人,「我」何以在一個大時代參加了罷工?當時社會環境如何,促使作為一芥草民的「我」參加罷工?那些歷史人物和團體有什麼作為,可以使「我」響應他們的罷工號召?先撥開年份、數據、團體和人物名稱的迷霧,由一個工人/庶民第一身的角度出發,從相關的書本和媒體中找資料和線索,去理解香港近代史,不但更容易理解,而且更有趣味。
首先,大罷工的時代背景是如何?我在本書找到了一些血淚和趣味的資料。對,因為本書的內容多元,「血淚」和「趣味」兼而有之──
當時香港人活著多艱難?艱難到賣兒賣女!有人1917年賣出第一名女兒,得到八十元,翌年賣第二名女兒只得二十元,第三年賣第三名女兒僅有兩元!生計艱難,貨幣貶值,非今日所能想像!
今天香港社會以華人為主流,少數族裔的就業待遇較差。原來19世紀時,印度人的工資比華人高,以警員工資比較,直至1915年,印度裔警員才與華裔相同,但與歐裔仍有很大差距。
以前香港是「幫會之都」,1847年,香港有華人有2.2萬餘人,而三合會分子多達1.5-2萬人,多數香港人是三合會成員。至20世紀初,加入幫會也是普遍現象,連孫中山也是幫會分子。
20世紀初,很多工人住「別墅」,不就是「時鐘酒店」嗎?原來,當年的「別墅」是出租給工人的宿舍,更通俗的稱呼是「散仔館」,是抗爭工人的聚集點。
除了對當時社會背景有一些了解,做「角色扮演」就得投入角色,投入「工人」這個身分。在此之前,還要先理解「工人」是什麼。嗯?「工人」是什麼,還需要討論嗎?正是,「工人是什麼」是一個仍在繼續討論的題目。字面上,「工人」的意思好像很容易理解,就是打工賺錢的人。但香港人總不會稱呼醫生、工程師、律師為「工人」。那麼,所謂「工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香港人對「工人」以至「勞工」的印象,往往等同於從事體力勞動的低下階層「藍領」。而被稱為「上班族」、「打工仔女」、「僱員」、「員工」、「職工」和「職員」的,印象中多數是「白領」。而無論「藍領」和「白領」,當他們要放假、遇到工傷,要離職或被解僱的時候,都必然涉及「勞工法例」,個個都是「勞工」,遇麻煩的話,就要找「勞工處」。
其實,誰是「工人」或「勞工」,並不純粹是字眼定義的問題,有些工作者,被稱為散工、經紀、營業員、判頭(編按:即承包商)、服務提供者等等……他們不被視為僱員,沒有假期,遇上工傷、被拖糧、被終止「合作關係」,都沒有任何法律保障!他們被認為是「自僱者」,但所謂「自僱」,往往都是要聽從公司指令,跟進公司的規矩,與受僱近似。
那麼,什麼是「工人/勞工」呢?這是自從工業革命至今的問題,並引伸出另一問題:工人有什麼保障?本書開篇〈龍少爺導讀──機器工人的故事〉(下稱〈導讀〉)對此作出回應,首先指出,「工人/勞工」可以是,但絕不等同於低下階層或「無產者」。很多打工仔都是業主,當他們積累了一定數量的財富和物業,再投資和出租,就是有產者,可被稱為中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而「工人/勞工」也不一定是兩手空空,沒有生產工具,很多建築工人和手工業者,都是自備工具上班。
再看百多年前「工人」團體,有部分是由「行會」發展而來。「行會」就是該行業從業員所組成的組織,成員有僱員、自僱者和小僱主。自從1910年代,因為法律規定,香港工人組織由「行會」轉變為工會。現在香港職工登記局依《職工會條例》登記的團體,包括勞資混合組織及純僱主組織,可見行會發展而來的痕跡。以今天的建築業工會為例,當中的會員多是受僱的員工,但有些時候,他們獨自向建築公司承包工程,變成自僱者,之後,他可能帶同一、兩名工人一同開工,他們的薪金來自建築公司,卻由自僱者發給他們。這位建築業從業員身分游移於受僱、自僱者和小老闆三者之間,他到底是不是「工人」呢?但無論如何,他也有資格加入工會。
到今天,什麼是「工人/勞工」這個問題似乎更不容易解答。資訊科技進步,「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興起,「平台勞工」(Platform Workers)越來越多。現時常見的食物外賣員就是近年新興「平台勞工」的典型。平台公司視「平台勞工」為自僱者,他們看似有很強的自主性,但電子平台的控制權完全在企業手上,可隨意調整外賣員的薪酬及待遇。
另一個趨勢,也是隨著資訊科技發展,及近三、四十年勞動彈性化而產生的,就是最近受到注意的「斜槓族」(Slasher)。說得好聽的,就是一人多能,盡展所長,同時有超過一個職業/工作崗位,時間彈性化,獨立自主。從另一面看,就是一人身兼幾職,殫精竭力,收入不穩,有時工時超長,有時完全無工開……
平台勞工和斜槓族往往與飯碗和權益都毫無保障的「零工」(Gig Worker)劃上等號,他們有投訴和要求,尤其是因工受傷的時候,企業、勞工處和相關政府部門指他們是自僱/服務提供者,不是「工人/勞工」,不受勞工法例保障。這是否這群辛勞的工作者的死胡同呢?〈導讀〉回顧百多年前的香港,對今天的我們有些啟發。
百多年前的「行會」很多是勞資混合體,而部分「行會」亦有為勞方發聲。本書的主角之一「華人機器總工會」(下稱「華機會」),也是「行會」之一。當時絕大部分機器工人都是受薪的勞動者,而華機會多番為受薪者說話,可算是工會。百多年前的香港勞動者已懂得為了權益,不要有僱員、自僱者和小僱主的隔膜,大家作為「工人」,有需要團結在一起。今天,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外賣員也不會在意他們被視為自僱的「平台勞工」身分,一直爭取權益,不時發動罷工,社會大眾都認同他們是在爭取「勞工」權益。
機器工人為何要罷工呢?本書有百多年前工資水平和社會背景的資料,顯示1920年時,機器工人月薪約三十元,已算是高薪,但當時物價騰貴,根本入不敷支,難以維持家庭生計。我們很容易有一個印象,認為貧窮的基層工人才會罷工。〈導讀〉打破這個誤解,指出機器工人是高薪者,卻一早建立了自己的行業組織,甚至早於清末已經投入政治運動,參加辛亥革命,並不是「愈窮愈革命」。機器工人懂文字,知道自己受到剝削,受到「洋老闆」的歧視和欺凌,明白團結抵抗的重要性,敢於爭取自己應有的勞工和政治權利,從清末至抗戰。可見,知識水平直接影響工人的意識,從機器工人的罷工宣言可略知一二:「……是次求增,又施故智,一元五角,聊算加工,恃此刻苛,誰人不憤。躋吾儕於黑奴之列,視我輩若亡國之民,般般輕視,種種每辱,若不發奮,豈得為人,倘系唔嬲,是真凉(涼)血。凡我同業,應當振臂之一呼,若不人格爭存,則不宜生於人類矣……」1920年代,時值全球罷工潮,英國有大罷工,美國也有一連串紡織、煤礦及鐵路工潮,亞洲各地也有反資反殖的抗爭。香港機器工人也在時代洪流之中,當年大罷工成為全球矚目的國際事件。
百多年前的香港工人知道勞工權益和政治息息相關,所以香港工運一直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意識強烈的香港工人參加清末革命,與孫中山聯繫。到民國初期,把持廣州的,無論是孫中山或敵對的陳炯明都支持工運,罷工工人「行路上廣州」獲得廣州政府支持。
為了政治信念,不同派系的工運勢力一直激烈爭鬥,影響著香港和內地的歷史。以華機會來說,它領導全港機器工人罷工獲勝,但1922年海員大罷工時,華機會卻號召各工會調停罷工,遭海員工會強烈譴責,指華機會是港英的御用工會,為資本家和港英服務。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華機會再次沒有號召罷工,但其屬下工人自發加入罷工行列。後來廣州發生英、法人開槍射殺華人的沙基血案,令更多機器工人參加罷工。有華機會會員對其工會澈底失望,在廣州成立「香港機工聯合會」,1926年,香港機器工人在廣州召開代表大會,另起爐灶,籌組「香港金屬業總工會」,打算取代華機會。華機會領導了1920大罷工,成就輝煌,後來卻有工人離棄,甚至要另建新工會取而代之,我們當如何評價華機會?當時香港工人有的支持中共,有的支持國民黨,形成兩股主要的工運勢力,影響著工會的態度,讀者們可從中思考。
抗戰時期,香港工運內部的矛盾似有緩和,工人都支持抗日,事例不勝枚舉。1936年,一批工會(包括華機會)響應內地籌款購買戰鬥機的號召,籌到兩萬四千多元,購買了一架命名為「香港僑工號」的飛機。1939年,國民政府出於戰時需要,招攬工人到重慶工作,三百多名熟練機器工人,在多個工會的協助下,徒步分批北上,闖過日軍封鎖線,到達重慶,到各兵工廠和鐵廠工作。
近代史中的香港處身火紅時代,香港工人投入工運和政治,推動了歷史。1920年代的三大工運:香港機械工人罷工(1920年)、香港海員工人罷工(1922年)和省港大罷工(1925-1926年),都是反抗剝削、反抗國際列強壓逼,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更是直接挑戰英國的政治罷工。港英政府當然不想民眾了解這一切,盡方法去冷處理,令香港人遺忘這段珍貴的歷史。本書正是針對這一點,還原香港的歷史角色和真實面貌──香港從來不只是一個經濟城市!香港工人從來不只是賺錢!
乘著懷舊潮流,希望有更多香港人細閱本書,認識香港工運對歷史的重大影響,一方面增加發思古之幽情的樂趣;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從中了解自己身為工人,和爭取勞工權利的重要性。
最後,要感謝梁寶霖、梁寶龍兩兄弟,他們在工運圈多年,做了很多研究和出版工作,整理了不少珍貴的紀錄,我一直十分欣賞。常言道:「一步一腳印。」但時日久了,特別是風雨飄零之際,腳印便容易消失。梁氏兩兄弟一直作出貢獻,發揚香港工運「行路上廣州」的精神和事蹟。有幸為本書作序,實在非常光榮!
2024年1月13日夜深
寫於「陸漢思牧師榮休分享會」之後
*麥德正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
龍少:出身草根,心繫中華的歷史學家
溫柏堅
國內同胞對港人一向有兩大「意見」,一是他們不愛國、對國內發展完全不感興趣,二是他們愛錢、可以為了個人利益而出賣同胞。如此偏見持續多年,直到梁寶龍先生以詳實的學術研究為港人正名,「誤解」才得以消除──這是梁寶龍先生對香港學術界的重大成就之一,作為一名心繫中華的歷史學家,他憑著滿腹經綸與一腔熱血,傳神地刻畫了香港工人為20世紀的中國工運所作出的貢獻。
梁寶龍先生,被業內尊稱為「龍少」,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既是工會運動領導者,又是史海鉤沉的不懈耕耘者。他少年時扎根工廠,後又成為了香港工會運動的先鋒;至於在歷史學的鑽研上,更是自學成才,雖未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其對史學之熱愛、文筆之流暢、運用史料之審慎,不遜色於諸多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龍少在學術界擁有著不可撼動的「江湖地位」,從周奕先生等人對他的尊崇中,便可見一斑。
筆者曾多次推薦龍少的大作,以供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博士生等群體作為嚴謹的學術參考,如《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一書。「海員大罷工」的成功,得益於孫中山領導下的廣州政府,在廣州政府的支持下,海員們逃去廣州、接受庇護,從而擺脫港英當局的壓迫。龍少以筆詮心,致力於還原香港歷史上重大勞工事件的原貌,他在書中不僅生動描繪了港人在國內工人與政黨支持下開展的反殖抗英民眾運動,也呈現了香港工人與國內革命力量同奮鬥、同建設的休戚與共──1920年機器工會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1925-1926年省港大罷工等等皆是如此,部分國內同胞對香港歷史瞭解不深,而近幾年發生的幾起社會衝突,更是令兩地關係頗為緊張。在特區民眾看似對北京缺乏信心、內地同胞對香港存有些許懷疑之際,龍少的著作,或許可以為香港和內地在精神世界重新搭建起信任的橋梁。
龍少的史學啟蒙,得益於陳明銶教授(Ming K. Chan)。1980年代,龍少結識陳教授後,便常常去香港大學旁聽陳教授的課程。一位是求知若渴的進步青年,一位是誨人不倦的史學大家,兩人結下亦師亦友的緣分,彼時的龍少雖入世未深,但陳教授慧眼識人、給予厚望,不僅幫助龍少取得出入圖書館的便利,還帶著龍少參與了《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和《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兩書的編撰工作。龍少當時負責總結記錄其他學者的學術成果,這是件苦差,但也是他與學術打交道的第一份差事,更為他日後的史學成就奠定了基礎。陳教授不僅鼓勵龍少完成了他的第一本書《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更出席了該書的新書發布會。陳教授素來是位鑽研學術的清高學者,既與龍少交情深厚,又為其史學新著做宣傳,可見龍少在陳教授心中的地位之高,亦可見龍少的學術含金量之高。筆者的師叔、陳教授的好友李培德教授,常常稱讚陳教授是一個「有分量的學者」,我想,龍少亦是如此。
陳教授桃李滿天下,但真正繼承他衣缽、專心研究華南地區工運史的,只有龍少。這位工人出身的歷史學家將其畢生精力匯於這一領域,也為之填補了諸多空白,1920年機器工會領導的罷工,打響了華南地區工運潮的第一炮,也使得當地的機器工人愈發團結,無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陳教授雖在博士論文中有所提及,但因此次勞工運動不是他的研究重點,終究未多筆墨。龍少悉此,便與兄長梁寶霖先生編寫了這本關於機器工會罷工的大作,不僅描繪了機器工會在辛亥革命和抗戰時的重要角色,也點明了香港工人在中國近代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是龍少的第三本著作,意義非凡,既呈現了香港工人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也是對陳明銶教授最好的紀念。龍少師承陳教授,他的學術生涯可以說是陳明銶教授重要的學術遺產,師恩難酬、銜草難報,龍少同陳教授生前的幾位好友一道,將其藏書從美國輾轉運至香港,在嶺南大學成立了「陳明銶教授學術藏書」,並將藏書內的資源整理編目以供學者使用。本書中,龍少對「陳明銶教授學術藏書」內的資源加以介紹,他深知恩師生平最珍視之物,也以恩師最希望的方式,令其學術大義得以延續、發揚。
龍少此作,史料詳盡、文采斐然,吾輩從中得以瞭解香港機器工人對國家、對城市的貢獻,也得以窺見龍少對史學的熱愛。這本書,值得作為國內頂尖大學的學術教材,筆者迫不及待想帶回南京大學,與學生們共進這一場學術盛宴,萬分期待。
溫柏堅
南京大學
17/11/2023
*溫柏堅任職於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中國歷史系。
推薦序
從前,有人行路上廣州……
麥德正
時興懷舊,不少香港人對於幾十年前,以至百多年前的事物都很感興趣,回顧當年衣食住行一類的歷史掌故,津津有味,可是鮮有留意工運。這也難怪,雖然香港百多年前已經有豐富的工運歷史,但香港人多數都不會留意,知道省港大罷工的大概,已屬難得。
原來,香港人開玩笑說的「戇兜兜,行路上廣州」,據說就是源起於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當時很多香港工人響應罷工號召,抗議英國政府在上海租界射殺爭取權益的工人,乾脆離開香港,返回廣州。雖然當時政府下令九廣鐵路停駛,但數以萬計罷工工人鬥志昂揚,堅決「行路上廣州」,場面壯觀,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可知當年罷工規模之浩大。原來,省港大罷工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非常重要的「前傳」,就是1920年的「機器工人罷工」。所謂「機器工人」就是操作機器的工人,集中在船塢、工廠中工作,當時近萬工人罷工18天,成功爭取增加工資。機器工人開創了「上廣州」的先河,返回自己在內地的老家,投靠親友,堅持不回港,長期罷工,成為早期「港式罷工」的特色。
機器工人罷工期間,電車工會受到鼓舞,也發動罷工,得到資方答應全部要求。香港機器工人罷工勝利後,廣東機器工人也罷工三天,得到加薪。罷工之後,香港和廣州工人紛紛成立自己的組織,提出加薪和改善待遇要求:香港有120間新成立的行業組織;1920年廣州有工會從26間增至100間,翌年再增至130間。受機器工人罷工影響,1922年海員大罷工爆發,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建築業工潮。
本書名為《邁向現代工運第一炮──1920年機工罷工百年紀念文集》,其實內容範圍不限於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而且是20世紀初的香港工人,如何認定自己的勞動權利和工人身分,組織模式從傳統的「行會」轉變為「工會」,進入了現代工運的模式,就是工人集體透過工會,向資方提出訴求,並在必要時發動罷工,逼使資方談判。當時中國外憂內患,民生艱難,政局風起雲湧,工人一方面要求合理的勞工待遇,另一方面反對國際列強壓逼,以罷工作抗爭手段,十年之間,風潮迭起,發動了機器工人罷工、省港大罷工和海員大罷工。這些罷工的規模和影響力很大,影響了香港以至中國歷史。把香港1920年代理解為工運和罷工的時代,十分貼切。
話雖如此,但這一系列罷工畢竟發生了百年,縱使當年如何波瀾壯闊,一切已事過境遷,當中涉及大量人物、團體和事件,錯綜複雜,而且與今天社會環境沒有直接關聯,一般讀者都會感到陌生,一時之間也不易消化。就算我作為工運中人,有時亦感到難以理解。
每當我墮入香港工運近代史的五里雲霧中,為了入寶山而不空手回,會採取一個「角色扮演」的方法,令自己成為「第一身」(編按:即第一人稱),去理解當時的工運,有點像玩第一身視角的電子遊戲,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進行探索。我會想像自己是一個百多年前的香港工人,「我」何以在一個大時代參加了罷工?當時社會環境如何,促使作為一芥草民的「我」參加罷工?那些歷史人物和團體有什麼作為,可以使「我」響應他們的罷工號召?先撥開年份、數據、團體和人物名稱的迷霧,由一個工人/庶民第一身的角度出發,從相關的書本和媒體中找資料和線索,去理解香港近代史,不但更容易理解,而且更有趣味。
首先,大罷工的時代背景是如何?我在本書找到了一些血淚和趣味的資料。對,因為本書的內容多元,「血淚」和「趣味」兼而有之──
當時香港人活著多艱難?艱難到賣兒賣女!有人1917年賣出第一名女兒,得到八十元,翌年賣第二名女兒只得二十元,第三年賣第三名女兒僅有兩元!生計艱難,貨幣貶值,非今日所能想像!
今天香港社會以華人為主流,少數族裔的就業待遇較差。原來19世紀時,印度人的工資比華人高,以警員工資比較,直至1915年,印度裔警員才與華裔相同,但與歐裔仍有很大差距。
以前香港是「幫會之都」,1847年,香港有華人有2.2萬餘人,而三合會分子多達1.5-2萬人,多數香港人是三合會成員。至20世紀初,加入幫會也是普遍現象,連孫中山也是幫會分子。
20世紀初,很多工人住「別墅」,不就是「時鐘酒店」嗎?原來,當年的「別墅」是出租給工人的宿舍,更通俗的稱呼是「散仔館」,是抗爭工人的聚集點。
除了對當時社會背景有一些了解,做「角色扮演」就得投入角色,投入「工人」這個身分。在此之前,還要先理解「工人」是什麼。嗯?「工人」是什麼,還需要討論嗎?正是,「工人是什麼」是一個仍在繼續討論的題目。字面上,「工人」的意思好像很容易理解,就是打工賺錢的人。但香港人總不會稱呼醫生、工程師、律師為「工人」。那麼,所謂「工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香港人對「工人」以至「勞工」的印象,往往等同於從事體力勞動的低下階層「藍領」。而被稱為「上班族」、「打工仔女」、「僱員」、「員工」、「職工」和「職員」的,印象中多數是「白領」。而無論「藍領」和「白領」,當他們要放假、遇到工傷,要離職或被解僱的時候,都必然涉及「勞工法例」,個個都是「勞工」,遇麻煩的話,就要找「勞工處」。
其實,誰是「工人」或「勞工」,並不純粹是字眼定義的問題,有些工作者,被稱為散工、經紀、營業員、判頭(編按:即承包商)、服務提供者等等……他們不被視為僱員,沒有假期,遇上工傷、被拖糧、被終止「合作關係」,都沒有任何法律保障!他們被認為是「自僱者」,但所謂「自僱」,往往都是要聽從公司指令,跟進公司的規矩,與受僱近似。
那麼,什麼是「工人/勞工」呢?這是自從工業革命至今的問題,並引伸出另一問題:工人有什麼保障?本書開篇〈龍少爺導讀──機器工人的故事〉(下稱〈導讀〉)對此作出回應,首先指出,「工人/勞工」可以是,但絕不等同於低下階層或「無產者」。很多打工仔都是業主,當他們積累了一定數量的財富和物業,再投資和出租,就是有產者,可被稱為中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而「工人/勞工」也不一定是兩手空空,沒有生產工具,很多建築工人和手工業者,都是自備工具上班。
再看百多年前「工人」團體,有部分是由「行會」發展而來。「行會」就是該行業從業員所組成的組織,成員有僱員、自僱者和小僱主。自從1910年代,因為法律規定,香港工人組織由「行會」轉變為工會。現在香港職工登記局依《職工會條例》登記的團體,包括勞資混合組織及純僱主組織,可見行會發展而來的痕跡。以今天的建築業工會為例,當中的會員多是受僱的員工,但有些時候,他們獨自向建築公司承包工程,變成自僱者,之後,他可能帶同一、兩名工人一同開工,他們的薪金來自建築公司,卻由自僱者發給他們。這位建築業從業員身分游移於受僱、自僱者和小老闆三者之間,他到底是不是「工人」呢?但無論如何,他也有資格加入工會。
到今天,什麼是「工人/勞工」這個問題似乎更不容易解答。資訊科技進步,「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興起,「平台勞工」(Platform Workers)越來越多。現時常見的食物外賣員就是近年新興「平台勞工」的典型。平台公司視「平台勞工」為自僱者,他們看似有很強的自主性,但電子平台的控制權完全在企業手上,可隨意調整外賣員的薪酬及待遇。
另一個趨勢,也是隨著資訊科技發展,及近三、四十年勞動彈性化而產生的,就是最近受到注意的「斜槓族」(Slasher)。說得好聽的,就是一人多能,盡展所長,同時有超過一個職業/工作崗位,時間彈性化,獨立自主。從另一面看,就是一人身兼幾職,殫精竭力,收入不穩,有時工時超長,有時完全無工開……
平台勞工和斜槓族往往與飯碗和權益都毫無保障的「零工」(Gig Worker)劃上等號,他們有投訴和要求,尤其是因工受傷的時候,企業、勞工處和相關政府部門指他們是自僱/服務提供者,不是「工人/勞工」,不受勞工法例保障。這是否這群辛勞的工作者的死胡同呢?〈導讀〉回顧百多年前的香港,對今天的我們有些啟發。
百多年前的「行會」很多是勞資混合體,而部分「行會」亦有為勞方發聲。本書的主角之一「華人機器總工會」(下稱「華機會」),也是「行會」之一。當時絕大部分機器工人都是受薪的勞動者,而華機會多番為受薪者說話,可算是工會。百多年前的香港勞動者已懂得為了權益,不要有僱員、自僱者和小僱主的隔膜,大家作為「工人」,有需要團結在一起。今天,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外賣員也不會在意他們被視為自僱的「平台勞工」身分,一直爭取權益,不時發動罷工,社會大眾都認同他們是在爭取「勞工」權益。
機器工人為何要罷工呢?本書有百多年前工資水平和社會背景的資料,顯示1920年時,機器工人月薪約三十元,已算是高薪,但當時物價騰貴,根本入不敷支,難以維持家庭生計。我們很容易有一個印象,認為貧窮的基層工人才會罷工。〈導讀〉打破這個誤解,指出機器工人是高薪者,卻一早建立了自己的行業組織,甚至早於清末已經投入政治運動,參加辛亥革命,並不是「愈窮愈革命」。機器工人懂文字,知道自己受到剝削,受到「洋老闆」的歧視和欺凌,明白團結抵抗的重要性,敢於爭取自己應有的勞工和政治權利,從清末至抗戰。可見,知識水平直接影響工人的意識,從機器工人的罷工宣言可略知一二:「……是次求增,又施故智,一元五角,聊算加工,恃此刻苛,誰人不憤。躋吾儕於黑奴之列,視我輩若亡國之民,般般輕視,種種每辱,若不發奮,豈得為人,倘系唔嬲,是真凉(涼)血。凡我同業,應當振臂之一呼,若不人格爭存,則不宜生於人類矣……」1920年代,時值全球罷工潮,英國有大罷工,美國也有一連串紡織、煤礦及鐵路工潮,亞洲各地也有反資反殖的抗爭。香港機器工人也在時代洪流之中,當年大罷工成為全球矚目的國際事件。
百多年前的香港工人知道勞工權益和政治息息相關,所以香港工運一直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意識強烈的香港工人參加清末革命,與孫中山聯繫。到民國初期,把持廣州的,無論是孫中山或敵對的陳炯明都支持工運,罷工工人「行路上廣州」獲得廣州政府支持。
為了政治信念,不同派系的工運勢力一直激烈爭鬥,影響著香港和內地的歷史。以華機會來說,它領導全港機器工人罷工獲勝,但1922年海員大罷工時,華機會卻號召各工會調停罷工,遭海員工會強烈譴責,指華機會是港英的御用工會,為資本家和港英服務。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華機會再次沒有號召罷工,但其屬下工人自發加入罷工行列。後來廣州發生英、法人開槍射殺華人的沙基血案,令更多機器工人參加罷工。有華機會會員對其工會澈底失望,在廣州成立「香港機工聯合會」,1926年,香港機器工人在廣州召開代表大會,另起爐灶,籌組「香港金屬業總工會」,打算取代華機會。華機會領導了1920大罷工,成就輝煌,後來卻有工人離棄,甚至要另建新工會取而代之,我們當如何評價華機會?當時香港工人有的支持中共,有的支持國民黨,形成兩股主要的工運勢力,影響著工會的態度,讀者們可從中思考。
抗戰時期,香港工運內部的矛盾似有緩和,工人都支持抗日,事例不勝枚舉。1936年,一批工會(包括華機會)響應內地籌款購買戰鬥機的號召,籌到兩萬四千多元,購買了一架命名為「香港僑工號」的飛機。1939年,國民政府出於戰時需要,招攬工人到重慶工作,三百多名熟練機器工人,在多個工會的協助下,徒步分批北上,闖過日軍封鎖線,到達重慶,到各兵工廠和鐵廠工作。
近代史中的香港處身火紅時代,香港工人投入工運和政治,推動了歷史。1920年代的三大工運:香港機械工人罷工(1920年)、香港海員工人罷工(1922年)和省港大罷工(1925-1926年),都是反抗剝削、反抗國際列強壓逼,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更是直接挑戰英國的政治罷工。港英政府當然不想民眾了解這一切,盡方法去冷處理,令香港人遺忘這段珍貴的歷史。本書正是針對這一點,還原香港的歷史角色和真實面貌──香港從來不只是一個經濟城市!香港工人從來不只是賺錢!
乘著懷舊潮流,希望有更多香港人細閱本書,認識香港工運對歷史的重大影響,一方面增加發思古之幽情的樂趣;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從中了解自己身為工人,和爭取勞工權利的重要性。
最後,要感謝梁寶霖、梁寶龍兩兄弟,他們在工運圈多年,做了很多研究和出版工作,整理了不少珍貴的紀錄,我一直十分欣賞。常言道:「一步一腳印。」但時日久了,特別是風雨飄零之際,腳印便容易消失。梁氏兩兄弟一直作出貢獻,發揚香港工運「行路上廣州」的精神和事蹟。有幸為本書作序,實在非常光榮!
2024年1月13日夜深
寫於「陸漢思牧師榮休分享會」之後
*麥德正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