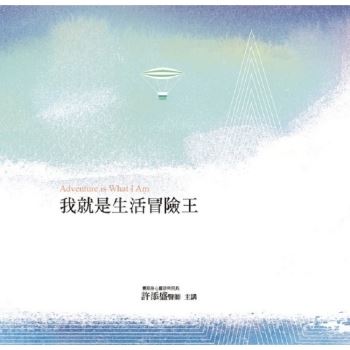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宋﹞朱熹,〈勸諭榜〉,《晦庵集》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紹熙元年(1190),朱熹(1130-1200)到任漳州知縣,隨即頒布〈州縣官牒〉,要求官員依令行事,意在整頓州縣事務,樹立規範。 其中,所發布〈勸諭榜〉,除試圖改正地方風俗,提倡人倫秩序,也推廣其教化理念。從朱熹的教化理念,可見其對士人與庶民有不同期待。如其勉勵士人「讀書窮理」、「修己治人」,但卻僅要求庶民百姓能做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即可。此與儒家傳統有關,也正是朱熹「明德新民」的教化實踐方式。此外,朱熹也非常重視地方社會的禮俗教化,曾修訂呂大鈞(1029-1080)〈呂氏鄉約〉,以〈增損呂氏鄉約〉作為地方社會的禮俗規約,以期促進社會道德與社會互助。「鄉約」可說是藉由集會的方式,對民眾進行社會教育。最早可溯自北宋呂大鈞「呂氏鄉約」。至明清時普遍盛行於鄉里間。而後世的鄉約發展,亦受其影響甚深。 木村英一指出,明代六諭即源自朱熹任地方官時所作的〈勸諭榜〉。 就字句上來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或可視為六諭較早的起源。
曉諭榜文:政令的傳布
關於「諭俗文」的研究,小林義廣〈宋代の「諭俗文」〉有較詳盡的討論,他指出早於宋代之前,唐代便有以皇帝名義發布諭俗文的實例,載錄於《大唐詔令集》中。而宋代則將此諭俗的主要職責轉移至地方官員身上。 熊慧嵐〈論宋代諭俗文─玉與守牧共天下〉則指出宋代的「諭俗」與「勸農」密不可分,地方官員常藉由勸農以諭俗。 至於地方士人所作的「曉諭榜文」,可溯自北宋陳襄(1017-1080)於皇祐年間(1049-1053)發佈的〈勸諭文〉:
「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載于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陳襄認為禮義之俗的道理在於應遵守三綱五常,濟助鄉里鄰保,不為非作歹。同時,從陳襄《州縣提綱》所作的「治縣箴言」中,表明為政應「先教化而後刑責」, 即可反映其制定勸諭文的理念。朱熹曾在〈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中為其作注,並藉其內容彰明教化,導民向善。 陳宓(?-1230)也於〈安溪縣到任諭俗文〉指出,擔心地方教化之意未明,無以導其向善之方,故採用陳襄教民之訓勸諭百姓。 由此,顯見陳襄〈勸諭文〉既是宋代曉諭榜文的開端,也是影響朱熹制定〈勸諭榜〉的關鍵。
================================
第二節 六諭宣講形式的變遷
嘉靖八年(1529),兵部侍郎王廷相(1474-1544)見民間天災旱荒嚴重,預備倉積糧不足,上奏請設義倉,認為義倉可以「寓保甲以弭盜,寓鄉約以敦俗」,又在談及義倉具鄉約教化的功效時提出:
「每月朔望日一會,在村鎮者以土地神為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神為主,至期設神位香案,社首、社正率一會之人,詣神位前上香奠酒,行再拜禮畢,社首以下各序長幼,立於神位兩旁,社副出於社末,中立,向神讀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云:『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讀畢,再讀曰:『凡我同會之人,能遵聖教者,神必降之福,有違聖教者,神必降之禍,慎哉!慎哉!』」
說明每月朔望各舉行一次鄉約會講,並由社首率約眾一同誦讀太祖高皇帝六諭。職是之故,以致於戶部題准:「每州縣村落為會,每月朔﹝望﹞日,社首社正,率一會之人,捧讀聖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則告官,輕則罰米,入義倉以備賑濟。」 因此,王廷相的上奏可說是推動六諭融入鄉約會講之關鍵。再加上嘉靖十九年(1540),監察御史舒遷強調鄉約的推行,並以「立鄉約以厚風俗」作為教化之道。 自此之後,以鄉約治民之法,便開始廣為地方官員及士大夫所推行。地方上的鄉約漸與六諭相互結合,也使得六諭宣講的方式產生轉變。
明代「中」期的六諭
自明代中期里老制度崩壞,木鐸之教不行以來,陸續出現改以鄉約作為教化風俗的方式。 此時,鄉約中寓有六諭或透過六諭勸民教化的型態、先後出現的時間紛繁並陳,情況不一。如弘治年間,文林(1445-1499)任溫州知府時,曾推行鄉約之法,並試圖以此約束族人,頒行《教民榜》、《白鹿洞規》、《古靈先生勸諭》、《溫公居家雜儀》,以行教化之事。 但具體規範中仍以「每鄉每保各置木鐸一個,令耆民照依太祖高皇帝舊制」, 可知此時同為里甲老人「持鐸循道」的宣誦型態。其後,正德、嘉靖年間,其實已有不少早期鄉約的發展,如潞州仇楫、仇森、仇樸、仇桓、仇欄兄弟所行〈雄山鄉約〉、安陽高陵呂柟(1479-1542)〈解州鄉約〉、祁門人余光行於〈河東運城鄉約〉及安邑張良知〈許昌鄉約〉等。 其中,正德六年(1511),〈仇氏家範〉中曾以舉行《藍田呂氏鄉約》和刊印《太祖高皇帝訓辭》,家給一冊,諷誦體行,作為治家之法。 但未言明如何宣講六諭,僅知已於鄉約舉行之時,發給每戶一本《太祖高皇帝訓辭》,以規範族眾。
正德十五年(1520),王守仁(1472-1529)所頒〈南贛鄉約〉,明顯具有太祖六諭的痕跡,其內文指出:
「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成,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雖未直接點出「太祖高皇帝」或「聖諭六言」之名,但仍將鄉約與六諭結合,期以發揮勸善規過的教化作用。 但其主要型態,仍是以《藍田呂氏鄉約》為本制訂而成。不過,王守仁〈南贛鄉約〉的推行,確是使其後鄉約發展越趨盛行的原因之一。 葉春及(1532-1595)曾謂:「嘉靖間,部檄天下舉行鄉約,大抵增損王文成公之教」。 明末陳龍正(?-1634)纂輯《陽明要書》時亦直言「鄉約莫詳於此」。 顯然王守仁〈南贛鄉約〉於明代鄉約發展中深具重要性。而王守仁的門生鄒守益(1491-1562)於〈敘永新鄉約〉中認為六諭有「遷善改過,潛移默化」的功效,並說道:「詢于大夫士之彥,酌俗從宜,以立鄉約。演聖諭而疏之,凡為孝順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訓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為之目十有四。市井山谷之民咸欣欣然服行之。」 說明此時已將六諭疏之為目,行於鄉約之中,並已開始對六諭進行初步的疏解。
至嘉靖四年(1525),呂柟行〈解州鄉約〉時所制定:
「諸耆老善人,每朔望或七八日到書院,可將《大誥》並律令及《藍田呂氏鄉約》、《日記故事》、近日本府發下《諭俗恒言》,摘其開心明目,關係身家風化,孝如曾參酒肉、伯俞泣杖,悌如田真荊樹,友如管鮑分金,化盜如陳寔、王烈等。類一一俗語講譬,令其歸里,轉化鄉村街坊及家人子孫。其年五六十歲以上者,令坐聽;三四十以下者,立聽。後講之日,令報化過人數及不改過之人,本職量行勸懲。若有不順梗化之人,定依《大誥》、律令,申稟上司究治。」
呂柟所作〈解州鄉約〉,已然開始實行鄉約會講,講解文本有《大誥》、《藍田呂氏鄉約》、《日記故事》、《諭俗恒言》等。其中較特別之處為述及《日記故事》中淺顯易懂之古代案例故事,意在通俗易曉,使百姓教化改過。惟仍未以六諭作為主要強調之內容。直到嘉靖三年(1524)浙江淳安知縣姚鳴鸞(1487-1529)才首度在政令中明確指出六諭,使民誦習之,並附有簡短的解釋。 而嘉靖六年(1527),安溪知縣黃懌制定讀約之法:
「聖諭及倣藍田呂氏古靈陳氏作鄉約一篇,頒示居民讀約法。首讀聖諭,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莫作非為。』次讀《藍田呂氏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次又讀《古靈陳氏教詞》,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載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終讀《本縣禁約》:『一禁火葬,二禁賭博,三禁教唆詞訟,四禁投獻田地,五禁男女混雜,六禁僧道娶妻,七禁私開爐冶,八禁盜宰耕牛,九禁偽造假銀,十禁般演雜劇,十一禁社保受狀,十二禁教讀鄉談,十三禁元宵觀燈,十四禁端午競渡,是皆責之約正,用以督勸。』 」
此時明太祖六諭已明顯見於鄉約之中,連同宋代《藍田呂氏鄉約》、《古靈陳氏教詞》及該縣禁約,一併納入讀約內容,以教化鄉里百姓。同時,從文中得知,鄉約體例大多會將規範析為條目,再分別疏解其內容。
由前述可知,嘉靖初年以前,六諭大多附載於教民榜文或地方官員的勸諭之中,仍未將六諭在鄉約中進行宣講。相較之下,《藍田呂氏鄉約》、《古靈陳氏教詞》等宋代鄉約、勸諭之文,則時常出現在明初士人文集與地方志中,顯見應已備受明代前期士人的關注。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5 |
中文書 |
$ 299 |
中國歷史 |
$ 306 |
歷史 |
$ 306 |
社會人文 |
$ 306 |
財經/企管/經濟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
明代開國之初,明太祖仿照儒家經典「木鐸教民」之制,由里老人手持木鐸,沿路宣誦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藉此勸民為善、教化百姓。嘉靖以後,因鄉約制度盛行,改為定期集會宣講六諭,是為明代地方社會施行教化的總綱,可見明代社會對於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視。
《聖訓演》成書於嘉靖十五年(1536),是六諭宣講文本的開端之作,最早收錄三原學派王恕對六諭的疏解。除六諭的詮釋外,也有婚喪禮俗的討論,並且特別重視女教的規範,以及著重在蠶桑絲織的婦功,反映陝西一帶的地域特性。
有別於明代理學家闡述儒家思想內涵的注疏內容,其編纂者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唐錡、陝西提學副使龔守愚均為地方官員。本書透過梳理《聖訓演》內容以釐清明代六諭宣講文本的演繹脈絡,同時觀察明代士人在地方上所為,或可映照出他們的治鄉理想,以及對於社會的關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林麗月專序推薦
作者簡介:
林晉葳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現為桃園市私立六和高中歷史科教師。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宋﹞朱熹,〈勸諭榜〉,《晦庵集》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紹熙元年(1190),朱熹(1130-1200)到任漳州知縣,隨即頒布〈州縣官...
「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宋﹞朱熹,〈勸諭榜〉,《晦庵集》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紹熙元年(1190),朱熹(1130-1200)到任漳州知縣,隨即頒布〈州縣官...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序】
道德教化是傳統中國治理重要的一環,宋元以後,透過朝廷和士紳的提倡,儒家思想對社會生活的規範更彰顯了政治與教化密不可分的事實。明太祖開國之初,即宣示「為治之要,教化為先」,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頒布的〈教民榜文〉中,規定每鄉每里置一木鐸,於里內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持鐸巡行本里,沿路宣誦:「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二十四字聖諭,稱為「六諭」,又稱「聖諭六言」、「聖訓六條」,自此成為明代基層教化的總綱。
嘉靖以後,宣導六諭的方式,由流動的「...
道德教化是傳統中國治理重要的一環,宋元以後,透過朝廷和士紳的提倡,儒家思想對社會生活的規範更彰顯了政治與教化密不可分的事實。明太祖開國之初,即宣示「為治之要,教化為先」,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頒布的〈教民榜文〉中,規定每鄉每里置一木鐸,於里內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持鐸巡行本里,沿路宣誦:「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二十四字聖諭,稱為「六諭」,又稱「聖諭六言」、「聖訓六條」,自此成為明代基層教化的總綱。
嘉靖以後,宣導六諭的方式,由流動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出版緣起
序/林麗月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第三節 史料運用與說明
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第二節 六諭宣講形式的變遷
第二章 聖明之治:《聖訓演》的編纂
第一節 編纂及注疏者簡介
第二節 《聖訓演》的體例與架構
第三章 聖訓明明:《聖訓演》的內容
第一節 六諭的疏解
第二節 婚喪與正俗
第三節 婦德與女教
第四章 以禮為教:《聖訓演》...
序/林麗月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第三節 史料運用與說明
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第二節 六諭宣講形式的變遷
第二章 聖明之治:《聖訓演》的編纂
第一節 編纂及注疏者簡介
第二節 《聖訓演》的體例與架構
第三章 聖訓明明:《聖訓演》的內容
第一節 六諭的疏解
第二節 婚喪與正俗
第三節 婦德與女教
第四章 以禮為教:《聖訓演》...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