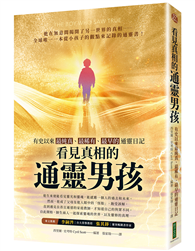青年之著陸──「陸詩叢」總序
茱萸
在此呈現的是「陸詩叢」,每輯由六冊詩集構成。第一輯的六冊詩集已於二○一九年問世,如今時隔數年,迎來了第二輯。接下來,還應該會有第三輯、第四輯、第五輯……在最初,我們規劃並期望,「陸詩叢」能夠持續不斷地將更多獨到的文本和獨特的詩人介紹給讀者,如今到來的第二輯,正是這種「規劃並期望」得以踐行的標誌,又一個新的開端。
揆諸現代漢詩的歷史,我們深知,基於「嘗試」的「開端」何其重要。而在該文體百年以來的發展進程中,「青年」始終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現代漢詩的事業亦總是與「青年」相關―無論篳路藍縷的「白話詩」草創者,還是熔鑄中西的「現代派」名家,抑或洋溢著激情的「左翼」詩人,乃至兼收並蓄的「西南聯大詩人群」,都在他們最富創造力的青年時期,開始醞釀甚至開始成就他們代表性的作品。肇始於一九七○年代末的大陸「先鋒詩」,亦發端於彼時仍是青年的「今天派」諸子對陳腐文學樣式的自覺反叛。這是文學場域仍舊富有生命力的象徵。此後的四十年間,在漢語世界,借助刊物、社團、高校、網路等媒介平臺,這個場域源源不斷地孕育出鮮活的寫作群體與個人。
作為此一脈絡的最新延展,出生於一九九○年代、成長並生活於中國大陸而又不乏遊歷世界之機遇與放眼寰宇之眼光的年青詩人們,在本世紀首個十年的後半期,開始呈現出集體湧現之勢。轉眼間已有十餘年的積澱,先後誕生了一批富有實驗精神的創作者。出現在本輯的六位「青年」,甜河、更杳、周欣祺、炎石、王徹之、曹僧,以及上一輯的秦三澍、蔌弦、蘇畫天、砂丁、李海鵬、穎川,即處於此一世代最具代表性的序列。
這些年輕的詩人,已在中國大陸、臺灣或者英倫、法國等地的知名院校完成了不同階段的學業,經歷過漫長的「學徒期」,擁有多年的「寫作史」,並已積攢了數量可觀的作品,形成了頗具辨識度的寫作風格。同時,他們亦獲得過不少權威的獎項,並在詩歌翻譯、文學批評或學術研究等相關領域開始嶄露頭角。他們是一批文學天賦與學術素養俱佳、極富潛力的青年詩人。
憑藉各自的寫作,他們已在同輩詩人中占據了較為重要的位置,經常受到大量詩人同行的認可,並擁有了一定的讀者規模―然而,由於機緣未到,在兩岸四地,他們並沒有太多使自己作品得以結集的機會。所以,本次出版的這批詩集,對作者們來說,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大家的關注和閱讀,更將是他們未來所能睹見的漫長寫作生涯中的第一個重要時刻。
這些詩,以及它們的作者,對臺灣的讀者來說,肯定還非常陌生。他們來自大陸,得以湊成第一輯的作者數量又恰好是六(陸),於是,我們乾脆將之定名為「陸詩叢」,並沿用了下來。他們平均在三十歲上下的年紀,是十足的「青年」,在大陸,則通常被冠以「九○後」的名目。但這種基於生理年齡的劃分,目前看來並沒有詩學方面明顯的特徵或脈絡,能夠使他們足以和前幾個世代的詩人構成本質的區別。因此,毋寧從詩人的「出身」及「數量」兩方面「就地取材」,以之作為本詩叢命名的便宜行事。
機緣巧合,第一輯作者的社會身分背景與寫作背景較為相似(這種情況在第二輯中已經有所改變),但並不意味著詩叢編選者的趣味將要限制於特定的群體。相反,正由於此番前因,我們遂生出持續編選此詩叢的設想,擬遵循高標準、多元化原則,廣泛地選擇不同背景與風格的作者,陸續推介中國大陸更年輕世代(繼「今天派」、「第三代」、「九十年代詩歌」、「七○後」、「八○後」等之後)的詩人及其寫作實績,以增進瞭解,同時促進兩岸的文學交流。但詩叢之名目既定,以後所增各輯,每輯僅收入六位作者、六冊詩集,以為傳統。
每輯的六冊詩集內,除詩作之外,另收錄有每位作者的詳細介紹,或更有自作序跋文字、作者訪談以及他人撰寫的針對他們作品的分析文章,出於體例考慮,此處便不再對他們進行一一的介紹和評論。我願意將本次「結集」的「集結」,視為六位中國大陸青年的詩之翅翼在初翔後的再一次著陸。
2019年3月21日初撰
2023年5月第二輯出版前夕修訂、增補
代序
語言的複瓣
帕麗夏
我與欣祺是在二○一八年十月的花蓮詩歌節上結識的,在那之後我們再也沒有機會見面。回想起來,那三天相處的畫面就如同在夜行車廂中看著窗外的風景和自己的倒影。我和她在同一個場次與讀者分享了各自鍾愛的一首詩,我念的是諾貝爾獲獎詩人蒙塔萊的〈假聲〉,那時還得借著大詩人的作品才能給自己增添一點公開發言的底氣。欣祺念的是她的網友(詩人AT)的一首小詩,她的聲音沉靜纖弱,小小地坐在椅子裡,長髮素面,目若朗星,人與詩我皆從未謀面,可我卻從她對友人作品的出聲閱讀中,感到年輕詩人之間微茫親近的聯繫。那是比大詩人遙遠的格言警語更有切身默契的輕言低語:「我知道,但很遠/我知道天空里什麼都是天空/轉過來,轉過去,翻著手腕/天空落下人體落入天空裡」,這是緩慢回放的「空中轉體」一般的詩行,語詞和語義在間隔中扭轉、折疊與往復,形成了交復的回響,甚至帶來了睡夢般的療癒效果。
我已經不記得欣祺當時分享友人的這首詩有何用意,後來讀她的詩,可以發現她的創作確實是與此相似、而又更為繁複的意念之詩,她在詩句中「空中轉體」的姿態也更為輕盈靈動。我第一次讀到時,就被深深迷住了。在欣祺的許多詩裡,總有一股正在顯靈、降落的冥冥之力,「我」被這一股不可名狀的引力握著、制轄著、守護著,「我」總在一個有些卑弱的位置裡去辨認其中的啟示,去與「它」發生問答乃至觸摸,使「它」在各種精妙的比喻和寓言式的畫面中顯形,浮現為一種關於自我和未來的「預感」:
被更輕的東西握著是什麼感覺
在夜的稠密中張開又收攏
如葉般披掛在身體的預感
一抖動就紛紛落下了
當你輕輕呼出第一口氣
那以掉落而非降臨的方式
出現在生命裡的神
已在愛中近盲
被想要守護的人守護著
是什麼感覺夢裡周身是海,跟著雲走
醒來周身是夢,跟著雲走
不是我走向你
而是島嶼她折疊翻轉
小紅帽,後視鏡里的冷風
遇見群鳥銜來
向上的恐懼和向下的善行
我們心中空洞洞的美麗
難道就是全部嗎
仍需試探,向幽暗而苦澀的核
但請讓你試探的手裡有我
假如說,思辨能力強勁的詩人常在語言中展示的是對抗性的辯證邏輯,並由此不免自限於二元化或本質化的思維模式,那麼,欣祺的寶貴之處,正在於她在詩中始終保持著意念的周轉,不被定型、不下結論、不做簡單粗暴的反抗、不借附也不想像一個強大的對象來救助自己。她的關切和注視總集中於「更輕」的生命,她的「輕逸之力」不必通過轉弱為強來形成出路,因為輕靈的意念本身就有足以承托自我的包裹性,它的周轉變形在語言之中具有更多閃閃發光的可能性。詩人固執地想繼續探入「空洞洞的美麗」中去觸碰更幽暗的內核,這裡有低微輕柔的虔誠問詢,但決非低弱的臣服。詩行一開始如同一朵凌空開放的複瓣花球一樣,張開又收攏,披掛又落下,始終保持在不安而美麗的動態之中,這樣的詩作該如何收束呢?她的均衡感和意志力總在讀者意想不到之處顯露出來,有時是乾淨有力的祈使句―「仍需試探,向幽暗而苦澀的核/但請讓你試探的手裡有我」,有時是全稱或最高級的描述和判斷―─「我獨自去集市,尋找一個底部有洞的容器/我發現全部的容器底部都有洞」(〈洞〉),「而最明亮的這世界,永遠有人慢慢下沉/比雨後的水汽更輕。」(〈降臨―─隔離日記〉),有時是決絕的否定與拒絕―「我要離開這些不徹底的事物了」(〈浮雲〉),「為我畫一個開放的三角形試試看/不要折疊或彎曲線條,不要說圓滿」(〈Geometry〉)。她的語言與她本人一樣,看似柔弱纖細,實則邏輯清晰、果決凌厲。在花蓮一別後的數年裡,我和欣祺也很少聯繫,而在我遭遇兩次比較重大的生活危機時,我總會在最危急的時候問她一句:「我能給你打個電話嗎?」我想已經覺察出她性格中的果決,在關鍵時候也想仰仗她。
我喜愛欣祺詩中對冥冥之力的召喚與低語,喜愛她在詩中美麗而殘酷的語調,彷彿生活中疼痛的迷霧―不論是內心的「稠密的夜」,還是記憶中的「密林」,要穿過它,只能以如此破碎、悲觀而篤定的方式,結果不會是「圓滿」、「徹底」的。她的痛苦與思索,看似一個個難以捕獲的懸念,事實上,是立足於每個創傷個體極為實際的精神處境,是遠比思索一個人如何變得更強大、一個人如何擺脫困境更加迫切的現實問題,她思索的是:一個已經破碎的心靈如何在一個既成的傷痛現實中繼續清醒地活著。這一直是欣祺最為關切的精神內容,這既與她自己成長過程中幾次重大的傷痛經驗相關,可能也是她從一個哲學系的學生轉為心理諮商專業的原因。
人與人之間的相識,與詩中的直覺是相似的。我對她的詩與人一見如故,當時想著若能一直和她保持聯繫就好了,於是在詩歌會後聚餐的庭院長桌邊,我一時興起,跟她說我成立了一個詩社,叫「崇光詩社」,想請她加入,讓她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社員。她很認真地想了想,沒有答應,笑說,得回去考慮一下。我們各自回酒店房間之後,仍感談興未盡,我又與她趁夜出行,坐了很久的捷運。我聽她細細密密地講起她遠在上海的家人、她身體的疼痛、她前路未卜的愛情。那一段路她是帶著很深的勞累,要到機場去接一位老友,從她對新朋舊友誠摯的情意裡,我知道她不是個自我封閉的人。她與信任的朋友共築著緊密的精神關係,並以此為基礎,總在努力地去踐行自己對於藝術和社會的理念,在行動中去兌現「美麗」和「善行」。
這一點構成了欣祺的詩歌與傳統意義上的「自白派」較大的不同,欣祺的詩乍看是自我辯詰的內轉式表達,但她往往是將自我放置在「我」和「你」這一組對話性的關係中來形成交互的參照(如〈白夜〉:「祈禱時,給我看你空空的手/我就告訴你人怎麼變成石頭」)、〈厭倦修辭〉:「你問我有沒有語言到達不了的地方/我不知道,不知道去就是來」),也常常用「我們」來召喚共同的情緒體驗(〈靜物考古〉:「我們閉嘴,向內看見外面的世界」、〈密林〉:「回看昨天的我們,小小的,被悲哀握在掌心。」、〈預感〉:「我們心中空洞洞的美麗/難道就是全部嗎」)。欣祺詩中的人稱代詞比較豐富,「你」字的用法頻繁且多指,有時她詩中的「你」很可能也是「我」的一個分身,「你」的出現既是構造一個抒情對象、辯難對手,更與她思維中對一種對稱性和鏡像性的偏愛有關。對稱和鏡像的存在,形成了基本的思辨張力,也營造出耐人尋味的圖式之美、結構之美。我不止一次在她詩中看到完全對稱的意象,比如:
〈輓歌〉
寫「心」這個字
需要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
和一塊手形的雲。
〈馬語者〉
入夜以後,我原諒所有睡眠甜美的人
如果世界能原諒兩塊一模一樣的鏽
我也能原諒血與骨,原諒引力
「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兩塊一模一樣的鏽」都是在描述不可能出現的重合,可是因其極難出現,又給讀者帶來難以言喻的想像的美感。用一模一樣的樹葉和一塊手形的雲來寫成「心」字,如此精妙形象,使人無法不傾心又佩服。而兩塊不可能出現的「一模一樣的鏽」,或許象徵著人與人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樣的血肉創口,我們能在這樣的詩行中感到詩人悲憫的善意,能獲得疼痛的感應和慰藉。每當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欣祺她在寫作中感到的「存在之難,難於狀物」(〈我作為鶴的一生〉)都在這樣對稱的意象間實現了。同時,自白與思辨可能造成的封閉之境,也在她對他人處境的關切中,在「我」、「你」和「她」構成的錯綜交互中,在「我們」共同的情感處境中,不再構成閉鎖的威脅,此間形成的交響,就如欣祺的一句詩所描述的「葉隙間的自我晃動如鈴」(〈離島生活〉),最終還是掀開並晃動出更為多面的「自我」,也賦予了語言更為靈動的音樂性。
寫作的療癒性就是在這之間產生的嗎?閱讀的親密感也是在這其間產生的吧?寫詩與讀詩有時也像是作者與讀者共同參與才
能完成的一個儀式。「儀式感」是我在欣祺詩中反覆感受到的關鍵詞,更多的時候,她在詩中舉行的儀式,是結束式、是悼念和輓歌。〈密林〉是欣祺在祖父去世之後寫的一首詩,我清晰記得她在捷運上跟我講述親人離世以及家人病痛給她的影響時,神情裡仍有鮮活的痛苦。有時,越是血脈相連的家人,越無法通過直接的傾訴和抒情來溝通彼此,對他們的愛只能以畫面、影像的方式深深鑿刻在記憶中,撕扯又恢復的家庭關係永遠是一則掩埋又破土的自我成長的寓言。在〈密林〉這首詩裡,祖父、父親與「我」的關係被呈現一個在梅雨時節的密林之中一前一後行走的狀態,整體的低氣壓和距離感並沒有讓「我」與父輩形成簡單的對峙關係,在對祖父的紀念儀式中,「我」與父親似乎也可以「交換位置」:
〈密林〉
我們一前一後走著,梅雨時節的
兩只蜻蜓,低低盤旋。
這些日子,我造殼,然後拆解它
我一次次和那個看日落的人交換位置
在梳頭的手,揀菜的手,數錢的手中
安放,睡去,遺忘。
寫作的儀式性就在於對「安放」和「遺忘」的反覆描畫,它既是悼念,也是抵抗遺忘、抵抗消失的生命被輕易塗抹。這種感受在疫情時更為逼仄,可是欣祺也能將這種最為沉重的心痛,交付於「更輕的東西」,為沉沒的生命祈禱、留駐,以緩慢至幾乎靜止的語速來完成一場紀念的儀式:
〈降臨〉
先降臨的是雨,然後才是潮溼和轟鳴
先暗下去的是被漏失的臉孔
已在靜默中漂洗過無數遍
……
而最明亮的這世界,永遠有人慢慢下沉
比雨後的水汽更輕。
變得「更輕」在欣祺的詩裡幾乎可以看作一個死亡的隱喻,而在哀悼的儀式中,消逝的傷痛也能在身體的「變輕」中稍微得到緩解,這種想像本身就是美麗且療癒的:
〈離島生活〉
我問他是不是那些來不及哀悼的人
都會變成我們頭髮上的羽毛
失去重量。
〈輓歌〉
悲傷是一床越來越輕的棉被
在欣祺的詩中,很少有靜止的事物,不僅人稱之間的關係和位置在變換,連意象本身都在發生重量和形態的改變,她所注視的事物往往在「變得更輕」、「下沉」、「降落」、「折返」或「自旋」,這些動態與她對生命、意念的運動軌跡的想像相關,同時也構成了詩作語言本身豐富的層次感。讀欣祺的詩,我最迷戀的就是這種猶如複瓣花卉張開又收攏的層次感,在精妙的比喻和輕靈律動的意象間,又暗布著冷峻的思辨張力和果決的判斷,這些特點在她後代表作中(如〈預感〉、〈我作為鶴的一生〉和〈假贈高達〉)都臻於圓熟。這幾首詩一開始都讓我驚詫,原來疼痛、意念、輕而弱的事物也能在語言中結晶出另一種美,能對生命幽暗的內核發出不可回避的問詢,這一切是以「眼淚」和「狀物之痛」為代價的:「這自旋的一夜,眼淚在周身結晶/狀物之痛引我去顏色的天堂。」(〈我作為鶴的一生〉)。或許正是因為總得以內心最深的痛感才能催動這一束複瓣的語言再展開一點點,所以她的寫作是屬於慢而深、少而精的一類,如今終於可以集成一本詩集與讀者見面,應是讓很多默默關注欣祺多年的人早已期盼的事。
我從和她在花蓮分別的那刻起就一直期盼著。直到我們行程快結束的前一晚,她才敲了敲我的房門,很鄭重地告訴我她願意加入我的詩社。我笑道,其實根本不存在什麼詩社,但因為她答應了,以後也就有了。臨別時我送了她一本書,在扉頁寫著:「我在語言中遭遇你、辨認你,而我卻有語言無法表達的喜悅。」如今讀她的詩集,更是如此。
二○二三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