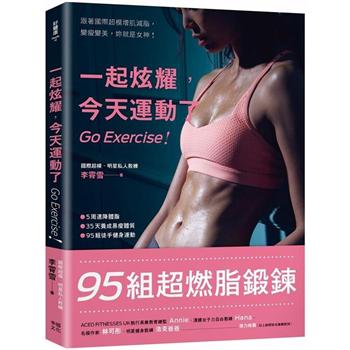1 婚禮
如果主角不是我,那真是一場美妙的婚禮!
陽光亮麗耀眼,親戚們互相寒暄著。新郎出現了――站在彌撒臺下等著我的,是我高中時就認識的那個男人,他在二次大戰後打過韓戰,婚禮上一身戎裝十分英挺。新郎爾耐斯特˙保寧(Ernest Borgnine)穿著軍服實在非常英挺!
我認識比爾(Bill,譯註:即新郎)已經七年,但是仍覺得對他不甚瞭解。來賓們抓著侍者對今天的一對新人問東問西。
不知道父母如何應對人家的胡說八道――「女兒都出閣了,你們也不年輕嘍!」我們沒有汽車,沒有房子,沒有家當,也沒有純銀餐具。我以前一直納悶,缺少一套純銀餐具,不知道還算不算正式成家。現在,比爾還有一年才大專畢業,別說是純銀餐具了,連工作都還沒有著落。毫無疑問,我父母答應這門親事真是失算!
婚禮上諸事不順。我小時候常夢想能辦一場超越我們家財力所能負擔的婚禮。如今我穿著一件減價時買來、大得不像樣的婚紗禮服;為我們用匣式照相機拍結婚照的,是我堂哥;而我母親為了準備招待親友的喜宴,忙著把她弄了一個早上的烤火腿送到婚禮現場,以致滿身火腿味。
我的夢想怎麼辦?我一直懷抱鴻鵠壯志――我希望專科畢業後就到紐約,擔任紐約時報的駐外特派員,如果此計不成,退而求其次,我希望能為俄亥俄州的但敦先鋒報(Dayton Herald)撰寫訃聞。
現在,我才畢業兩個星期,連未來的職責是什麼都不清楚,卻即將走上復活教堂的長通道,宣誓「我願與他廝守一生」。
我和在彌撒臺下等著我的新郎目光交接,物質匱乏和夢想幻滅看來都不重要了。我是怎麼了?我愛上了這個人。我們真是一對璧人,有那麼多共同點――這才重要嘛!
我們倆都是一次只嚼半條口香糖,卻把另外半條留起來,(世上有多少人會做這種事?)我們都喜歡美國幽默劇作家羅伯特˙班卻里(Robert Benchley, 1889―1994)的詼諧風趣,都痛恨共產主義。還有什麼?噢,對了,看牙醫都拖拖拉拉不乾脆。我們認識的很多夫婦在結婚時,都還沒有這麼多共同點呢!
當我跪在他的旁邊,透過白面紗看到他的耳朵上有一團白漆,身上則有一股濃濃的松節油味。他在暑假期間替人油漆房子賺外快,以後這事就不必了,他一定可以找到更體面的工作。再說,油漆是易燃物,我可不喜歡和一個不能在他旁邊點火柴的人在一起。
比爾很需要工作,但是在他工作之前,我得先花幾年時間把他調教成稱職的丈夫。首先,我要對他耳提面命――按時剪頭髮。老天啊,我真討厭他披頭散髮,活像是剛用吸塵器吸過的長毛地毯。
還有,他的飲食習慣也要改一改了。他不喜歡喝湯,但是在我娘家,無論多濃的肉汁都可以當湯喝;他常吃蔬菜,我則把蔬菜當成壁爐前的裝飾品;至於我這下半輩子,要跟一個早餐從不吃冷食的人一同生活,那真是難以想像啊!
我們婚禮的男儐相是常跟比爾玩撲克牌的死黨艾迪˙菲利普(Ed Phillips),他把戒指交給了比爾。比爾把戒指套進我的手指時,我微微一笑,艾迪和他們那群小男人很快就要過氣了,他們別想再和比爾混單身漢生活――撲克牌一打打到天亮。從現在起,是我們兩人的天地了,我們將一同欣賞落日,彼此對望。
與比爾並肩站在彌撒臺下時,我心裡掙扎著要不要替他設定一個作息時間表。和他交往的這幾年中,他總是遲到。我正發誓要永遠相守的這個人,每次看球賽都漏掉唱國歌或開球的那一段,去音樂會則絕對看不到拉起布幕、序曲響起的那一刻。他現在看起來這麼輕鬆,對於我即將調教他的一切都還渾然不知,我要教他;養成用完原子筆就把筆蓋套回去的好習慣,免得下次要用的時候筆芯都乾了;我也要教他:左撇子用完電話後如何掛電話,省得把習慣用右手的人摘得雞飛狗跳。
神父是波蘭後裔,我努力從他的口音和彌撒使用的拉丁文辨識他說的話,隨後我聽見他提高嗓門清晰地訓諭:「比爾,你將成為一家之長,而爾瑪,妳將成為家庭的重心。」
他想得美!他把這當成了什麼啊?一個小鬼因為比大小的緣故,結果選了五分錢硬幣,卻不拿十分錢的銅板?我見識過這種「家庭重心」的細節瑣事;受過四年大專教育,我還是得埋沒長才,連丈夫閒來打保齡球時都得陪在一旁。
也許我可以叫比爾去當家庭的重心――至少偶爾和他換著做做看嘛!
「現在我宣布你們結為夫妻。」
可能除了「火箭正升空」和「我國正處於戰爭狀態」這類的話之外,少有幾個句子像上一段話那麼嚴肅。
我們的婚宴是在市郊一個社交大廳舉行,外戰老兵團體(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of United States)多半在那裡辦聚會。折疊椅靠牆擺,整個大廳看起來跟公路局車站的候車大廳很像。大廳中央一張長桌上鋪了白色的桌巾紙,蛋糕和火腿三明治堆成的小山都在桌上。
一輛車停在大廳門口,一對夫婦和六個小孩從車裡鑽出來,那個男的兀自嚷著:「查理(Charlie)來了!啤酒在哪裡?」
比爾看著我問道:「是你們家的親戚嗎?」
我點點頭說:「是我姑丈。」
接下來的那個大半天,我已記憶模糊――我們兩家的親戚分坐大廳兩邊,好像交戰雙方壁壘分明…‥幾百個不相識的小孩滿臉塗著蛋糕跑來跑去…‥女儐相們個個一臉「幸好這是妳結婚,不是我」的表情……我母親呢,就聽她一個勁兒地大呼小叫,因為桌上的火腿都吃光了。
一個前來道賀的客人問我們要去哪兒度蜜月,我告訴她,我本來很想到紐約看一場百老匯表演,在一間豪華旅館下榻,半夜坐馬車逛中央公園。
「所以,你們現在決定要去哪兒度蜜月?」她追問道。
「我們要到密西根州的拉維湖(Larvae Lake)釣魚。」
她笑著說:「真浪漫。」
比爾向我求婚的時候,把我的訂婚戒指掛在雪茄上,還把菸都點燃了。嫁給這樣一個男人,我還能期待什麼!
婚禮當天下午四點左右,四下不見比爾的踪影,我到處找他。最後在大廳外的停車場上,我發現他和艾迪及那幫死黨湊在一起,邊說笑邊喝啤酒。他回到我身邊時,那群人正要開始打撲克牌呢!
婚姻似乎比我想像得還要艱難許多。……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親愛的,只剩下我和你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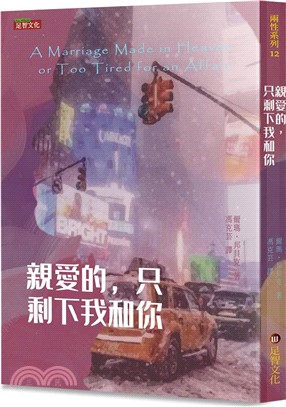 |
親愛的,只剩下我和你 作者:爾瑪.邦貝克 / 譯者:馮克芸 出版社: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3-10 規格:21cm*15cm*1.7cm (高/寬/厚) / 1 / 平裝 / 276頁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親愛的,只剩下我和你
關燈以後,天亮以前,親愛的,只剩下我和你了。
迎接朦朧未明的天光,面對懵懂未知的未來,
就讓我們彼此扶持、攜手共度。
王子、公主結婚後,究竟如何度日?作者以輕鬆詼諧的筆調、饒富智慧的語句,鋪陳婚姻關係的寫實面貌,進行赤裸真實的婚姻告解:
‧為什麼戀愛時的心跳頻率,在蜜月後就介於昏迷和死亡之間?
‧我要去跟誰偷情,好讓人把我從婚姻勞作中革職?
‧結婚多年之後,羅曼蒂克到哪裡去了?
‧為何孩子總是抱怨父母的穿著太年輕,思想卻太陳腐?
既然妻子與母親難為,老公與奶爸難做,那幹嘛還要結婚?
也許是,因為生命是一支你想與配偶同時起步收腳的舞蹈,當事業落幕、朋友走遠、孩子長大時,你還可以回家與親愛的老伴共舞;在去日苦多、來日無多的年紀,還有一個人陪你哭笑、跟著操煩,無論疾病或健康,都彼此扶持、攜手共度……
作者簡介:
爾瑪.邦貝克(Erma Bombeck)
著有許多暢銷書,包括《母職:歷史上次悠久的專業》、《肖似護照相片,你就該回家》。她和丈夫定居美國亞利桑納州天堂谷,婚姻美滿,夫妻倆皆是懶得外遇。爾瑪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去世。
譯者簡介:
馮克芸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碩士,曾獲第四屆中央日報探親文學類首獎、小說獎佳作。目前從事編譯工作。
章節試閱
1 婚禮
如果主角不是我,那真是一場美妙的婚禮!
陽光亮麗耀眼,親戚們互相寒暄著。新郎出現了――站在彌撒臺下等著我的,是我高中時就認識的那個男人,他在二次大戰後打過韓戰,婚禮上一身戎裝十分英挺。新郎爾耐斯特˙保寧(Ernest Borgnine)穿著軍服實在非常英挺!
我認識比爾(Bill,譯註:即新郎)已經七年,但是仍覺得對他不甚瞭解。來賓們抓著侍者對今天的一對新人問東問西。
不知道父母如何應對人家的胡說八道――「女兒都出閣了,你們也不年輕嘍!」我們沒有汽車,沒有房子,沒有家當,也沒有純銀餐具。我以前一直納悶,缺少一套純...
如果主角不是我,那真是一場美妙的婚禮!
陽光亮麗耀眼,親戚們互相寒暄著。新郎出現了――站在彌撒臺下等著我的,是我高中時就認識的那個男人,他在二次大戰後打過韓戰,婚禮上一身戎裝十分英挺。新郎爾耐斯特˙保寧(Ernest Borgnine)穿著軍服實在非常英挺!
我認識比爾(Bill,譯註:即新郎)已經七年,但是仍覺得對他不甚瞭解。來賓們抓著侍者對今天的一對新人問東問西。
不知道父母如何應對人家的胡說八道――「女兒都出閣了,你們也不年輕嘍!」我們沒有汽車,沒有房子,沒有家當,也沒有純銀餐具。我以前一直納悶,缺少一套純...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一九四九
1. 婚禮
2. 生活在愛中
3. 「闖入我們婚姻的……」
4. 無論疾病或健康
一九五三
5. 「妳不再年輕囉!」
一九五四~一九五八
6. 子女
7. 快樂的代價
8. 無論貧富
一九五九
9. 同窗團聚
10. 朋友何用?
一九六四
11. 空巢危機
12. 革命旋風
13. 「請眾人為我賜福,因為我有罪」
一九六七
14. 大錯
15. 年久失修的房子
16. 創意爭辯
一九七一
17. 青少年
18. 性革命
一九七四
19. 恐龍
20. 「羅曼蒂克」怎麼了?
21. 為了過得更好,還是為找事做?
22. 嗨!爸,嗎,我回來了!
23. 道德觀不同,一家人永無寧日
一九七九
24. ...
1. 婚禮
2. 生活在愛中
3. 「闖入我們婚姻的……」
4. 無論疾病或健康
一九五三
5. 「妳不再年輕囉!」
一九五四~一九五八
6. 子女
7. 快樂的代價
8. 無論貧富
一九五九
9. 同窗團聚
10. 朋友何用?
一九六四
11. 空巢危機
12. 革命旋風
13. 「請眾人為我賜福,因為我有罪」
一九六七
14. 大錯
15. 年久失修的房子
16. 創意爭辯
一九七一
17. 青少年
18. 性革命
一九七四
19. 恐龍
20. 「羅曼蒂克」怎麼了?
21. 為了過得更好,還是為找事做?
22. 嗨!爸,嗎,我回來了!
23. 道德觀不同,一家人永無寧日
一九七九
24.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