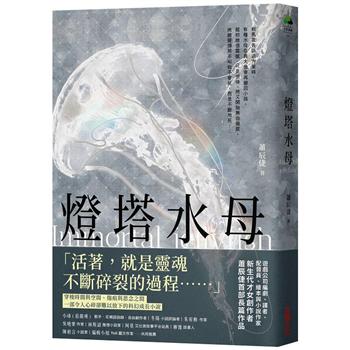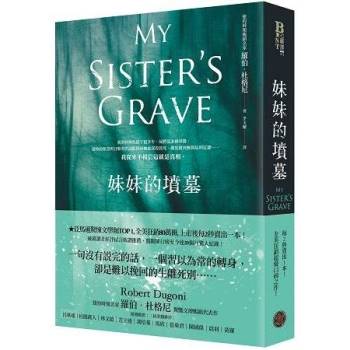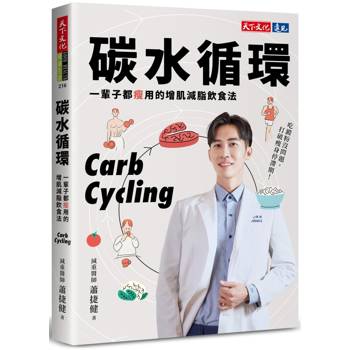序言
只要看著尤莉亞(Julia)空洞又呆滯的雙眼,就知道一定發生了可怕的事。不斷有平民從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Donbas)撤離出來,戰爭在此肆虐,已經持續了八年,現在的情況又更殘酷。
這區的火車只開到頓涅茨克州(Donetsk Oblast)的臨時首府,克拉馬托爾斯克(Kramatorsk)。在俄國入侵之前有十五萬人居住於此。三十四歲的尤莉亞是計算機科學講師,興趣是背包旅行,她想幫助突然被迫離開家園的人們。雖然在頓巴斯站出來投入志願活動的人不多,但整個烏克蘭社會幾乎都動了起來。眾多志願者協助分配食物與藥品、將人們帶離砲火地區、修理運來的汽車、為士兵或自己準備裝備。火車站裡面也有許多提供支援的人,鳥瞰克拉馬托爾斯克的火車站呈現大寫字母H,可以看到志願者在周圍負責指揮人流並維持秩序。儘管四月陽光和煦,但待在街上幾個小時還是會讓人冷到起雞皮疙瘩,多虧這些志願者,人們才能在綠色的帳篷裡享用熱食與飲料,保持暖和。
撤離的人有不少老弱婦孺。對老人來說相當艱辛,因為要前往克拉馬托爾斯克,要轉乘好幾趟車,跨越一百多公里。有些人要逃離被砲火襲擊的城鎮,卻在等待巴士的時候遭遇不幸。不過在克拉馬托爾斯克,可以說暫時脫離險境。
尤莉亞走向綠色帳篷,準備在火車站開始她第一天的工作。她一直都在幫忙,但人們不斷撤離,所以她也不會長久待在一個地方。因為前線正向克拉馬托爾斯克推進,政府好幾個星期前就已經呼籲非志願者,或非服務於重大基礎設施的人離開頓巴斯,以利軍隊作業;這座飽受砲火蹂躪的城市正迅速衰敗,變得荒蕪。尤莉亞想有所作為,所以不打算離開,因此她得加入當地的志願者,或是去基礎設施幫忙,否則自己留在那裡只會成為負擔。
其他志願者原本以為她想要插隊上月台,在交談後才知道她想幫忙,他們這才讓她過到月台。她走了幾步,手機突然震動,然而廉價智慧型手機在強光下什麼也看不清楚,於是她退到角落,直到牆壁遮住陽光才終於能讀簡訊。她在戰爭初期遇到的一位記者問她,撤離的巴士會從哪裡離開。尤莉亞的英文能力有限,花了幾分鐘才弄懂記者在問什麼,回答說她不知道。要不是這封簡訊,她大概已經踏進帳篷、套上了志願者穿的螢光背心。
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突然響起。尤莉亞這時才親身體會到,原來飛彈落下的前一刻,是聽不見聲響的,她以為是有人在很近的地方開槍,可能在車站廣場的另一側。她跑向車站入口才意識到自己做了蠢事——她應該留在原地並趴在地上。兩顆近五百公斤的集束炸彈在車站上空分解,散成子炸彈後造成大面積殺傷,而子炸彈不會同時爆炸,所以會讓人覺得地面好像裂開了。尤莉亞的眼角瞥見閃爍、煙霧、倒落地面的綠色帳篷,所有東西都被煙霧與塵埃抹成灰色。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靠著雙腿下意識地往前走。她看到火車站玻璃門後的人群,知道自己進不去,旁邊有幾個人跪著躲在牆後面,她就過去一起雙膝跪地,彎下腰、低下頭。爆炸聲突然從另一頭響起,大概有破片飛來打到什麼,尤莉亞感覺灰泥灑在她背上。她很害怕,不知該如何保護自己。
爆炸停止後,充滿痛苦與折磨的尖叫聲起此彼落。入口前的停車場有輛車在燃燒,旁邊的車也接連起火,尤莉亞擔心車子會爆炸,因此趕緊跑離那裡。她在迷茫中衝向最近的避難處,轉過身時看到一名男子,揹著受傷的小女孩,尤莉亞問他是否需要幫助,他們就一起扛起小女孩,把她放上長椅。男子提起孩子的上衣,遍體鱗傷非常嚴重,脖子上卡著破片,但沒有流血,似乎沒有傷及動脈。尤莉亞看到警車,擋下它的去路,把警察帶過來,請求警察為女孩急救。
好像有什麼東西把尤莉亞推向車站,不過她不確定是什麼,或許是好奇?她想看看自己究竟經歷了什麼,以及可能發生的事。尖叫聲傳來,雖然她很想幫忙,卻沒有太多能做的事,當時她的背包裡有一卷彈性繃帶,只是煙霧散去後,眼前可怕的景象令她猝不及防。她沒想到這種爆炸不只會撕裂四肢,也能直接把身體炸成碎片。人肉、器官、頭骨碎片四散在車站周圍的行李箱、手提包、背包和娃娃之間。地上躺著屍體,有人臉上卡著破片。地上四處都是大片血跡,無法繞過,尤莉亞只能踩著血水走過去。
她無法幫助重傷者,還好已有醫護人員在處理,不過重傷的人比醫護人員還要多。驚魂未定的尤莉亞靠著腎上腺素,勉強攙扶一些還能行走的人離開車站。當尤莉亞快要走到其中一個避難所時,聽到有人從教堂大喊「來這裡」,因為教堂裡有個安全的地下室。尤莉亞前後帶了一位老太太與一位坐在輪椅上、雙腿流著血的男人過去。第三趟時,她看到長椅上有一位老太太。
「妳能走路嗎?」尤莉亞問。
「我有條腿很痛。」長椅上的老太太回答。
「我看看。」
尤莉亞摸著老太太的腿,確認整條腿都在。當這位計算機科學家把手伸向腹部時,發現有塊她沒注意到的突起物。她稍微拉起老太太的上衣,才看見外露的腸子,顧不上內心的驚恐,她馬上向醫護人員求救。
尤莉亞再次走向車站,看見有個女人站在那,看起來驚魂未定,但還能走路。她周圍有很多包包,尤莉亞拿起她的行李,問她還有沒有同行的人。
「兒子,但死了。」烏克蘭婦人冷冷地回答。
尤莉亞說服她躲在教堂裡,因為危險尚未解除,可能會有更多飛彈掉下來。
她回到車站時幾乎已經沒人了,只剩下柳柏芙(Lyubov)貼在女兒的屍體上。孩子的臉少了一半,眼睛處插著破片。幾十公尺外躺著圓點U戰術飛彈的殘骸,上面寫著「為了孩子」——這屢次出現的口號說明此次空襲,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報復;因為烏克蘭控制的城市對不被承認的共和國進行砲擊。這次空襲造成六十一人死亡,其中有六名孩童,以及一百二十一人受傷。
尤莉亞不斷哀求倒在女兒血泊中的柳柏芙去教堂躲好,最後終於說服了她。尤莉亞拎著她的東西,而柳柏芙抱起貓。她沒有哭,也沒有表現出任何情緒,好似什麼也沒發生,不過走到一半,她突然停下。
「我有女兒的護照!」她叫了起來。
「我來幫你,要怎麼做?」尤莉亞問。
「護照可以認出她。」
尤莉亞承諾把她送出去後會繼續幫她,所以後來尤莉亞帶著護照回去。她知道屍體在哪,也知道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只是屍體已經不在,收屍團隊已經把她帶走了。尤利亞扶著柳柏芙,一邊走一邊找收留死者的地方。她和柳柏芙說了許多話,最後變得比較熟識,得知柳柏芙的另一個女兒在文尼察(Vinnytsia),是她勸母親撤離的。她們來自巴赫姆特(Bakhmut),那裡的局勢會在接下來的幾週內變得危險。後來警察告訴他們,屍體指認將在隔天進行,也告訴他們相關醫療機構的地址。尤利亞把柳柏芙送到教堂,留下自己的電話號碼,告訴柳柏芙隔天可以陪她去指認,要是地下室不舒服,也願意提供她住宿,若有任何需要幫助的地方都可以找她。
經歷了這一切,尤莉亞的情緒非常激動,要是這時遇到俄羅斯人,一定會馬上把他撕成碎片。直到回到家她才平復心情。
父親和祖父都在家,母親因為承受不住接連的壓力,得知俄羅斯在基輔地區的罪行後,不久前收拾好行李,已從克拉馬托爾斯克離開。因為頒布禁酒令,尤莉亞一週前自己釀了啤酒,她應該讓酒再陳釀兩個星期的,但她不想等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她邊說邊打開瓶子,把酒遞給父親和祖父,告訴他們自己今天經歷了多麼可怕的事。
「你怎麼會這麼傻!」父親說。
幸好父親不知道她腦裡醞釀已久的計劃。二月二十四日,當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攻擊時,她立刻致電徵兵處,想要加入國土防衛軍的行列。她當時得到的回應是:「我們會在需要你的時候回電。」但此後她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在克拉馬托爾斯克受到襲擊之後,她決定再試一次,這次她沒有打電話,而是直接到徵兵處申請入伍。雖然她想入伍的理由很老套——她想在祖國需要的時候幫上忙,但這同時也讓她有理由繼續留在家園。
尤莉亞不是唯一決心入伍的人,自願入伍的人日漸增多。根據二〇二二年八月的民調顯示,有兩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在軍警部門服役過;近四成的受訪者參與志願活動;分別有百分之八十一與百分之六十的人捐款給軍隊和人道援助。正是因為民眾參與和出力,才會讓世上最大的軍隊之一陷入困境,使其未能達成預期的目標。
二〇二二年二月,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攻擊,這在現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不只因為這是歐陸在二戰後的首次武裝衝突,將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而且造成的衝擊不可逆轉,也因為這是現代史上,受攻擊的社會總體參與度最高的一次。
烏克蘭人不僅大規模自願上前線,也普遍參與公民抵抗。他們為士兵及平民募款、組織援助,為了保衛自己的城鎮建造路障、準備汽油彈、焊製反坦克拒馬;或只是帶些茶點去軍事崗哨。他們盡己所能參與其中,有些人做偉大的事,有些人做小事,每個人都很重要。起身抵抗需要勇氣。志願者會進入砲火區送餐點、藥物或必要裝備。即使是沒有熊心豹膽的人,也在遠處幫忙;送來一車車的必需品,讓志願者去戰場上分發。其他人持續工作,以提供資金給平民和軍隊。
烏克蘭人好似已經內化了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暴政》(On Tyranny)一書中的第十二條規則:
「盡可能地勇敢」:
若我們之中無人準備為自由而死,所有人都會死於暴政。
在攻擊最初的幾個小時裡,情況很糟,甚至是絕望的,但烏克蘭人沒有打算投降。抵抗與對勝利的信念前所未有地團結起這個國家。無論烏克蘭最終要付出多高的代價,烏克蘭人都不再是過去的烏克蘭人。
這本書是我二〇二二年一月到九月在烏克蘭的工作成果。當時我為《全面週刊》(Tygodnik Powszechny)撰寫報導,因此週刊讀者會在本書讀到一些先前的文章,不過有些部分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