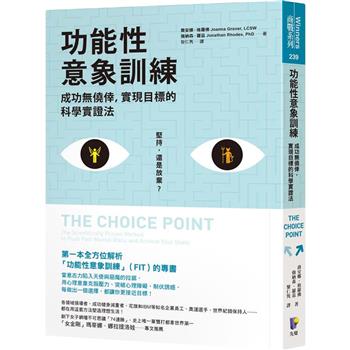沒有計畫,沒有目的地,
只要出門,就是旅行,是所謂無謀小旅行。
只要出門,就是旅行,是所謂無謀小旅行。
故事要從二○○九年的初春開始說起,十天的東京旅行,
自此開啟了獨自一人旅行的開關,也確立了無謀小旅行的最佳模式。
過去總以為旅行必須結伴才叫快樂、才有安全感,
就算自我決斷力與危機防禦力都提升了,
還要面對身邊人對於獨自出國旅行的質疑:
「是個性孤僻?不好相處?揪不到人?
還是有什麼性格上的缺陷?」
不過一旦跨過這面子問題,就沒什麼好胡思亂想的了。
──開始一個人旅行之後,就很難回頭了。
不需要什麼詳盡計畫,可能跟隨著日本小說或電影場景主題,
甚至只看當天起床時的心情,隨興安排或調整行程。
不刻意追逐觀光景點,也放下必去必吃必買的執念,
而是與自己同行的自在。
「一個人旅行不是孤獨或寂寞的問題,而是不必顧慮他人關於好玩或不好玩的感受,自己以為好玩的地方就算被他人視為冷門景點也無所謂,甚至算不算景點都沒有關係,我喜歡這種旅行模式。」──米果
本書特色
旅行中的每個瞬間,都是最美的定格
特別邀請速寫插畫家康普特,為本書重現每篇遊記中的經典畫面,一起流連可能對你也深具意義的日本角落,喚起旅行當下的感動與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