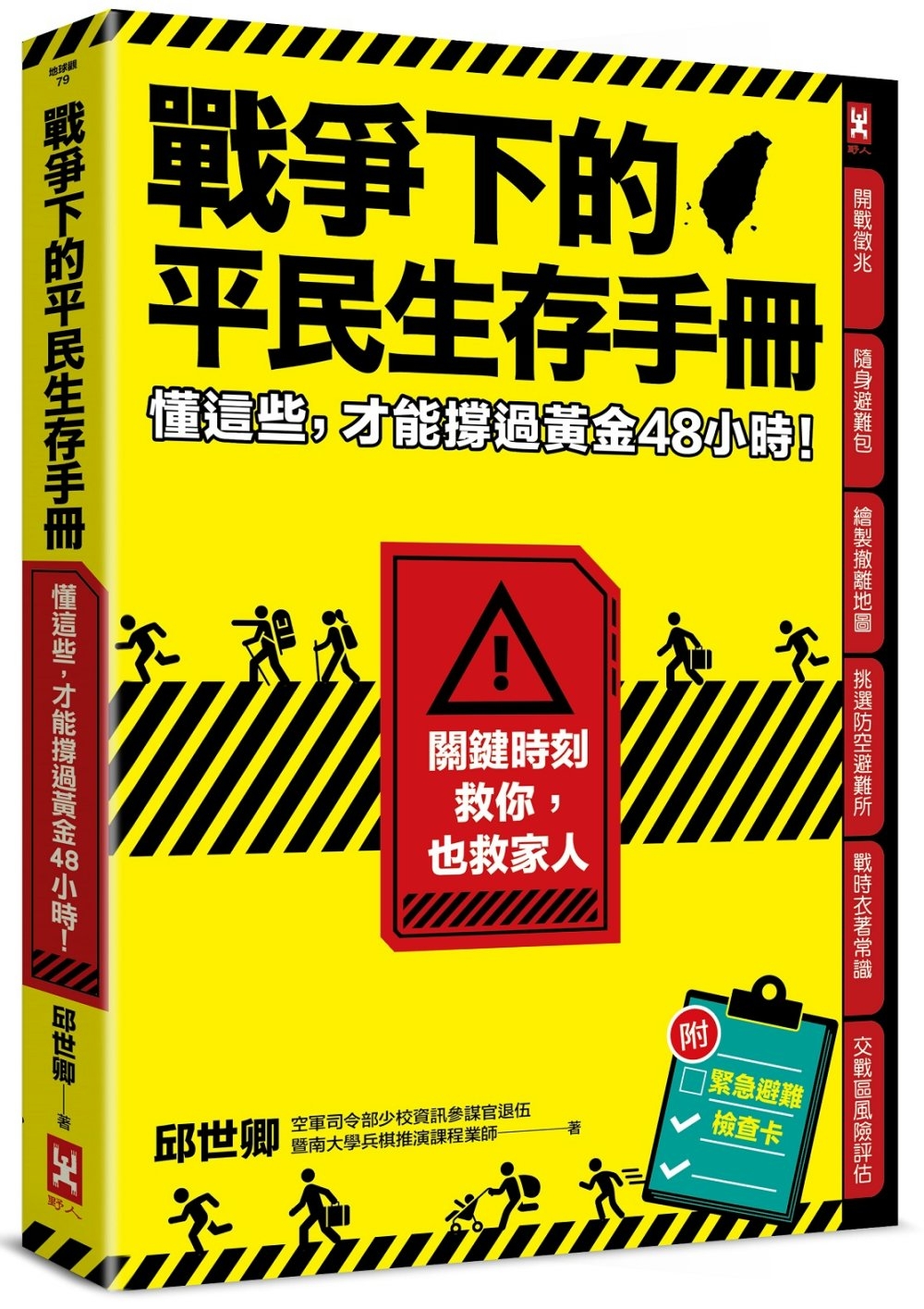第一章 在平常那條路上的我們
沒有什麼美麗的死亡。
如果有的話,不流出鮮血的死法,或許就是最美麗的。
×
不只是外縣市,實際上東京也到處遍布廢棄工廠。
這棟建築物或許該說是高度經濟成長期的遺物。長期密閉又被燻黑的漆黑空間裡,井然有序地排列著生鏽的鐵製機械。
過去這間工廠應該曾不分晝夜地製造著某種物品。牆壁格外厚實,天花板卻很低,照明設備不多。幾乎所有日光燈都被拆除,或是因為年久劣化而破裂。廢棄的工廠當然早已被斷電,就算打開開關也沒有任何反應,是個讓人覺得喘不過氣又昏暗的地方。
只有陽光透過等距嵌入的小窗戶照進室內,淡淡照亮遺留在這座工廠內的物體。
「唔呼……呼喔……唔……!」
頭上紋著刺青的男人緊抱住自己的身體,就連「好痛」兩字都沒辦法清楚說出口。雙腿不停掙扎,使堆積在地板上的煤灰及塵埃揚起,四處飛揚。
「拜……別殺……我──」
最後男人——不再動作。
「……四十五秒。」
一之瀨朱理看了一眼手錶,將右手的手槍放回掛在左胸前背袋的槍套裡。黑色西裝外套上別著一個發亮且鑲著金邊的黑色圓形領章。形狀雖然跟搜查一課的刑警配戴的紅色圓形徽章相似,顏色卻是深沉的黑。
這個黑色圓形徽章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不受限於警察法第六十七條以及警察職務執行法第七條中關於持有槍械的規定,得到了特別許可。
持有填裝實彈,而非空包彈手槍的搜查官。
然而現在的朱理不覺得那是一項重責。
「真難看……」
他只覺得又看到了一場腐敗的死亡。
朱理無法對變成死屍的男人送上任何弔唁的目光。
冰冷又混濁的雙眼微微顫動。朱理那對晦暗的黑色眼瞳,就像在俯視著一隻死去的害蟲,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死亡。
就像被撈上岸的蝦子一樣不斷掙扎的刺青男,雙眼痛苦地睜大。男人最後用雙手緊緊抓住胸口,蜷起身子朝右側倒去,就在這樣的狀態下變得僵硬。
臉色蒼白的男人口中淌下口水,那滴唾液靜靜地滴落,弄濕了地板上的塵埃,將一小部分渲染成灰色。
……自私的殺人犯。強姦了七名女子,殺害其中六名後埋在深山裡。唯一存活下來的女子只留下線索就自殺了。以現行法來說,那是僅供參考的間接證據。依據那些微的線索找出那個男人之後,朱理給他一項提議。
是要認罪,還是要當場死在這裡。
然而男人沒有做出任何選擇,逃跑了。他落荒而逃的行動,等同於承認了殺人犯行。
刺青男還說著「拜託別殺我」──臨死前都表現出對於活下去的執著。
──為什麼自己殺了人卻害怕被殺呢?
朱理面不改色地操作智慧型手機,貼在耳邊。
「……我是一之瀨。是課長嗎?對。我有事要向你報告。」
水分攝取不足的喉嚨乾渴,讓他本就低沉的嗓音更加沙啞。
「重要嫌疑人死亡了。」
×
在一排警視廳搜查一課強行犯組的辦公桌後方,還有另一間辦公室。
那是獵奇殺人事件特別搜查課──大多都簡稱為奇特搜,是個專門調查非正常死亡、獵奇以及奇異殺人事件的部門,牆上掛著三名所屬搜查官的名牌。
挺著大肚腩坐在主管座位上的,是四年前從搜查一課調到奇特搜的課長,神樂坂修造。平常總是穿著鮭魚粉的西裝背心,還有一張看起來性格開朗的福神臉是他的個人特色。掛在椅背的灰色外套上,別著證明奇特搜搜查官身分的黑色金邊圓形徽章。由於奇特搜偵查的都是特殊案件,因此這個徽章被警察職員成為「不祥之黑」。
「長時間用電腦處理工作真累人……」
就跟大多數的民營企業一樣,警察組織也為了速度及效率,邁向無紙化。搜查資料大多都是以檔案共享。
這讓神樂坂課長感受到不同於昭和時代的壓力,按了按肩膀。對於凡事都靠紙筆解決的傳統世代的老年人來說,長時間用電腦處理工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摘下具備阻斷藍光效果的老花眼鏡,他揉了揉出油的鼻梁。
「適度的休息也很重要」——神樂坂課長對自己這麼說。
他拉開抽屜,翻開自己的私人相簿。照片上的他面帶幸福微笑,身旁有妻子及女兒陪伴,以及調皮地吐出舌頭的愛犬。像這樣看著泛黃的全家福,被淒慘生活蹂躪的心靈就感覺變得滋潤起來。
平時就被要求保持紀律言行的警官,會在除了工作之外──也就是從家庭中尋求生存動力是理所當然的欲求。
「課長~」
這道慵懶的聲音讓神樂坂課長收起笑容,繃起臉來。
「前科資料完成比對了,我寄給你喔。」
今年二月,帶著一些隱情分配到這個部門的新人──佐藤健一,在三臺大型電腦螢幕圍起的辦公桌前翹著腳,托著臉頰散漫地坐著,時不時喝一口大罐的能量飲料,只有右手操作滑鼠的點擊聲十分忙碌。
「動……動作真快啊,佐藤。」
「也沒有多快吧,只是把自動驗證篩選出來的資料貼上去而已。這種事情任誰都會做。」——他的語氣中不帶任何嘲諷,是真的這麼想。
神樂坂課長將相簿收進抽屜裡,重新戴上老花眼鏡,連上共用網路打開資料。點擊經過壓縮的檔案進行解壓縮後,畫面上一口氣出現了滿滿的資料,這讓他的雙眼頓時更加疲憊,他呼出一口鼓舞的嘆息。
「照你的經歷來說,原本不該讓你處理這種無聊的工作啊。」
「……」——佐藤彈了一下放在辦公桌上,堅決不戴上的黑色圓形徽章。
「佐藤,抱歉,一直跟你說這種話──」
健一默默地喝光能量飲料,將空瓶「哐」地一聲放到桌上。
「你如果想跑現場,就跟著一之瀨一起去吧。他總是一個人扛下許多事情,而且工作本來就不是分擔處理,而是要合力完成。」
新人困擾地皺起眉頭,這不知道是課長第幾次提議要團隊合作了。他不會拒絕,但總是會像在自言自語似的碎念道:
「……饒了我吧……」
健一搓了搓包裹著喀什米爾名牌西裝的雙臂。
話雖如此,神樂坂課長也覺得不能強迫他照做。如今時代發展快速,更強烈地要求高效率及迅速,因此搜查一課對於證據繁多,轄區也不願處理的複雜殺人案件會以「之後交由專門搜查獵奇殺人事件的部門進行調查」為藉口,把案子丟過來。如此一來,即使案件搜查的時間拉長,也能保住搜查一課的面子。不過,有搜查官為此犧牲是事實,也有不少人對奇特搜專門處理獵奇殺人事件的特性感到厭惡,逃離這個部門。不知不覺間,這裡就被當成逼人主動離職的降職部門,就算有新成員進來也會馬上離職,以至於一直以來都只有從部門設立之初就在的一之瀨朱理跟神樂坂課長待在這裡。
健一也算待很久了,神樂坂課長已經目送過好幾個才調到這裡,沒過幾天就請辭的人離開了。這個新人貫徹不前往淒慘的現場,只處理內務的工作態度,就某方面來說或許才是正確的選擇。
……電話響起,直接接通奇特搜的座機放在健一的辦公桌上。由於液晶螢幕年久失修,顯示出來的數字淡得無法辨識來電號碼。儘管整個警察組織都邁向數位化,但在高層的命令下,這個搜查一課的角落部門仍遵守著「還能用就用」的指示。
「獵奇殺人事件特別搜查課您好!」
精神飽滿地接通電話之後,健一的語氣頓時沉下來,毫不掩飾嫌棄地回應「啊,是一之瀨前輩啊……」。他也沒問對方有什麼事,立刻就按下保留鍵,轉接到神樂坂課長辦公桌上的內線電話。
「喔,一之瀨啊。辛苦了,今天去了哪裡?」
『我為了調查府中的強盜強姦殺人案件,現在在秋留野市的邊界。』
「是那起案子啊。你跑到真遠的地方去呢。狀況如何?」
『我有事要向你報告。』
報告──
既不是告知搜查進度,也不是要商量。
又來了啊。聽出話中含意的神樂坂部長心想,用一聲苦澀的嘆息回應。
『重要嫌疑人死亡了。』
「這樣啊……那這次應該也跟之前一樣,不是你殺的吧?」
『是的,我沒有殺了對方。』
「保險起見,你說明一下狀況吧。」
從電話的另一頭能聽見警車的鳴笛聲越來越靠近,似乎是朱理叫來的支援。重要嫌疑人都在眼前死亡了,他卻不見一絲動搖,冷靜說明狀況的口吻令人不寒而慄。
『裝備的一把手槍以及手銬都沒使用。我請他跟我回局裡時,他就逃走了,我一路追進廢棄工廠內,不得不在適當的使用範疇內舉槍以示警告,但沒有發生肢體接觸,接著他就突然按住胸口,自己倒下去了。死因大概是心臟病發之類的突發性疾病。』
他平淡地用公事公辦的口吻,單純地描述眼前發生的事實。
以非公務員的身分進入警視廳的一之瀨朱理,原本是搜查一課的刑警。負責教育他的人留下的評價是「槍法超群,各方面還算優異,但個人意見略顯不足」,在個性鮮明的強行犯組中,似乎總是被前輩耍得團團轉。令人意外的是,這樣的他在四年前自願調到奇特搜──他說「既然沒有人願意,那由我去吧」──主動加入了。雖然沉默寡言,但神樂坂課長認為他是個正義感比任何人都強的青年。
只有兩個人的奇特搜過了一段平穩的日子。當時的朱理確實沒什麼個人的意見,但在神樂坂課長追根究柢的強硬詢問之下,他才總算會害臊地說起關於自己妻女的事情。面對時不時就看向擺在辦公桌上的全家福,並趁著休息時間一邊打盹一邊準備升遷考試的他,神樂坂課長也感到莞爾。
然而,他在幾個月後遭遇了慘劇。重返工作崗位後,他就變得不太對勁,不但將全家福蓋在桌上,彷彿是被某種附身似的,開始著手調查獵奇案件。
他成為了一名無論面對什麼遺體,都能泰然自若的優秀搜查官,但現在的他只會向身為上司的神樂坂課長「報告」,而且他的報告總是──
『──以上……課長,你有在聽嗎?』
「啊,有。又是心臟啊,但我記得府中的那個嫌犯沒有什麼慢性疾病吧?」
『是啊。』
自從發生那起事件之後,就再也無法從他的話中聽出一絲感情。
神樂坂課長點開電腦桌面上名為「報告書」的資料夾,裡頭存放著一個月前也是相同結果的案件報告,撰寫人員的姓名欄中寫著一之瀨朱理。即使神樂坂課長向法院申請了逮捕令,也還是無法成功逮捕犯人,因為嫌犯就在拿著逮捕令前往逮捕的朱理面前,跟這次一樣突然心臟病發,離奇身亡。
神樂坂課長忍不出發出已經變成習慣的嘆息。
「一之瀨,雖然不能說得太直白……但像這樣一再發生突發狀況的話,我也會被要求進行說明。我不是在懷疑你,但你真的沒有觸碰到嫌犯吧?」
『沒有。』──朱理立刻回答。
「那就好。遺體應該會馬上送去解剖,就算其他人說些閒言閒語,你也別放在心上,把報告交過來之後去調查下一個案件吧。剛才來了一起要交給奇特搜的案件,我看過之後就把資料傳給你。」
『好的。我先掛斷了。』
掛上電話之後,神樂坂課長垂下一雙瞇瞇眼。
「……又鬧出人命了嗎?逮捕令呢?」
「姑且正以違反毒品防制條例為由申請中。」──但很可惜,只能留下遺憾。
「自從我分配到這裡之後,已經是第五個人了耶。一之瀨前輩該不會是其實覺得逮捕之後還要讓對方坦承犯案很麻煩,就不小心把嫌犯殺了吧?」
「不要這樣臆測同一個部門的夥伴。」
「夥伴?這就難說了……他應該不這麼認為吧。」
「一之瀨是個認真的搜查官。」
「那就是認為說謊也是權宜之計的認真警察呢,是最惡劣的那種人。」
健一這麼說完,偷偷連上警察資料庫。他看著朱理的資料。沒有被特別要求寫悔過書,乍看之下也是個經歷極其普通的警察,但更新的大頭貼有著一雙死魚眼,看起來就像罪犯被拍下的入獄照。
「課長也是這麼想的吧?」──健一拉長尾音說。
「什麼?」
「一之瀨前輩的眼神真的很可怕啊,那是殺人犯的目光。他絕對有碰觸到那些嫌犯。如果沒有推倒對方施予外力壓迫,不可能會引發什麼心臟病。」
「佐藤啊……」
聽到新人不停講著一之瀨的壞話,神樂坂課長只能露出曖昧不清的苦笑。
他摸了摸自己的大肚腩,看向朱理的辦公桌。
放在他辦公桌一角的相框依舊蓋著,上頭積著薄薄一層塵埃。健一似乎對蓋上的相框絲毫不感興趣,不過只要看一眼就能了解一之瀨真實的為人。三年多前那個個性低調,一臉幸福地支持著妻女,一之瀨一家的「父親」──
「只是巧合接連發生而已吧。」
「是喔……」
「解剖結果說明了一切。一之瀨真的沒有觸碰到對方。」
「那麼──」
健一的上半身靠上椅背,向後仰去。這個辦公室原本是搜查一課的資料室,他仰頭望著滿是昭和時代留在天花板上的焦油汙漬。
「……反而更毛骨悚然吧。」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純黑的執行者(1)的圖書 |
 |
純黑的執行者1【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青木杏樹 出版社: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8-28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23 |
驚悚恐怖 |
$ 334 |
中文書 |
$ 342 |
驚悚推理 |
$ 342 |
日系驚悚推理/神怪靈異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純黑的執行者(1)
★充滿黑暗的懸疑鉅作!
★冷靜殘酷的刑警X充滿謎團又狡猾的惡魔
★為了復仇,刑警選擇隨著惡魔墜入地獄
隸屬於專門搜查離奇屍體跟獵奇殺人事件的「奇特搜」刑警.一之瀨朱理有個傳聞──只要是他負責的案件,都一定會以「嫌犯死亡」作結。
朱理是三年前發生的虐殺事件中唯一的倖存者。
他在重傷瀕死之際,跟突然現身,自稱惡魔的青年.巴力訂下契約,
以避免自己喪命為代價,獻上犯罪者的性命。
這一切都是為了向殺害家人的犯人復仇──
作者簡介:
青木杏樹Anju Aoki
出生於新潟縣。以《黑妖犬 罪犯側寫師.犬飼秀樹》(台灣角川出版)一作出道。個性鮮明的人物描寫與嶄新的故事結構蔚為話題。在《無名群演》(暫譯)中,敏銳的心理描寫及可讀性受到很高的評價,並獲得北區內田康夫推理小說文學獎的評審特別獎。
譯者簡介:
江宇婷
從書店員到出版社編輯,現為專職譯者。
經手圖文書、實用書、漫畫輕小說及手遊,
願能伴隨文字看遍更多不同的世界。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在平常那條路上的我們
沒有什麼美麗的死亡。
如果有的話,不流出鮮血的死法,或許就是最美麗的。
×
不只是外縣市,實際上東京也到處遍布廢棄工廠。
這棟建築物或許該說是高度經濟成長期的遺物。長期密閉又被燻黑的漆黑空間裡,井然有序地排列著生鏽的鐵製機械。
過去這間工廠應該曾不分晝夜地製造著某種物品。牆壁格外厚實,天花板卻很低,照明設備不多。幾乎所有日光燈都被拆除,或是因為年久劣化而破裂。廢棄的工廠當然早已被斷電,就算打開開關也沒有任何反應,是個讓人覺得喘不過氣又昏暗的地方。
只有陽光透過...
沒有什麼美麗的死亡。
如果有的話,不流出鮮血的死法,或許就是最美麗的。
×
不只是外縣市,實際上東京也到處遍布廢棄工廠。
這棟建築物或許該說是高度經濟成長期的遺物。長期密閉又被燻黑的漆黑空間裡,井然有序地排列著生鏽的鐵製機械。
過去這間工廠應該曾不分晝夜地製造著某種物品。牆壁格外厚實,天花板卻很低,照明設備不多。幾乎所有日光燈都被拆除,或是因為年久劣化而破裂。廢棄的工廠當然早已被斷電,就算打開開關也沒有任何反應,是個讓人覺得喘不過氣又昏暗的地方。
只有陽光透過...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死亡比鄰居更滿不講理。
溫暖的家庭,有位體貼的妻子,以及愛笑的女兒。
生活絕對稱不上富裕,但這種平凡的幸福──我也曾經擁有。
這些幸福隨著溫熱的液體不斷從脖子湧出。即使我拚命按壓,依然從指間一滴滴流下。眼看妻子替我熨燙過的白襯衫逐漸染成鮮紅,女兒在我出門時對我說「路上小心」後遞來的粉紅色條紋手帕,終究無法再吸收湧出的血。
「啪噠」一聲掉落的手帕,絆到拖著的腳背。
──礙事。
我一腳踢開,手帕碰到掉在走廊上的一根粗大釘子。
那正是讓妻子跟女兒慘死的「異物」。
妻子被迫咬著口塞,被折磨到最後一刻,頭...
溫暖的家庭,有位體貼的妻子,以及愛笑的女兒。
生活絕對稱不上富裕,但這種平凡的幸福──我也曾經擁有。
這些幸福隨著溫熱的液體不斷從脖子湧出。即使我拚命按壓,依然從指間一滴滴流下。眼看妻子替我熨燙過的白襯衫逐漸染成鮮紅,女兒在我出門時對我說「路上小心」後遞來的粉紅色條紋手帕,終究無法再吸收湧出的血。
「啪噠」一聲掉落的手帕,絆到拖著的腳背。
──礙事。
我一腳踢開,手帕碰到掉在走廊上的一根粗大釘子。
那正是讓妻子跟女兒慘死的「異物」。
妻子被迫咬著口塞,被折磨到最後一刻,頭...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章
第一章 在平常那條路上的我們
第二章 我是被獨留在這個世界的人
第三章 溫柔的背叛
第四章 墮落的執行者
最終章
後記
第一章 在平常那條路上的我們
第二章 我是被獨留在這個世界的人
第三章 溫柔的背叛
第四章 墮落的執行者
最終章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