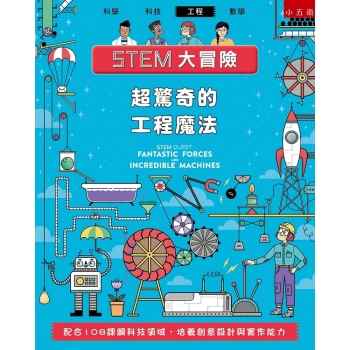南歸,北迴,高地,異鄉,
一趟趟往復,交織成一場歷練,人在其中成長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這時代的迴游者
2022年書展大獎得主陳德政
第一本後青春散文集
詹偉雄、李取中、鄭宗龍 聯袂推薦
「停止移動,就停止了追尋。我在變動中安身立命。」――陳德政
一趟趟往復,交織成一場歷練,人在其中成長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這時代的迴游者
2022年書展大獎得主陳德政
第一本後青春散文集
詹偉雄、李取中、鄭宗龍 聯袂推薦
「停止移動,就停止了追尋。我在變動中安身立命。」――陳德政
不同於魚類洄游至出生地延續生命,城市人在不同地域間往復來回,每個落腳處都可以是家。受每個地域的環境、文化所滋養,最終成長為自己想要的樣子。「選擇性迴游」是這時代的一種生命樣貌。不是無奈地漂流,是承擔,縱有孤單也是歷練的過程。
四十歲世代的陳德政,以四十篇散文凝視不同迴游時空中的自己,記述影響他的人、文化、土地與身體行動。影響他最深的爺爺、作不完的考試夢、南國當兵記事、職棒三十年心情、瘟疫年代的寫作生活、新新人類的寓言、來自「地下」的樂團、永遠的張雨生、行走台灣百岳的身心歷程、異國文化的遙望與回想……這本書既是他的成長歷程,也是這世代共同記憶的縮影。
你四十好幾又活在台灣,那就別管普魯斯特了,這本書才是你我的《追憶似水年華》!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
歌手說萬物皆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契機。詩人說有時我寫出一個字,便注目凝視著它的輪廓,直到它發出光芒。於是作者用一字一句所發出的光芒,照進時空的裂縫中,再一次地好好的告別了那些曾經存在的人、事、物。——李取中.《大誌雜誌》、《編集者》總編輯
德政談自己,他的文字像一雙透亮的眼睛,領我濳入時代的共感記憶、拉著我攀登抒情高山,他細膩、紳士,折射一幕幕人與土地的美麗風景。——鄭宗龍.雲門舞集藝術總監
【南歸】
我在各方面都受他的影響很深,如家中的東西要收拾整齊,對未來保持著一種樂觀,喜歡到處趴趴走,而且每天寫日記。我遺傳到爺爺鼻子的形狀,身體裡流著他的血。爺爺以身作則,總讓我覺得當一個讀書人,一個寫文章的人,是值得驕傲的。――〈爺爺〉
【北迴】
上車後我總是沉沉睡去,心情在車程中默默轉換,準備從一種狀態跳躍到另一種狀態。從都會到鄉村,綠色的田取代了灰色的樓,掠過的風景不再是風景,更像換場的布幕。醒來後倏然回到孕生我的城,這裡有不同的語言習慣、飲食胃口,有不同的天空與雲。
我彷彿又變回當時的少年,重拾他走路的姿態,記起他心裡想過的事情。直到打開家門,看見逐漸老去的父母,才明白在他們眼中,我沒有幻滅的夢。我不知道其他人經過台北車站時想起了什麼,我會望見車站的另一頭,是家。――〈台北車站〉
【高地】
爬山的過程那麼辛苦,是什麼原因讓人一直走下去?對我來說,一次次山行讓我更理解自己,確認並且接納了自己是個內向的人,電話、電鈴和電梯,這些讓我緊張的事物山上都沒有。
內向的人往山裡去。――〈一個人的山〉
【異鄉】
關店前的週末,Other Music號召了一場遊行,有些客人吹著小喇叭,有人敲著手鼓,店員高舉店旗,一群愛音樂的人歡歡喜喜踩過東村的街,替摯愛的店送行。那是我深深想念的城市……
影片一幕推過一幕,我和酒神像兩個時間裡的偵探,巡邏在記憶的街頭,櫥窗裡的動態、人物的表情、門牌的號碼,都是我們採集的證明。也許我們更想採回的是從前的交情,那年夏天的自由自在。――〈世界就是中古唱片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