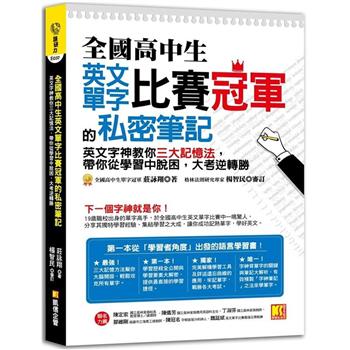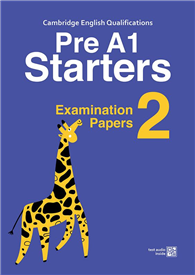曾經的棒球選手,今日的小說寫作者
走出牛棚的陳尚季
刻畫與棒球交會的生命故事,記下比輸贏更重要的事
走出牛棚的陳尚季
刻畫與棒球交會的生命故事,記下比輸贏更重要的事
這八篇短篇小說描述八個與棒球有關的故事,但主場景通常不是球場,主角也多不是球員。棒球就像時間,有可能讓人失去能力,失去家人,失去榮耀,失去健康……,然而,這些曾因棒球而熾熱過的心,就算黯淡如灰燼,也依然有著燙手的溫度。
〈斷棒〉
「阿公,我從以前就想問你啊,你幹嘛要撿斷掉的棒子回來? 又不能拿來打球,你真的是拿來做木工喔?」
「那些不能丟,有些東西斷掉了還是很重要,不能丟。」
〈再見阿嘉〉
阿嘉的右手不斷敲打車窗和前置物箱,我看見他手指上的肉色缺口,像座沒有生命的山坡。
〈最好的投手丘〉
父親憤怒的眼神和傷人的話語,讓他感覺自己的心裡什麼都沒有了。難道哥哥的比賽和雪芙蘭都比他還重要嗎?
〈白頭鷹〉
大家只會看見吉祥物的可愛動作,不會看見真正的他。而且重新踏進棒球場,也許是他可以懲罰自己的方式,他這樣想。
〈等待幻影〉
只要看到你們打棒球,我就知道我沒有把她忘了。對我來說,痛苦和快樂,它們有時候是同一種東西。
〈和平時光〉
拿耀發現這段時間他已經習慣等待,等待月亮被雲遮住,等待船靠岸,等待戰爭結束;只有活下來才能再打野球。
〈被藍眼睛捕捉的事〉
哈伯通過檢查後去廁所照鏡子,幾乎要開始相信那隻眼睛真的是身體長回來的。
〈最後的太陽〉
我想到工廠裡剩下的那五只尚未完成的太陽牌手套,意識到我或許要變成這世界上最後一個做太陽牌手套的人了。
這些故事,觸及臺灣的職棒、教練的內心、球員的掙扎、吉祥物的獨特性,以及臺灣手套工業的沒落等等;故事裡的人都已離開球場,他們的身影像一顆指叉球,忽然消失在視線所及之處。這些事物即將消失或者已經離去,作者透過書寫,將教練、球探,以及站在背光處的球員們帶回他們曾奉獻青春的地方,並紀念球場上的前輩們,希望在作品裡與他們相遇。
共同推薦
吳明益(作家、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專文推薦
許又方(楊牧文學研究中心主任)
曾文誠(資深球評)
林言熹(球魂網站副站長)
陳德政(作家)
黃崇凱(小說家)
黃暐婷(小說家)
楊富閔(小說家)
黃俊隆(自轉星球文化社長、投手)
林聖修(啟明出版發行人)
.隨著一篇一篇作品的開展,可以看出棒球「賽」並不是尚季的重點,他更關注的是藉由棒球這種許多臺灣人關注的運動,去思考他的生命議題……他的作品裡不只有棒球,還有「斯塔德」丈量的「生命場域」,以及山風海雨和記憶的共同駐留。――吳明益
.我始終相信,一直寫下去,那逐漸被遺忘的人事物會在某個魔幻時刻裡,重新再出現一次;而比賽,還沒結束。――陳尚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