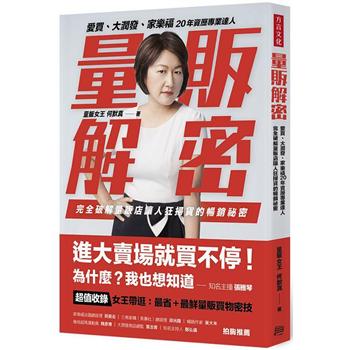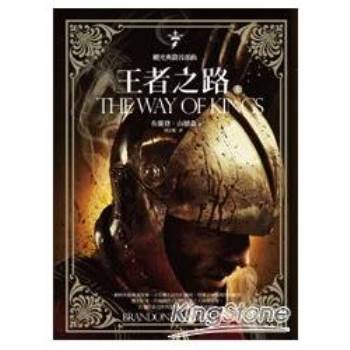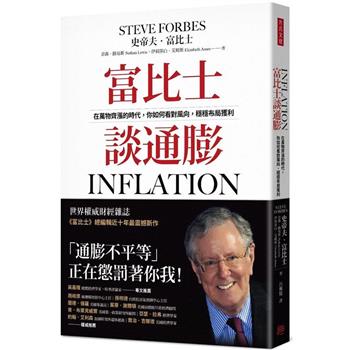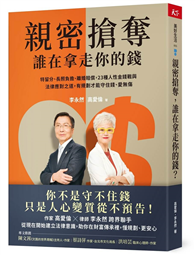我媽姓謝,名若君:南洋咖哩雞
文/蔡明亮
每次回古晉老家,跟親友聊到我媽,大家總是讚嘆她的廚藝。小時候幫我洗澡、餵我吃飯的鄰居大姊姊大珠,現在也快八十歲了,她說:「你們家有很多做點心的傢俬,都是你媽買的,你看她那麼節省,倒是很捨得在這上頭花錢。」
這使我想起,從前過年時,媽媽帶著一家大小在客廳烘焙雞蛋糕的情景。有時大珠也在場幫忙,一個洗衣服用的大鐵桶,裝了調開的蛋麵糊,用一個木製把手彈簧狀的鐵器撥打麵糊。因為不能間斷,所以大人小孩輪番上陣,至到麵糊打發為止,再把麵糊勺進鐵鑄的模具,蓋緊,用碳火烘烤,不久,一顆顆像花朵大小的雞蛋糕就烘好了,香氣四溢。
我媽姓謝,名若君,我爸喚她阿君,朋友也喚她阿君。
我外公叫謝錦勝,廣州人,在他那個苦難的年代,跟著移民潮去到香港,那時只有十三歲的他,就在街邊學賣麵。因為個子小,就站在小板凳上煮麵。後來,又乘船移向南洋,在婆羅洲一個叫砂拉卓的河口小鎮落腳,開了麵檔,娶了我外婆;外婆叫楊麗華,生了我媽,我媽三歲時她又生了我舅,我舅還沒滿月,外婆就瘋了,聽說被人下了降頭,每到半夜就會燒著香上街又哭又拜,要外公去把她尋回來。有一天,竟然往我媽的嘴裡塞竈頭下的灰燼,幸好被外公發現。不久,外婆就過世了,外公頓時感覺房子裡陰氣森森,一時發慌,抱起小嬰兒,拉著女兒,連夜搭船,順著河逃往古晉。後來就有人說,古晉有名的街邊美食哥羅麵(乾撈的諧音)就是外公第一個帶進來的。
這是我媽講給我聽的故事,她就是那個差點被自己母親餵灰燼噎死的小女孩,長大後非常好吃。我媽小學沒念完就開始跟著外公賣麵,切蔥、切辣椒、炸蒜頭豬油、包餛飩,這些準備工夫都是她白天的活,晚上還要到麵檔幫忙端盤洗碗;外公給她搭公車到麵檔的錢她從來不用,提前出門,用走的,省下來的錢都是買吃的,吃到好吃的,就學著自己做。「這樣省很多錢。」她說。我的記憶裡,小時候廚房的廚櫃,總是藏著媽媽做的糕點,有一次被我發現了用白紙包著的,一條深褐色條狀的東西,其貌不揚,偷偷切下一小片往嘴裡送,那味道卻好極了,那是媽媽做的榴槤糕,比起外面買的不知好吃多少倍,忍不住又多偷吃了幾口。
我爸是我外公的徒弟,也是賣麵的,我媽嫁後的生活,起初也沒什麼改變,開檔前爸爸要擀麵,其他的備料都是媽媽做,晚上照樣要到麵檔去幫忙。後來爸爸存了一筆錢,在鄉下買了一塊地,種胡椒、養鷄生蛋,開起了農場,一邊還在賣麵,但媽媽就不跟去麵檔了,原本要備料的活也請了工人幫忙,她只負責包餛飩,分出了大部分的精力照顧孩子跟農事。媽媽既勤快又手腳俐落,養雞養鴨還養鵝,也種香蕉、玉米、紅毛丹、人參果……不久,農地就長出像牛角般大的香蕉,熟黃的牛角蕉可蒸也可裹麵粉炸,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她也會去挖野生的木薯,搗爛加椰奶,蒸成香香QQ的木薯糕。我爸是客家人,喜歡吃擂茶,煮擂茶要用到許多野菜,媽媽就鑽進野地裡去找,也總是讓她找到,她煮出來的擂茶比客家人還道地。
這段期間,我們家簡直像美食天堂,一有空,媽媽就做吃的,各種糕點輪番出爐:九層糕、白糖糕、馬蹄糕、煎堆;還有從阿嬤那學來的客家菜粄,要不就是各種甜湯:紅豆湯、綠豆爽、椰漿黑米、摩摩喳喳……沒有她不會做的,每一樣都很好吃。我爸晚上收檔回家有一習慣,喜歡吃炒花生配黑狗啤(健力士),媽媽時不時就要炒花生裝在美祿罐裡,那罐花生也是我們小孩平時的零食。
我家飯桌上的菜也很有特色,爸爸喜歡吃鹹魚,媽媽就用鹹魚燜豆腐,用鹹魚炒三層肉,非常下飯。有一道用鹹魚做的菜,我猜是媽媽發明的,因為賣麵要用到豬油,所以媽媽平日就要炸豬油,炸剩下的豬油渣,她就會把大蒜、梅香鹹魚和豬油渣,按比例一起剁碎混合,再放入鍋裡去炒,利用豬油渣的油脂,炒出一道色澤金黃的醬料,我們用它配飯拌粥,非常甘香可口,媽媽知道我最愛這味菜,她生前只要我回家,就專程為我炸豬油,取其渣做這道鹹魚豬油渣,甚至裝到玻璃罐裡,讓我打包出國。
咖哩雞也是她的拿手菜,常煮。煮咖哩的馬鈴薯要先炸過,才不會一下子就化掉;她說爆香薑碎蒜末,轉小火炒咖哩粉,這樣咖哩才不會苦。從她告訴我這些煮菜的邏輯看來,我媽媽是絕頂聰明又有天分的。她的咖哩跟別人不同,她加了很多蔬菜,蔬菜要選那些耐煮的,又不會太搶味的,比如玉米筍、長豆、茄子,煮出來的咖哩雞別有一番風味。還有一般的咖哩會辣,我家的咖哩不辣,因為媽媽知道我從小就不會吃辣,所以我家的菜從不放辣椒。
我們家有七個小孩,我排行老三,弟弟出世後家裡忙不過來,把三歲的我送去外公家,到我十二歲才回到媽媽身邊。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媽媽特別向著我,偏心我,有什麼好吃的,她總是把最好的一份留給我。我曾經有一段時期很愛吃雞肝,每當家裡有殺雞,她總是把蒸熟的雞肝整顆拿給我吃;還有一次很深的印象,她種了一片玉米田,收成的時候,才發現每株玉米都長得不太好,大部分的玉米粒都是稀稀落落的,一大鍋玉米煮熟後,就看媽媽在鍋裡東挑西找,挑出一根最多玉米粒的就遞給了我。後來,我每次在國外,坐火車經過鄉村,看到玉米田,我總會一直望著,我想起媽媽,想起她的玉米田。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文學.老屋.好料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4 |
中文書 |
$ 284 |
飲食文學 |
$ 284 |
飲食文學 |
$ 324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2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文學.老屋.好料理
從川端町的紀州庵到文學森林
是料理記憶,也是文學滋味
17位散文名家 × 念想的家常菜
談飲食、說軼事、念故人
把文學放進烹飪中,把念想的料理化作動心的文字
作家下廚烹調,也是一種創作,用鍋鏟揮灑出生活的藝術。
\\黃金陣容作家群 獨門料理幸福上桌//
●周夢蝶最愛的牛肉麵,出自哪位軍人作家的手藝?
●正統川菜其實不辣?!馬世芳透過作家莊祖宜,取得川菜妙方?
●林立青的職人料理「剝皮辣椒雞湯」,在不同工地特色就會改變?
●遍嚐義、荷、西、葡蛤蜊鮮魚的韓良憶,如何以獨步手法改良這道料理?
●以鹽漬、曝曬等方式保鮮的客家菜,有什麼特殊發展軌跡?
更多精彩內容:洪愛珠從蘆洲、南門市場找到冬瓜,復刻外婆冬瓜肉的美好滋味;瞿欣怡傳承母親的家常菜;為緩解職業婦女壓力,方梓變出「電鍋菜」……
「在紀州庵,品嚐的不只是美食,而是,每一次夾菜、每一口咀嚼,都像是在品味多彩繽紛的人生,感受世間誠悃動人的情誼。」──封德屏(紀州庵文學森林館長、《文訊》總編輯)
.作家說菜也下廚,帶你品嚐食物承載的時光故事
文友聚會,催生出周公讚不絕口的「張家牛肉麵」。作家廖玉蕙的芋香牛肉末,膾炙人口,是她開啟寫作之路的重要料理。馬世芳的川味椒麻雞,由作家莊祖宜提供醬汁祕方,經歷了什麼轉變,成為「思念的遠方滋味」……
文人說飲食,要好吃,也要有好故事,有人寫廚房傳技,有人寫親情回憶,更多寫出生活的痕跡。作家們用文字為家常飲食添上文學魅力,每個作家端上的,是私房菜,也是一篇篇文學作品。
.百年老屋復刻作家料理
紀州庵初建於1917年,位於川端町,原為平松家族經營的日式料亭,平松家族以故鄉「紀州」(きしゅう)命名。後續興建離屋、別館與日式庭園。二戰後轉為公務人員眷舍,小說家王文興曾居於此。
2004年,紀州庵被指定為市定古蹟。2011年,紀州庵文學森林新館落成,成為文學展演與推廣的重要基地。設有文創書店、演講空間及「風格茶館」,提供由文學名家設計的特色料理,巧妙融合文學與餐飲,再現百年前日式料理屋的風采。
作者簡介:
編者 封德屏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曾任雜誌、出版社編輯,並曾參與籌畫《夏潮》雜誌,1976年與友人合辦東明出版社。1984年進入《文訊》迄今,歷任主編、副總編輯,現任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董事長、紀州庵文學森林館長。長期主編《文訊》雜誌,並多次主持《台灣文學年鑑》、《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等工具書,以及《張秀亞全集》、「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等編纂計畫。著有散文集《美麗的負荷》、《荊棘裡的亮光──文訊編輯檯的故事》、《我們種字,你收書──《文訊》編輯檯的故事2》。曾獲金鼎獎最佳編輯獎、金鼎獎特別貢獻獎、台北文化獎等。
繪者 微枝
左手嚕貓,右手畫圖;畫圖不喜歡打草稿,胸懷小志且理直氣壯。在創作的路上老是東張西望、龜速前進,執著於雞毛蒜皮的小事、喜歡用費工的方式生產,揣著一點天真,繼續走向下一個故事裡。
章節試閱
我媽姓謝,名若君:南洋咖哩雞
文/蔡明亮
每次回古晉老家,跟親友聊到我媽,大家總是讚嘆她的廚藝。小時候幫我洗澡、餵我吃飯的鄰居大姊姊大珠,現在也快八十歲了,她說:「你們家有很多做點心的傢俬,都是你媽買的,你看她那麼節省,倒是很捨得在這上頭花錢。」
這使我想起,從前過年時,媽媽帶著一家大小在客廳烘焙雞蛋糕的情景。有時大珠也在場幫忙,一個洗衣服用的大鐵桶,裝了調開的蛋麵糊,用一個木製把手彈簧狀的鐵器撥打麵糊。因為不能間斷,所以大人小孩輪番上陣,至到麵糊打發為止,再把麵糊勺進鐵鑄的模具,蓋緊,用碳...
文/蔡明亮
每次回古晉老家,跟親友聊到我媽,大家總是讚嘆她的廚藝。小時候幫我洗澡、餵我吃飯的鄰居大姊姊大珠,現在也快八十歲了,她說:「你們家有很多做點心的傢俬,都是你媽買的,你看她那麼節省,倒是很捨得在這上頭花錢。」
這使我想起,從前過年時,媽媽帶著一家大小在客廳烘焙雞蛋糕的情景。有時大珠也在場幫忙,一個洗衣服用的大鐵桶,裝了調開的蛋麵糊,用一個木製把手彈簧狀的鐵器撥打麵糊。因為不能間斷,所以大人小孩輪番上陣,至到麵糊打發為止,再把麵糊勺進鐵鑄的模具,蓋緊,用碳...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主編序:美食美文,相互輝映◎封德屏
周夢蝶指定料理:張拓蕪牛肉麵 樸月
思念,從這道說起:蛤蜊獅子頭 古月
魔幻料理:紅麴燒肉 方梓
味蕾是一座神祕的城:我和仙草雞 羅思容
被客家茶文化昇華的美食:客家粄圓與東方美人茶 吳德亮
過年才上桌的好滋味:蘇式熏魚 朱全斌
簡單美味的幸福:蹄花麵線、芋香牛肉末 廖玉蕙
旅行的味道:歐式番茄蛤蜊烤魚 韓良憶
小說家的私房料理:玻璃肉麻油麵線與莎梨酸菜鴨 凌煙
人生味,辣中帶甜:剝皮辣椒雞湯 林立青
想念遠方的滋味:川式椒麻雞 馬世芳
紀念李永平:胡椒豬肚湯...
周夢蝶指定料理:張拓蕪牛肉麵 樸月
思念,從這道說起:蛤蜊獅子頭 古月
魔幻料理:紅麴燒肉 方梓
味蕾是一座神祕的城:我和仙草雞 羅思容
被客家茶文化昇華的美食:客家粄圓與東方美人茶 吳德亮
過年才上桌的好滋味:蘇式熏魚 朱全斌
簡單美味的幸福:蹄花麵線、芋香牛肉末 廖玉蕙
旅行的味道:歐式番茄蛤蜊烤魚 韓良憶
小說家的私房料理:玻璃肉麻油麵線與莎梨酸菜鴨 凌煙
人生味,辣中帶甜:剝皮辣椒雞湯 林立青
想念遠方的滋味:川式椒麻雞 馬世芳
紀念李永平:胡椒豬肚湯...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