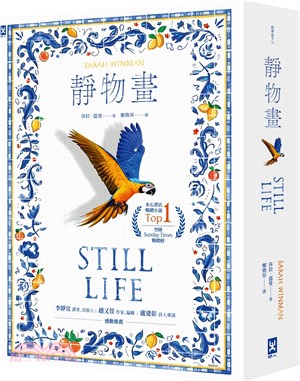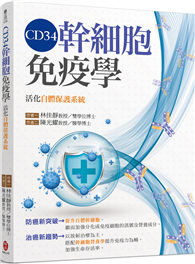生命帶來的傷口,
終會在時光流轉之中慢慢癒合
終會在時光流轉之中慢慢癒合
★ 英國水石書店選書、暢銷小說Top 1
★《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小說Top 10
★《衛報》年度好書
★《早安美國》讀書俱樂部選書
★ BBC「Between the Covers」讀書俱樂部選書
★ 澳洲最大連鎖書店DYMOCKS年度選書
★《Parade》雜誌年度好書、《娛樂週刊》必讀精選
★ 榮獲InWords 文學獎(TILA)
★ 榮獲「書本就是我的名牌包」年度讀者最愛小說(The Books Are My Bag Readers)
★ 入圍獨立圖書獎小說獎(Indie Book Awards)
★ 英國銷售突破10萬冊,亞馬遜讀者突破3萬評論,4.4星高分好評!
★ 授權英、美、匈、荷、義、西6國語文
「我們只需要知道人心的本事有多大,艾芙琳。」
「那你現在知道了嗎?」
「知道,恩寵與怒火。」
1944年,在義大利托斯卡納,二十四歲的英國士兵尤里西斯遇見了年逾花甲的艾芙琳,陌生的兩人在被炸毀的酒窖裡救下一幅藝術瑰寶,也共度了一個悠閒而難忘的午後。
尤里西斯曾是手工地球儀的學徒,艾芙琳則是藝術歷史學家,要她說是間諜也不無可能。艾芙琳來義大利的目的是拯救可能被戰爭摧毀的畫作,也重溫她與英國小說家E.M.佛斯特相遇的回憶,在那次旅程中,她還愛上了某個人以及城裡的風景。
兩個很不一樣的人就這樣在彼此身上找到契合的靈魂,艾芙琳對生活和美的見解在尤里西斯的心裡種下一顆種子,隨後將長成他往後四十年的生命途徑,也為他的人生帶來意想不到的改變……
被戰爭延遲的奧運、失蹤的美國士兵、費里尼的電影、佛羅倫斯大水災……
透過藝術、愛和災禍,兩個深刻的靈魂在此交會,也一再錯身而過,
他們的人生是注定心碎,或者終能迎來幸福?
本書特色
◇封面由英國HarperCollins藝術副總監操刀設計,融會佛羅倫斯風情與特色元素
◇扉頁特別收錄:佛羅倫斯老地圖&手繪地球儀設計草圖,親近古城街巷與匠人風采
感動推薦
李靜宜 | 譯者、出版人
趙又萱 | 作家、編輯
盧建彰 | 詩人導演
各界好評
「莎拉.溫曼故事中那股純粹的喜悅極具感染力。我很享受在非凡的時代和地點與這些令人難忘的人物一起度過時光。」──英國知名主持人 葛雷漢.諾頓Graham Norton
「溫曼的書中充滿了喧鬧、生機勃勃的生活感……這部小說充滿活力、魅力和寬廣的心靈。」──《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精巧別緻……沒有足夠的最高級來形容這本小說的規模和美麗。」──《星期日獨立報》Sunday Independent
「一句接一句,一字連一字,《靜物畫》就這樣成為詩。」──《紐約時報》書評
「旅行癖的補品和孤獨的良藥。這是一本罕見的、充滿深情的小說,讓人對這趟閱讀之旅感激不已。」──《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美好……甜美又機智。」──《泰晤士報》The Times
「充滿了難忘的人物和令人沉浸的氛圍,這是一首對愛、藝術和詩歌的歡樂夏日頌歌。」──Hephzibah Anderson,《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
「在《靜物畫》中,溫曼成為希望的偉大敘述者。」──Helen Cullen,《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
「一個關於善良的心和同胞精神,美好而慷慨的故事……帶來希望與快樂、充滿人性的小說。」──《每日鏡報》Daily Mirror
「內容豐富、感人至深、充滿希望。莎拉.溫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故事家之一。」──Joanna Cannon,《鄰居家的上帝》(The Trouble with Goats and Sheep)作者
「讀者會希望盡可能長久地享受莎拉.溫曼這本美麗小說帶來的樂趣。」──Donal Ryan,《A Low and Quiet Sea》作者
「體現了人類精神的全部慷慨。」──Rachel Joyce,《一個人的朝聖》(The Unlikely Pilgrimage of Harold Fry)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