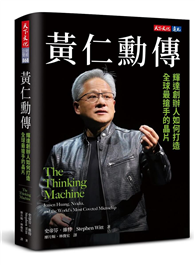在海南雞飯與花園城市之外
深入瞭解這個特殊威權體制的綿密手法
以及推動改變的不懈努力
在許多人心中,新加坡是理想的模範國度:那裡有高度發展的經濟、乾淨美麗的城市景觀、嚴刑峻法下的良好秩序。執政黨在國會擁有九成席次的新加坡政府,也樂於宣傳這幅人民在執政者領導下安居樂業的圖像──而且他們有選舉,非常民主。
本書作者韓俐穎從小也是這樣相信的,直到她開始幫忙上街採訪。她逐漸碰觸到新加坡政府權力設下的種種關卡與阻礙,不能隨意上街抗議表達訴求只是其中一種。若是執意發聲談論某些事情,政府有許多方式磨耗你的身心和經濟,像是伸縮自如的「藐視法庭」指控。
透過採訪接觸或親身參與的各種經驗,韓俐穎想在書中呈現的並不是關於新加坡的唯一真相,而是更為細膩複雜的新加坡面貌。她的描述讓我們極為具體地看到威權體制的羅網如何有效進行管控,也讓我們看到頑強的公民如何想方設法尋找能夠施力的空間。在新加坡推動轉型正義的民間工作,以及推動同志權益的粉紅點活動,都是重要的例子。這些努力,也持續為當地的政治社會環境種下希望。
推薦序──
吳易叡|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程副教授
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共同推薦──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
黃克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劉致昕|《真相製造》作者
蔡秀敏|歷史學者
鄧筑媛|彩虹平權大平臺執行長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
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作者簡介:
韓俐穎Kirsten Han
新加坡獨立記者及公民運動者。二○二二年起擔任《湄公河評論》(Mekong Review)季刊主編,這是一本專注於亞洲的文學雜誌。她經營《我們公民》(We, The Citizens)和《改變現狀》(Altering States)兩份新聞通訊,撰寫關於新加坡政治、人權、公民社會和毒品政策的文章。她的文字曾刊登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外交政策》等多家媒體。二○一八年獲得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協會的傑出法治新聞獎提名,二○一九年獲得人權新聞獎。韓俐穎也是變革正義公社(Transformative Justice Collective)的成員,致力於廢除死刑和終結新加坡的反毒戰爭。她是三隻貓的媽媽,擁有五到十五個K-pop絨毛玩具。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臺灣版序:無論你在何方
二○二四年五月一個星期五的夜晚,我們臺北之旅的一個月行程接近尾聲,我和先生從臺北車站附近的旅館走到立法院周遭的街道。我們非常關注國民黨與臺灣民眾黨如何強行推動一項爭議性的法案;身為大半生在威權環境中工作的記者,來到一個民主國家渡假,一場自由進行的政治示威抗議讓人再興奮不過。離開臺灣之前,我們一定要再次造訪。
現場已經聚集了數千人,有些坐在人行道,有些坐在馬路上,有些在宣傳車之間遊走,聆聽不同人士的演講。資深運動者辛苦打理乏味無趣的後勤工作;熱情的高中生嚮往十年前自己還太年輕無緣參加的太陽花學運;上班族工作一整天之後結伴前來關心最新進度。我看到手牽手的情侶,帶著小娃娃的家庭,跟著夫妻前來的活潑狗兒成了示威者的寵兒。人們揮舞著自製的海報、事先印製的標語。口號聲、音樂聲與笑聲此起彼落,當然也少不了謎因與雙關語。政治人物踐踏正當程序讓人們感到憤怒、挫折,但整體的氣氛相當放鬆。我看到的警察大多忙著指揮交通,保護人們不被汽車與摩托車撞到。
如果政治人物能循規蹈矩、民主程序能運作順暢、民眾不需要上街抗議,當然都是好事一樁;然而我發現像臺北街頭這樣的大規模行動,有一種不可思議、撼動人心的力量,顯示了在必要的時候,人們會攜手同心,表明立場。我知道對於議題各個方面的細節,大家必然會有許多歧見;但是這樣的集會展現了共同的希望與願景──人們期待生活的社會,期盼看到的國家。
在新加坡,人們對於自己期盼看到的國家也有共同的夢想,並且竭盡所能朝著這個目標努力。臺灣運動者與組織者使用的許多策略與方法,新加坡同儕不是望洋興嘆,就是嚴重受限。示威抗議實質上遭到禁絕,因為《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會懲罰任何未經警方許可、「涉及宣傳理念」的公開集會或遊行──就連一個人進行也不容許。示威抗議想要通過警方這一關,必須在十四個工作天之前上政府網站申請。運動者知道要取得許可難上加難,這意謂我們只能將活動局限在演說者角落(Speakers’ Corner)──全新加坡唯一能夠舉行未經警方許可集會或示威的一座小公園;或者尋找其他方式來組織線上或線下的行動。其他選項也處處都是挑戰:劇場演出必須獲得資訊、通訊及媒體發展管理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核准,公開展覽也必須申請許可,外籍人士未經批准不得在公眾活動上發言。新加坡對於種族與宗教議題有各種法規,不僅用來對付種族歧視者,也用來壓制聲討種族歧視的少數族群。這樣還不足夠,人民行動黨政府以懲治藐視法庭及「假新聞」為由,透過立法擴張權力;執政黨高階成員則是以代價高昂的誹謗訴訟來打擊批評者與政治對手。我與臺灣公民社會的朋友討論時,他們大感驚訝:新加坡運動者如果想在凡事須經政府核准的狹隘空間做一點事,過程會有如行經地雷遍布的戰場。但是我們仍然利用自身的資源盡力而為,試圖開闢未來可以運作的空間。
這樣的工作相當困難,風險居高不下,有時也相當寂寞。運動者的故事──尤其是不遵守政府規定的「壞運動者」──在新加坡被邊緣化,主流媒體受官方掌控、因此被人民行動黨的敘事宰制,很少出現非官方許可的聲音與觀點。我和同儕有時會感覺,我們所身處的國家與這個政府向世界投射出來的新加坡,是兩個相互平行的次元。我們看到政府不希望人民看到的事情,發出政府不希望人民聽到的聲音,經歷其他新加坡人可能永遠不會經歷的遭遇──例如警方調查、檢察官起訴、法院訴訟、抹黑汙蔑。正如同在野黨國會議員會組成影子內閣、提出影子報告,呈現政府立場之外的選項;新加坡公民社會掌握的真相,也一樣給新加坡亮麗的公關形象帶來必要的平衡。
我寫作本書是為了點亮燈光,讓各種不同的敘事能夠走出陰影,獲取它們應有的地位,呈現更為細緻、複雜的新加坡面貌。我無法自居為新加坡全體公民社會的代言人──如果我這麼做,請不要相信我;但是我可以分享我如何體驗、觀察、思考自己的國家,一個既讓我怒火中燒、也讓我同等著迷的地方。
我嘗試讓局外人也可以理解本書內容,但寫作時念茲在茲的還是我的新加坡同胞。我們有好多事情必須告訴彼此,好多事情必須為後世留下紀錄,但是能夠這麼做的平臺與管道十分有限──儘管有社群媒體與其善變的演算法。我對這本書最大的期待,就是要讓不接受權力體制敘事的新加坡人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同時也對不受制於人民行動黨規則的公共論述有所貢獻。如今,隨著《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中文版問世,我也開始思考這本書對於新加坡之外的人有何價值。
我經常被指責對自己的國家「說壞話」,被視為一種背叛,但是我不以為然,從來不相信只因為我是新加坡人,就有職責為自己的國家洗白。新加坡的缺陷或許丟人現眼,但面對與批判這些缺陷絕非「背叛」國家。我們身為國民,擔負責任的對象是其他國民,不是國家權力或者宰制性的政治敘事。我之所以書寫新加坡的缺陷,是因為我們能夠、也必須做得更好。為了做得更好,我們首先應該瞭解、並且能夠討論國家的問題。當我的作品跨越國界,那是在向外接觸,希望能夠建立覺察、營造團結,連結其他地方打造更美好世界的努力。
今日的情勢相當艱難:有太多國家的民主品質每況愈下,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造成分裂與壓力,氣候危機威脅全體人類。在這個彷彿世界陷入火海的時代,人們很容易灰心沮喪,覺得無法做出正向的改變。我非常熟悉這種憤怒與悲傷,但正因如此,我也知道共鳴與連結的力量。在這世上,我會遭遇可怕的事,也會看到人們竭盡全力嘗試解決問題,或者至少改善狀況。他們的熱情與決心、同情與關懷、勇氣與堅持為我帶來激勵與動力。當我們看到彼此在崗位上全力以赴,我們會一起變得更加勇敢、堅強。如果你明白自己其實並不孤單,就不會覺得事情沒有希望。
美國黑人女性主義者、民權運動領袖芬妮.露.哈默(Fannie Lou Hamer)曾經宣示:「沒有人能夠真正自由,除非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這番話深得我心,儘管我有時候心情跌落谷底,因為自己顯然無力讓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在這樣的時刻我會提醒自己,公正的世界不可能由一個人打造,窮盡一生之力也不可能。那會是一場持續開展的使命,我們必須日復一日付諸實行,每一個世代都在前一個世代的基礎上繼續努力。那也是一場超越國界的使命,因為我們關愛與照顧彼此、眾生、地球的能耐,要比任何政治人物與國家政府的權力更為古老、強大,本身就是自成一格的力量。
無論你在何方,你也擁有這股力量。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臺灣版序:無論你在何方
二○二四年五月一個星期五的夜晚,我們臺北之旅的一個月行程接近尾聲,我和先生從臺北車站附近的旅館走到立法院周遭的街道。我們非常關注國民黨與臺灣民眾黨如何強行推動一項爭議性的法案;身為大半生在威權環境中工作的記者,來到一個民主國家渡假,一場自由進行的政治示威抗議讓人再興奮不過。離開臺灣之前,我們一定要再次造訪。
現場已經聚集了數千人,有些坐在人行道,有些坐在馬路上,有些在宣傳車之間遊走,聆聽不同人士的演講。資深運動者辛苦打理乏味無趣的後勤工作;熱情的高...
章節試閱
序論:認識一個國家的權利【節錄】
「我不認識韓女士描述的國家。」
二○一八年新加坡駐美國大使米爾普里(Ashok Kumar Mirpuri)投書《紐約時報》,反駁我先前發表在該報的一篇文章,上述那句話是他的結論。我的文章描述新加坡與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如何在死刑議題上一搭一唱,並且有志一同將「假新聞」的相關論述化為武器。
米爾普里大使寫道:「韓俐穎的文章將新加坡描繪為一個威權主義的樂園,對政府的批評會遭到扼殺,毒品走私者則一律絞刑處死。」他聲稱我的說法背離事實,在新加坡「我們熱烈辯論各項議題,線上與線下都是如此。」
大使做了諸多反駁,其中以結論最讓我印象深刻。我猜想,新加坡政府既然如此保護自身的國際形象,大使自然必須配合發表這樣的言論。然而大使閣下也有可能是真心誠意,也許正如他所述,他認識的新加坡與我截然不同。
你我所見略同嗎?
每逢一年一度的新加坡國慶日,我們都會高歌「一個國家、齊心的人民、一個新加坡」,然而過去十三年來(還沒結束)我愈是深入探索、研究、報導與寫作新加坡,我愈能夠發現──而且持續發現──新加坡是多面的:富人的新加坡、窮人的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客工(移工)的新加坡、華人的新加坡、少數種族的新加坡、掌權者的新加坡、異議者的新加坡。這些新加坡層層相疊,營造出各種經驗的集合與子集合,既相互交會又彼此分歧。
儘管人生與政治從來不是一清二楚,但人們往往習慣於二元思考,標舉競爭性的自由民主作為「自由」的模範,將威權主義想像為高壓極權的警察國家。新加坡讓這樣的二元想像陷入錯亂。新加坡兼具兩種體制的要素,而人們對這個國家的感受究竟是自由民主抑或窒息威權,則因為他們身處的位置而有很大差異。
且讓我首先說明自己的出身背景。我是一個新加坡人、一個獨立記者、一個運動者。正因如此,我處於一個非比尋常的位置。我不是新加坡主流媒體的記者,因此不必面對為統治菁英守門的總編輯;我也不是為國際媒體工作的外國記者,因此不必倚賴政府當局定期更新工作簽證。我擁有新加坡公民權,政府不能將我驅逐出境,至少不能直接驅逐。我的新聞工作與寫作讓我有機會訪問身分地位形形色色的人們,並且退後一步從更廣闊的視野來思考政治、民主與社會。身為一位運動者,我深度投入公民社會的運作──特別是死刑、刑事懲罰、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等議題;我也參與一群為數不多的新加坡人,一起進行組織、倡議與風險承擔工作。我聽取運動者與新聞工作者的怨言、閒聊與思考,這兩個群體的新加坡經驗與街頭巷尾的尋常百姓大不相同。
從我在二○一○年投身新加坡公民社會以來,曾經報導過三屆國會大選(,並且見證了多樁死刑案件歷程,其中一些死囚重獲生機,但絕大多數難逃一死。我曾經報導過多起示威抗議──或者說是新加坡標準的示威抗議,在警察局外面守候以追蹤當局對運動者「罪行」的調查;從藐視法庭到政府所謂的「非法集會」,這些「罪行」無所不包。我曾經三次被警方依《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進行調查偵訊:第一次受到嚴厲警告,第二次被高抬貴手;直至二○二三年六月,我還在等候第三次調查偵訊的結果。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曾經透過新加坡警察部隊(Singapore Police Force)對我發出警告,原因是我五個月前的一則臉書(Facebook)貼文涉嫌藐視法庭。我上法院挑戰這項警告,但是敗訴,最後必須支付總檢察署八千新加坡元的訴訟費用。
在我過去撰寫──媒體專題報導或評論、非政府組織(NGO)的報告、我主編的通訊《我們公民》(We, The Citizens)──的案件中,一部分是關於政府如何調查或起訴運動者。例如范國瀚(Jolovan Wham),他招惹警方的「犯行」再尋常不過:拿著一張畫有笑臉的紙板拍照,舉行的論壇有外籍人士透過Skype參與;後者讓他入獄。另一樁案件是西南巴萊(Seelan Palay)的入獄,他進行一場表演,拿著一面鏡子走向國會大廈,在建築物外面靜默佇立。此外還有警方對於運動者張素蘭(Teo Soh Lung)與鄞義林(Roy Ngerng)住家的搜索,理由是兩人在選舉投票日前一天(當局禁止競選活動)發布臉書貼文,因此違反「冷靜日」(Cooling-Off Day)規定。我也報導過移工議題與勞工權利遭到壓制,最近的案例就是二○二○年至二○二一年新冠肺炎大流行(COVID-19 pandemic)期間,數千名男性移工被隔離在空氣不流通的宿舍裡長達數個月。
換言之,我見識過許多新加坡政府公關活動避而不提的事情。對於發生這些事情的新加坡,權力體制的成員聲稱他們「不認識」。
政治自由與定義新加坡的權利
「認識」一個國家代表什麼意思?誰的認識順理成章?誰的認識不具正當性?誰的經驗能夠界定新加坡是什麼或者不是什麼?
我們對於新加坡的觀察或認識受到自身背景與立場的影響。對某些人而言,這個城邦的體系頗具吸引力;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它猶如一場壓力沉重的夢魘。許多人處於中間地帶,一方面很享受現代城市帶來的舒適生活,一方面要擔心自己跟不上激烈的競爭,必須設法適應一個憎恨失敗、懲罰異議的社會。
對於一個新來乍到、隨意為之的觀察者,新加坡──先進的科技、閃耀的天際線、教育程度良好的人民、無所不在的連結性──看起來並不像是一個威權主義國家。與其他國家──包括一些近在咫尺的鄰國──不同,新加坡的運動者不必擔心身體上的攻擊、綁架或暗殺。有些新聞工作者雖然惹惱政府當局,但並不會遭到專斷為之的逮捕或監禁。新加坡人不會因為個人政治觀點、政治活動而人間蒸發,不會發生流亡異議人士在異國橫死的事情。我們在網路上的討論往往各執己見、措辭強烈、運用嘻笑怒罵的迷因(memes)。
然而街頭沒有屍體或者監獄沒有記者,並不等於自由或民主。作為一個國家,新加坡將一種恐懼的文化正常化,《二○一八年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數位新聞報告》(2018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發現,六三%的新加坡受訪者表示「擔心在網路上公開表達個人政治觀點會被政府當局找麻煩」。新加坡人長期以來都將政治視為「高風險」或者「危險」。當新加坡人將「空間」──從學校教室與工作場所,到公務員體系與新加坡政府法定機構(statutory boards),任何一個根據體制人脈與地位來決定個人社會資本的網絡──描述為「去政治化(depoliticised),我們的意思是:只有一種非常狹隘的政治意見會被容許公開表達。新加坡人可以公開談論政治,但前提是觀點要與統治菁英看齊對正,因為這些觀點很容易被接受為「常識」。人們如果與宰制性的敘事唱反調,就會被貼上「搞政治」或者「激進」的標籤。人們知道表明真實想法不是明智之舉,從學校、職場到家中餐桌上都是如此。
獨立之前的新加坡,政治舞臺相當熱鬧;今日的新加坡,公民社會規模偏小、發育不良,其成長與成熟數十年來受到阻礙。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八○年代的逮捕與拘禁行動,讓一千多人未經審判就身陷囹圄,讓運動者與志工失去工作,讓公民社會的運作走走停停。時至今日,新加坡的公民社會不僅要倚賴數十年來的工作與進展,也必須在理論層面與實務層面重新學習,這都是因為早年的壓迫造成重大損失。
拜層層疊疊的法規與限制之賜,這樣的工作持續受到阻礙。依據新加坡公共秩序法,單一個人就可以構成非法集會或者遊行。全新加坡只有一個地方不必警方事先批准就可以抗議示威,而且絕不是李顯龍(Lee Hsien Loong)總理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特派員克莉絲汀.艾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專訪時形容的「一個廣大的發言場域」。不管是在什麼地方,運動者想要獲得許可進行「與理念相關的」活動往往非常困難,甚至不得其門而入。運動者還必須提防其他重重的法規:藐視法庭、「假新聞」、外國勢力干預。更別提那些檯面下的「黑名單」或「灰名單」(greylisting)做法,如何讓運動者的生活與生計處處碰壁。
在此同時,新聞記者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在地主流媒體──紙媒、網路、電視與廣播──受制於必須申請執照的法規,讓政府間接掌控高層人事任命,而且深陷於自我審查的企業文化。二○二一年,新加坡報業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將旗下掌控國內所有報紙的媒體事業獨立出來,成立「新報業媒體」(SPH Media),一家非營利性質、接受政府資金的公司,由一名前任內閣部長出任董事會主席。獨立媒體生存困難,接受外國資金──就算正當的新聞獎助金也一樣──若不是遭到禁止,就是會帶來風險,可能因此被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籤。在地的富裕階層不太願意支持獨立媒體,擔心自己會觸犯執政黨。部落客與獨立記者則必須面對以打擊「假新聞」為名的命令、調查與訴訟。
結果就是國家看似自由,但個人必須盤算:我的言論或者行為會不會太接近實質或想像的紅線?這種警覺已經完全內化,讓某些新加坡人一方面堅稱自由並未受限,一方面拒絕碰觸特定議題;另外一些人則是為求心安,盡量迴避「政治」或者任何「政治性」事務。如果你向來對界線敬而遠之,自然就不必擔心自己逾越界線。
現在讓我們依據這樣的背景脈絡,重新思考如何認識與定義新加坡。在新加坡的權力運作動態之下,某些敘事與訊息會被發揚光大,其他則被遮遮掩掩、排斥摒棄、審查或自我審查,無法出現在公共論述之中。公民社會的成員被耳提面命:運動者犯下錯誤、有欠公平、心懷偏見,我們「居心不良」,因此證詞與工作都不具可信度。少數族群與邊緣團體的生活經驗被嗤之以鼻,與此同時,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的政府要員則將關於種族正義與LGBTQ+權益的熱烈討論定性為「西方輸入」。
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新加坡的「真實情況」與人民行動黨主導權力體制的觀點成了同義詞。
報導新加坡的挑戰
新加坡是蕞爾小國,但充斥著矛盾、分歧與怪異特質。許多事情發生在檯面下、紀錄之外與灰色地帶,很難完整呈現或詳實敘述。如此一來,書寫新加坡也變得既富挑戰性又令人著迷。
在地媒體與國際媒體經常鼓吹揄揚我的國家是如何成功:從教育、都市規劃、經濟發展到社會發展,新加坡都被視為典範。這種讚揚雖然往往不無道理,但也經常誇大其詞,或者抽離了背景脈絡。新加坡的某些層面、政府政策及其施行、社會與文化,必須更近距離實地觀察,才會清晰可見。
一個例子發生在二○一八年,全球矚目的美國總統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川金會」之前,許多外國記者飛來本地,參與這場媒體大拜拜。一如前述,CNN明星特派員艾曼普當時專訪李顯龍總理,快結束時,她提及新加坡的「嚴峻的內部規範」以及欠缺政治多元性:「你認為新加坡將何去何從?你能夠預見一個更有彈性的未來嗎?你會推動更大程度的開放嗎?」
李顯龍祭出一如預期的辯護,指稱新加坡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選擇他的政黨,因此如果新加坡「嚴峻」、如果新加坡欠缺政治多元性,那也是順應人民的期望。
我還記得觀看這場專訪的片段、閱讀逐字稿的時候,很希望艾曼普能夠進一步追問李顯龍。人民行動黨領導人每當被質疑宰制一切、鉗制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壓抑政治環境的時候,總是會拿選舉當擋箭牌。然而選舉的存在並不是民主社會的唯一指標;就算當成唯一指標,新加坡選舉的公平性仍有許多問題可以質疑。儘管如此,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受訪時還是輕描淡寫就可以過關,原因在於外國媒體欠缺追根究底所需的背景知識、節目時間與決心。對於二十四小時運作的國際新聞輪播,新加坡只是眾多地方、眾多故事其中之一,而且很少會是最重要的地方與故事。
在地媒體奉行政治服從,國際媒體關注程度不足;新加坡以及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民夾在中間,因此欠缺多元化、多層次的面貌呈現。
序論:認識一個國家的權利【節錄】
「我不認識韓女士描述的國家。」
二○一八年新加坡駐美國大使米爾普里(Ashok Kumar Mirpuri)投書《紐約時報》,反駁我先前發表在該報的一篇文章,上述那句話是他的結論。我的文章描述新加坡與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如何在死刑議題上一搭一唱,並且有志一同將「假新聞」的相關論述化為武器。
米爾普里大使寫道:「韓俐穎的文章將新加坡描繪為一個威權主義的樂園,對政府的批評會遭到扼殺,毒品走私者則一律絞刑處死。」他聲稱我的說法背離事實,在新加坡「我們熱烈辯論各項議題,線上與線下都是如此。...
目錄
臺灣版序:無論你在何方
序論:認識一個國家的權利
第一章:消除成見的過程
第二章:我們不知道的事
第三章:記憶造就了我們
第四章:開放空間與密室運作:新加坡的公民反抗運動
第五章:國家的叛徒
第六章:掌權者的皮影戲偶
結語:我們將會萬分驚訝
致謝
臺灣版序:無論你在何方
序論:認識一個國家的權利
第一章:消除成見的過程
第二章:我們不知道的事
第三章:記憶造就了我們
第四章:開放空間與密室運作:新加坡的公民反抗運動
第五章:國家的叛徒
第六章:掌權者的皮影戲偶
結語:我們將會萬分驚訝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