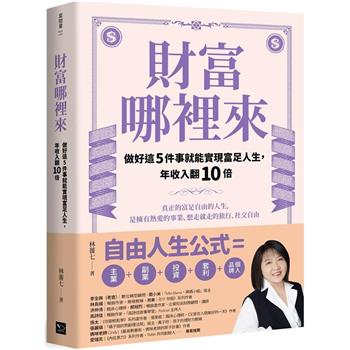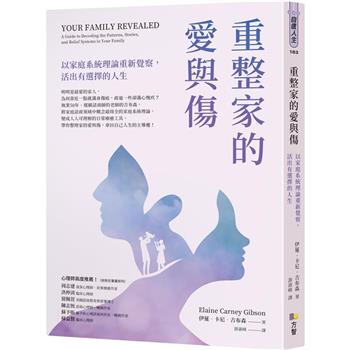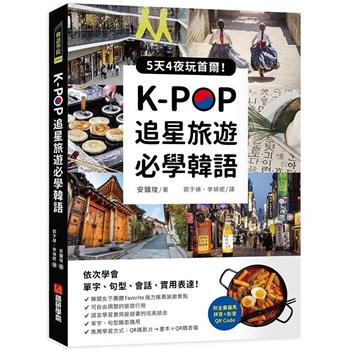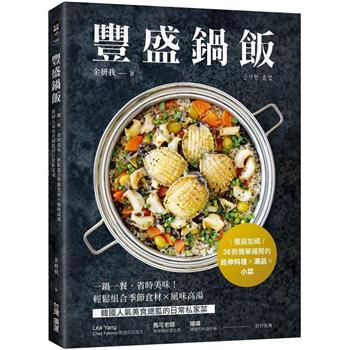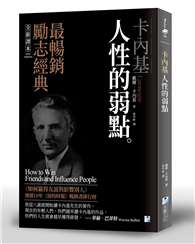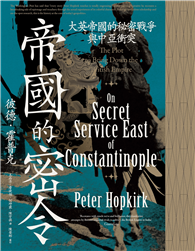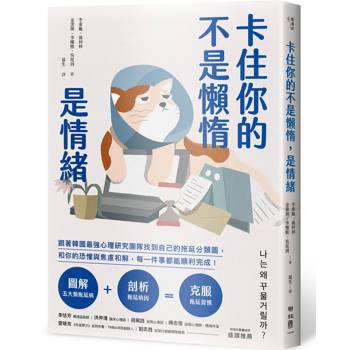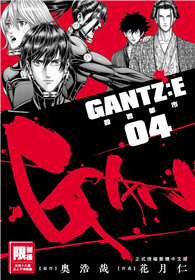★☆第25屆臺北文學獎年金大獎得獎作品★☆
一本女兒書寫父親的書
一個老派知識分子一路走來、積極參與臺灣社會轉型的漫漫歷程
=臺灣社會學家瞿海源的人生遍歷=
在(本書)訪談的過程中,我花了兩年將我的視線駐留在父親的知識社群,以及他們在歷史波濤中的痕跡……瞿海源與他的友伴站上了屬於自己的節點,節點接著節點,一起被時代沖刷,在沖刷中抉擇行動。
他們對抗威權追求自由,卻也經歷了被政治迷惑、被情懷迷惑、被流量迷惑、被自己迷惑的考驗,各自人生,也印照成我們的當今。而一切都還在沖刷中,但因為看見過往,當今所見,緩緩都有了歷史疊影,新的理解可從此而生。——瞿筱葳(本書作者)
瞿海源,臺灣社會學家,出生於二戰時的四川,三歲來臺灣。在六〇年代自由主義的微弱氣息中,成為本土第一代建立學術基礎的中堅,他和他的老師與同儕,在人生的青壯時期站在民主轉型的第一線,也進入了各種社會改革的現場。他們有些後來走進體制,有些維持運動姿態,有些堅持論政不參政,有些依舊維持抑或悖離了原本的初衷……所有的故事與人物,後來散進新聞、茶餘甚或課本教材乃至電視劇,他們有些還在世,有些已然離去。
瞿海源也是瞿筱葳的父親,在九〇年代的中學時光,她看著父親與野百合的大學生們出沒廣場、在電視評論時政,趕稿給報社記者,在諸多國政議題間辯論與溝通;成年後,看著他推動公共媒體、編寫課本,在艱難議題上成為抗議照片中最明顯的白髮爍爍。與此同時,瞿筱葳也開展自己的冒險,從社運、媒體、紀錄片一直到 g0v ,多個角度觀察並參與這個社會的變動。
對於父親,瞿筱葳以為已經做了一輩子田野,實際執筆後卻發現還有太多故事必須探究,不只對父親,也對那個其實不遠的九〇年代。父與女,受訪者與寫作者,在不同的時代與領域穿梭,聆聽與對話交織出雙軌的記憶,這也才發現,父親一直行動、一直想說的是:個體跟個體間,要有所連結,要逐漸形成共識;已成中年的女兒想要理解的,則是父親在名望之下的真實樣貌,以及過往的每個振幅間,我們如何走來。而這個回望與追溯,就是瞿海源一路走來的漫漫歷程,以及臺灣社會不間斷的變遷。
♬封面設計 & 封面、 內頁插圖 王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