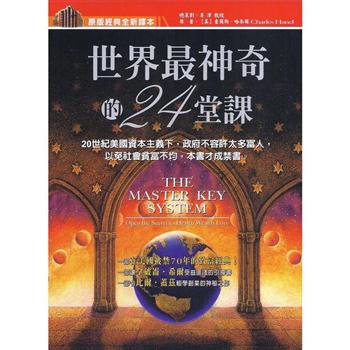導言
王鷗行
現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老師之一,將詩歌作為分享和探索人類內在智慧的媒介,絕非偶然。如果我們追溯到咸認影響了社會制度和思想的古代史詩,如《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伊利亞德》(Iliad)和《金雲翹傳》(Tale of Kiều)等作品,直到今天仍被人們所感受和踐行,我們會在這些文本中發現一個核心紐帶:將詩歌當作公民參與的媒介,不是作為論戰,而是強大而複雜的架構⸺其中公民的角色與社會的關係變得寬廣而複雜。換句話說,詩歌作品一直是相即的作品。
在Thầy(老師)圓寂後的幾天裡,多家媒體邀請我以佛教作家的身分,就這一重大事件發表講話,但我婉言謝絕了,因為我有什麼可說的呢? Thầy 還有什麼教誨是尚未鞏固,不言而喻的?他的修行和畢生工作,始終是為我們面對這一刻做好準備,進而為我們自己在俗世中的悲痛做好準備。我一直認為,什麼都不做,比缺乏強烈的意願或適當的條件而去做,要來得明智。但是,當一行禪師基金會執行董事丹尼斯.阮(Denise Nguyen)聯繫我,希望我跟我們的社群分享,並為《請以真名呼喚我》新版撰寫文章時,這些呼喚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因為我能夠作為你們中的一員,與你們對話。
眾所周知,語言和聲音是我們最古老的傳播媒介。Narrative(敘事)一詞的詞根是gnarus,在拉丁語中是知識的意思。因此,所有故事首先是知識的翻譯。不僅如此,它們還是能量的傳遞。正如Thầy 所教導的那樣,能量不會消逝。作為一名詩人,這是我每天都要面對的真理。因為閱讀一篇文章,即使是公元前十七世紀創作的文章,也是在接受四千多年前的思想所產生的語言能量。這樣,說話是為了生存,教學即是將我們的思想帶向未來。這篇文字彙集了Thầy和佛陀的教誨,是傳遞給未來世代的筏子。我們有這樣的共識,因為我們一直依附著這艘木筏。作為一個物種,我們擁有這樣的媒介是多麼幸運。我相信,儘管醫學和科學有重大的發展,語言仍是我們最先進的技術。我們應該致力為所有有情眾生建造新的木筏。我們的工作,正如Thầy 的工作,是跨越多個時代和無數領域,帶來解脫的悠久傳統的一部分。
是的,能量,甚至人,都不會真正死去。但我也必須說,作為一個還不具備出家修行功德的在家修行者,我必須承認,看到Thầy 的遺體準備火化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我知道Thầy 經歷了死亡和臨終,正如佛陀教導我們的那樣,死亡和臨終是所有眾生必須經歷的痛苦過程之一。由於我的修行不夠堅定,我含著淚水觀看了Thầy 的葬禮隊伍,既為他所建立的美麗社群而流淚,也為我心中的巨大悲痛而流淚。我為自己流淚,也為其他尚未有智慧和功德來承受這種痛苦的人流淚。
二○一九年十一月,我的母親身患癌症,彌留之際,四肢的熱度已經消退。她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Con ơi, giờ con đã biết nỗi đau này, con phải đi giúpngười ta nghe.”(我的孩子,你既然認識了這種病,就必須用這些知識去幫助別人。)我的母親雖不識字,但會背誦越南佛經,並經常用她的iPhone 聆聽Thầy的教誨。我告訴她:「好的,我不會白白經歷這種痛苦。」既然我們中的許多人都為Thầy 的圓寂而感到痛苦,我認為將悲傷視為一種能量,也是很有幫助的。願我們讓悲傷教會我們如何生活。讓它成為蓮花的淤泥,就像Thầy 所說的那樣。讓我們和它坐在一起,讓它穿越我們,從而將它轉化為類似愛的東西。我的母親從Thầy 那裡學到,痛苦可以轉化為知識。這不就是語言的作用嗎?
我謙卑地祈請各位,特別是我們的法師和長老們,因為你們已經「出家」,因此是人類現象的真正先驅。我謙卑地請求你們,在你們的修行中,尋找所有可能改變悲傷的方法(我相信你們已經這樣做了)。而我們這些「在家」修行者,將追隨你們的腳步。在我看來,這就是為什麼出家人是勇氣的真正化身,是比任何曾經舉起刀劍的人都更安穩、堅決的戰士:你們選擇了剃度,向人類知識懸崖之外的廣袤未知進軍,而我們則留在相對安全和舒適的地方,等待著你們的發現,隨時準備出發。
有人說,悲傷其實就是愛――但卻無處可去。在這個很可能占據我餘生的探索之中,我問自己,也問你們,親愛的社群:我們應該去向何方,無論是在我們之內,還是我們之外?現在,我們有了如此寬敞的木筏,可以容納如此多的人,再加上Thầy 的教誨,也許還會有悲傷,但已經沒有恐懼了。
知道你們一直都在,當你們坐下來,當你們跟隨呼吸,當你們供養,便是在探索答案。知道你們就在我們的前方,我可以在路上瞥見你們明亮的長袍,就像灰塵中的陽光碎片,我怎麼會害怕呢?更有甚者,我又怎麼會迷失呢?
沒錯,我很悲傷。我還會難過一段時日。儘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我還是找到了你。在你身上,我找到了自己。
那就是敘事,那就是知識。而詩歌,包括這些詩歌,使之成為可能。
以希望和文字寫就――
王鷗行(Ocean Vuong,法名:德海)
二○二二年五月
麻薩諸塞州北安普頓
譯者序
一懷抱一懷抱的詩/釋真士嚴
沒想過能完成一行禪師詩集的翻譯。禪師喜歡詩。二○一四年中風前,每年大年三十都會和弟子們一起吟詩賞詩。禪師的許多詩已譜成曲。當然,在賞詩聚會中,弟子們會準備吉他、古琴等樂器伴奏,獻上一首又一首的詩歌。禪師是那麼自在歡喜,這一天總是笑容滿面。要瞭解禪師,不可能不讀他的詩。
禪師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詩集。一九四九年秋,越南龍江出版社出版了《秋昏笛聲》(Tiếng ĐịchChiều Thu),收錄了五十首詩和一個劇本。那年禪師二十三歲,還很年輕。禪師初為人熟悉,並不是以僧人或法師的身分,而是作為一位詩人。禪師開創自由詩體,詩集出版後,認識他的人漸漸多了。禪師以詩會友,經常跟志同道合的年輕僧人和越南著名詩人一起分享詩作。
一九五四年,禪師在印光佛學院教書時,完成了大學學業,以法越文學專業學士學位,從新成立的西貢大學文學院(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畢業,並繼續創作詩歌,撰寫文章和書籍。
翻譯禪師的詩是一個大工程。多年來,一直不敢翻譯這本詩集,因為覺得這是極之艱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事。禪師的詩,除了幾首以英文創作外,其他均以越文寫就。我們知道,如果從英文翻譯成中文,會跟原本的詩作有很大距離,因為文化和語法上的差異,從越文翻譯成英文時做了許多修改、添加和減少。所幸越文和中文非常相似,均是單音字,文法也相近。因此,我們決定盡可能從原本的越文詩集《一懷抱一懷抱的詩,一滴一滴的太陽》翻譯成中文,希望能接近詩歌的原貌。中文詩集收錄了一百四十三首詩,包括二十多首尚未翻譯成英文的詩。越文詩集中的一些註釋,也加入了中文詩集。詩的排列次序,則依據越文詩集。
三位譯者身處三個不同的國家。我在法國梅村和梅村鄰近巴黎的梅村禪修中心,阮荷安在越南胡志明市,劉珍在中國上海。我們透過現代科技一起賞詩論詩,每人負責翻譯部分詩篇。感謝荷安對越文、中文和漢越語的細緻理解,豐富的翻譯經驗,以及多年來對文學和佛學的研究和教學,為我們理解和翻譯禪師的詩作提供莫大的幫助。劉珍一直從事寫作,對詩歌充滿熱誠,這幾年翻譯了禪師的多本著作,由她來做整本詩集的最後把關和潤飾,最適合不過。
年前,在英國「米香共修團」的週末廣東話禪營中,我建議安排一個賞詩的環節,一起欣賞禪師的中文詩歌。沒想到大家都很歡喜,感覺新鮮,並且深受感動。希望那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將延續禪師喜愛的詩歌聚會。
在此,希望提出越語的一個特點。越語雖有「你」和「我」的說法,但習慣上鮮少使用,反而常用親屬稱號來稱呼彼此,習慣將家族關係延伸到社會關係中,因此不管說話還是書寫,皆常只見到「兄」、「弟」、「姊」、「妹」、「嬸」、「叔」……這也見於禪師的詩中。
每一首詩,都充滿禪師對弟子和眾生的慈悲與無邊的愛。每一首詩的翻譯,也充滿了弟子對禪師的感恩和尊敬。翻譯和校對時,有很多感動的時刻。儘管盡心盡力,仍難免有不足之處,願朋友們見諒。
感謝大塊文化出版發行這本詩集,讓弟子們能以詩報師恩,以詩結緣。
釋真士嚴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法國Maison de L'insp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