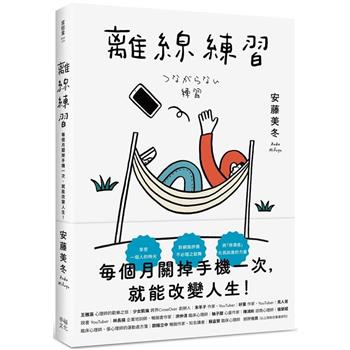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 朱宥勳第一本抒情散文集。
◎「我是因為討厭寫字,所以才喜歡文學的。」
◎ 減重是為了感情挽回?戰神卻被評為缺乏攻擊欲望?會寫作是因為肌肉不協調不想寫字?⋯⋯關於身體的、情感的、性別的、政治的,透過幽默自嘲與自我挖掘,看見不同面貌的朱宥勳。
王盛弘(作家)
寺尾哲也(作家)
宋文郁(作家)
李欣倫(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李桐豪(作家)
沐羽(作家)
洪明道(小說家/醫師)
孫梓評(作家)
盛浩偉(作家)
蔡宜文(《蔡宜文的多元宇宙》Podcast主持人)
謝宜安(作家)
——推薦
每一個平凡長大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凡的辛苦
本書是朱宥勳第一本抒情散文集,討論他在三十歲以前從來不會考慮的身體——身體不就是用來實踐頭腦思考的工具嗎?重點應該放在頭腦吧!——直到身體基本機能出了狀況,才讓以前從來沒考慮過的減重、健身、格鬥進入生活,全面改變了生活型態,也才誕生了這本思索身體的作品。
開始探索身體後,發現文字善於指涉思想而拙於切進身體。身體的感受讓文字的描述像是摹本,語文只能試圖逼近,而難以直接命中。但也在這些想盡辦法瞄準的書寫中,讓我們讀起來有著全新的觸感。
與書同名的〈只能用4H鉛筆〉,談到作者幼年學寫字,肌肉協調不佳而字寫不好,因而討厭寫字,最後卻成了持續書寫的作家。〈坐監實習生〉回憶在一所更甚於監獄的私校求學,牢密禁錮卻使得每一代的學生迸發出創作的渴望。〈第一次減肥就失敗〉則是一篇驚人的「異男情感路」冒險,錯誤的減肥方式混雜同等錯誤的感情挽回法,讀起來讓人覺得荒唐卻又不忍。〈記得怎麼吃〉是全書核爆級的「懺情錄」,從味覺啟蒙展開的不完美婚姻故事,個中滋味只能各自評斷。在不了解身體而與之抗衡多年後,終於學習透過新的方式來認識自己的身體,〈碳水的辯證法〉、〈身體駕駛員〉、〈拳腳的應用題〉便是進入試圖理解的篇章,從飲食方式到重新連結身體,都進入了新的天地。
整本散文集,可以看見一個先天身弱的孩子,在成長階段面臨身體的限制,卻發展出對閱讀的喜愛;因為私校的嚴格管制,進而產生了創作的想望;因為腿部疾患而開始運動減重,卻開展了對於飲食與身體的全新認識。這些形而下的、物質上的變化,卻大大影響了對自己與對世界的認識。
朱宥勳這麼寫道:「以往念到『辯證法』的時候,總是以心智、以抽象概念去理解。但現在,我所吃的每一口冰淇淋和雞胸肉,每一份薯條和燙青菜,都用身體牢牢記得:這就是正,這就是反,這就是合。身體不言,但它會用每一道步伐的輕重告訴我,最近的狀況如何。我們彼此控制,彼此折磨,也彼此取悅,而這一切,正最證明了我和它的親密。我是它也不全是它,等於它也外於它;如此,才總算是認識了身體——人到三十多,終於能和它好好打聲招呼,原來你是這樣地、一直在這裡。」
每一個平凡長大的孩子,都有自己不凡的辛苦。身體限制我們、苦勞我們,而身體也滋養我們、豐富我們。這些平凡或不凡的辛苦,終究長成了我們的模樣,而終於我們也學著感受身體。身體不是我們以為的那樣,但它始終等待我們去理解。
「從宛如監獄的校園開出寫作的果實、從失戀中學到眼淚與味覺、在傷病中找到與身體共存的方式、從對抗學校機構到嘗試對抗陽剛氣概,宥勳的自我清晰地從對抗中呈現。在這本書中每一篇文章、每一個符號,宥勳對我們傳送訊息(很難得地,並沒有太說教),讓我們看到他如何找回他的身體,同時也建立他更新版本的自我,即使要甘心放棄一些自由。」
—— 蔡宜文,〈推薦序:目擊證人在這裡〉
「思考文學時我們很少特別想到身體。請益文學前輩『怎樣才能寫出好作品』時,很少人會收到『練好身體』這樣的回答。〈只能用4H鉛筆〉讓人意識到,身體的『不自由』可以根本的影響書寫。反過來想,《只能用4H鉛筆》重新掌握、改造身體的過程,可以視為是自由的追求。」
—— 洪明道,〈推薦序:從身體發力,用思考決鬥〉
「在這本書裡,身體不再屈於頭部的運輸,而是反過來:我將窮盡頭腦的能力,試著把關於身體的種種,運輸到文字裡來。關乎情感、關乎性別、關乎技術、關乎政治⋯⋯也不止於這些的。說得清楚、說不清楚的,都讓我們試試看吧。」
—— 〈自序:身體在這裡〉
作者簡介:
朱宥勳
台灣桃園人,一九八八年生,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曾獲金鼎獎、林榮三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台積電青年文學獎。
出版過:
小說集——《誤遞》與《堊觀》。
小說連作——《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用虛擬的未來口述歷史結構,以多樣觀點描述一場台灣近未來的戰爭,探索台灣民族共同體的想像。
長篇小說——《暗影》以職棒簽賭案來探索台灣社會的面貌;《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摸索學校教育體制的權力結構問題。
非虛構作品——《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以評傳筆法描述九位戒嚴時期台灣小說家的故事,凝鍊出小說家們畢生的苦心與執著,也展現台灣文學如何在受壓迫時代努力找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故事;《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台灣文學百年論戰》以章回小說的形式,訴說貫穿二十世紀的十場台灣文學論戰,這一次次的論戰也就形塑了我們現在的文學環境;「作家新手村」系列二書《作家生存攻略》與《文壇生態導覽》,以田野調查精神一五一十描繪神祕的文壇鋩角與求生術;《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分析如何用小說技術來解析世界、說服他人、洞悉讓人混淆的資訊洪流;《學校不敢教的小說》藉經典小說解讀來分享學校教育裡不會探觸,但卻是許多年輕心靈期待理解的作品。
與朱家安合著的《作文超進化》,教學生培養思辨能力,只要知道人們如何思考、大腦如何運作,就能把文章寫得又快又好。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介紹新世代的小說創作者。與愛好文學的朋友創辦電子書評雜誌《祕密讀者》,曾持續三年不間斷出版當下台灣僅見的文學評論刊物。
也在聯合報鳴人堂、蘋果日報、商周網站、想想論壇等媒體開設專欄。
個人網站:https://chuckchu.com.tw
章節試閱
只能用4H鉛筆
依照日本工業規格(JIS),鉛筆的筆芯硬度共有十七個等級。最軟的是6B,接著是5B、4B⋯⋯直到B,數字越小顏色越淺,筆芯越硬。而在另一端,最硬的是9H,同樣會依序降到2H、H為止,數字越小顏色越深,筆芯越軟。在我念小學時,大多數的同學都使用介於光譜正中央的HB或F,只有在畫畫的時候,會選擇顏色比較深的2B或3B。我則跟大家相反:我用的是校門口文具店買不到的3H和4H。
聽說,那是特別要畫細細淡淡的線條時,才會用到的鉛筆。
但我拿它寫作業,寫作文——我最討厭寫作文了。
精確一點說,我討厭的是寫字。而這跟我使用的鉛筆有莫大的關係。不知道為什麼,只要我使用B系列的鉛筆,作業簿每頁都會烏黑糜爛。別人寫起來乾乾淨淨的頁面,我的就會是畫壞的素描。每一筆畫,我硬是可以比別人粗上一倍;再加上我寫字姿勢不好,手掌總是在紙面拖磨,這些筆畫就進一步被手汗抹成畫壞的水墨。
一開始,大人多半以為我不認真寫作業,屢屢退件,要我擦掉重寫。他們會這麼想很合理,因為我確實寫得奇慢,寫沒兩行就喊手痠、要休息。不過,橡皮擦完全無法挽救我的「畫作」,不管重寫幾次都沒有比較好,反而把紙頁擦薄擦破了。來回幾次,每一本作業簿都從內爛到外,表裡如一,弄得老師也無處下紅筆。
大人終於發現:問題癥結在我寫字很用力,下筆如下刀,運筆如刻碑。老師上課說古代書法家「力透紙背」,我心想這有什麼難的,我隨便都透三層,就算用的是軟軟的2B鉛筆。如果這是大書法家的資質,我早生幾百年搞不好就是一代宗師了。但可惜我生在一九八八年,成長於剛剛解嚴那個半開放半保守的年代,一名小學生的價值,至少有一半是由他的字跡美醜決定的。大人急啊:每個老師都說這孩子成績不錯,但那個字⋯⋯說得好像我罹患了什麼遺傳疾病一樣。
下筆太用力是個物理問題,那就得用物理方法解決。大人沿著日本人開發出來的筆芯硬度,讓我一節一節往上測試。B不行就換HB,或者F,或者H,或者⋯⋯一路連踏七座營盤,總算是在4H這關找到了平衡點。如果再往上到5H,筆芯就實在太硬,削過之後跟長槍沒有兩樣,我不必怎麼屏氣凝神,也能一筆扎個透心涼。4H剛剛好:不至於筆畫到處,開山裂石;也不至於碳粉漫漶,把作業簿塗成煤田。我第一次學到「煤田」這個詞的時候,還真就想起了小時候的作業簿,四個格子一組剛好併成一片「田」,不含鉛不含水的墨跡在大平原上水淹七軍。
筆夠硬,作業寫不乾淨的問題也就到一段落。但那時候不管大人或我都沒意識到真正的問題背後還有問題——為什麼我寫字會用力到,無法跟別人用同樣的鉛筆?
那個年代,「感覺統合能力測試」之類的檢測還不流行,即便我的母親自己是小學老師,也未必能意識到「有些問題不是認真就能解決」,多少需要一點早療或動作訓練。我當然更不會懂這些,只是本能地覺得「寫字很煩」。所以,在小學階段的四大科目裡,我最討厭國語科,社會科次之,自然科又次之,最喜歡的是數學。跟這些科目本質毫無關係,純粹是依照考卷所需的「中文作答字數」來決定的。小時候的我超級討厭寫字。而我並不知道,其實我跟「字」本身無冤無仇,純粹是我的寫作姿勢、用力方法出了很大的問題,導致我寫每一個字都比別的同學更疲勞。畢竟他們沒有把能量浪費在「力透紙背」之上。
幸或不幸,我也正處於台灣教育史上「剛剛開始要廢除體罰」的階段。我自小也被熱熔膠棒、木製飯匙或從課桌椅拆下來的木條打過,不過總體而言,應該是比戒嚴時代的人少挨了不少板子。在這新舊交替的時期,我的老師們便以罰寫來取代體罰。多年以後,我在師培課程裡明白了他們的邏輯——如果都要處罰學生了,與其無意義地使學生疼痛,不如讓他「順便」練習一些需要反覆操作才能精熟的技能,比如寫出一手漂亮的好字。
殊不知對我來說,罰寫就是體罰。上課愛講話、聽課不專心、偷偷在抽屜裡讀課外書⋯⋯每天我都能成功讓自己領到罰寫。或者抄課文兩遍,或者抄生詞二十行。母親和我同校,她教高年級,幾乎每天都要上課兼課輔到傍晚四、五點。中低年級的我則中午十二點就應該放學,不用去安親班,直接去她任教的班級找她。但我硬是可以罰寫到兩點、三點甚至抄到放學鐘響。沒有人知道我為什麼會寫這麼慢,我也不知道。而我的字跡有變漂亮嗎?
嗯,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在那堂師培課上全程微笑。
因為我不守秩序,所以罰我抄課文,這個邏輯大概只比用頭痛藥去醫治肚子痛好一點點。最悲傷的是:我的頭還是繼續痛。
討厭寫字的我,最討厭的學習活動自然是「寫作文」了。別看我現在彷彿語文教育改革鬥士,到處批評作文教學哪裡不合乎寫作原理、哪裡是無效訓練,小學時的我可沒有這麼高層次的困擾,我討厭的只有「寫字」本身而已。而作文偏偏都是字。所以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自己最早幾篇作文是怎麼寫的。
人物:我和母親
時間:某天下午
地點:母親在臥房,我坐在小桌旁
母親:「你可以寫『我們這次校外教學去了九族文化村,學到很多新知識』。」
我縮寫:「校外教學去九族,學到很多。」
我問:「那下一句呢?」
母親沉吟:「你可以寫『我們看了很多表演,認識了很多原住民文化』。」
我再縮寫:「我們看表演了解原住民文化。」
我再問:「那下一句呢?」
⋯⋯
如是反覆一下午,就能完成一篇作文了。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教過我的小學老師,非常驚訝我日後竟然成為一名作家,整天寫臉書還不停出書。不過,請容我稍稍辯解:我並沒有完全抄襲我母親的文字。她確實曾經在快要被我逼瘋的狀況下,一句一句「引導」我寫作文。但老實說,即使我當時非常年幼,我仍然不太滿意她唸出來的句子,因此在我落筆為文時,我已經絞盡腦汁、用上我當時所有的創造力,去修改她的文字了。
不是因為「九族文化村」顯然不能代表「原住民文化」,而是因為,我覺得她的句子還是太長了。
字太多,筆劃也太多。
記得嗎?我討厭寫字。
所以,任何她唸出來的句子,都會被我縮寫成更短的版本。如果可以,我會少寫幾次主詞。經實驗證明,如果一個段落開頭就已經有「我」或「我們」了,接下來兩三句通通省略,老師也不會發現我偷懶。或者,當母親無意間在相鄰的句子內用了重複的字眼,比如上述場景第二句的「很多」,那我就會合併句型,只講一次甚至不講。至於要寫哪些字眼,我也是精挑細選的:「認識」二字共三十三劃,「了解」二字共十四劃,就算我還沒學到除法,我也知道把「認識」換成「了解」會很划算。
我會非常、非常慎重地,在腦袋裡思考母親提示的句子裡,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刪減。在找出「最省力解」之前,我是不會輕率動筆的——我就曾有幾次衝動落筆,寫了兩三個字,才發現還有更省力解。但4H的筆跡已經重重刻下,我一時腦袋打結,困在超難的數學題裡:到底要繼續寫下這個「比較差的句子」,還是要擦掉重寫「最省力解」?哪一個總筆畫數會比較少?心念電轉,我突然意識到:不管哪一個答案,一定都比「一開始就寫最省力解」的筆畫更多了。逝者已無可追,我再也無法踏入同樣的河流兩次,回到那個可以少寫兩三筆的平行時空裡了。思及此,幼時的我悲從中來,眼淚便把作文簿淹成了4H鉛筆也無法挽救的水鄉澤國了。
如此習慣,便被我沿用到所有必須寫作的場合。大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我那麼喜歡看書,每個禮拜可以三本五本從圖書館搬書來回,但學校舉辦的「讀書心得比賽」我永遠沾不上。書比我看得少的,一年下來可以累積五十篇、八十篇圖文並茂的心得,換得朝會上台表揚的榮譽,而我的圖書證有數以百計的借閱紀錄(且常常因為上課讀這些書而受罰),卻永遠只交最低規定篇數、且每篇只寫到最低規定字數。我不賴帳,但帳也不能賴我。
這類「精算」,自然也發生在國語習作的「造句」或「照樣造句」欄目。現在我當然知道,那些習題意在培養學生的文法和語感。許多同學懶得造句,會拿參考書或安親班給的答案來照抄。我也懶,但懶在別處:我嫌參考書上的解答太冗長,懶得抄。那時的作業簿封底還有「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這樣的對句,如果那是國語習作的例句,我一定把它刪成「活潑」和「堂正」(管他語感對不對,反正意思乍看沒有不對),並且在心底抱怨「好學生」跟「中國人」根本不能對成一組——「中國人」是一個完整的身分,正如「學生」也是一個完整的身分一樣,何必多寫一個「好」?那可是六劃呢。
到了中高年級,便有老師哭笑不得向母親抱怨:「沒見過懶成這樣的,更氣人的是答案還都對!」
大人和我都沒有想到,這套行之有年的偷懶術,竟可能是我這一生最早的「文學技術鍛鍊」。因為討厭寫字,所以我比很多人更早養成了「落筆前先思考」的習慣,不會想到哪裡寫到哪裡;因為想要省力,我也無意中讓自己理解了「一句話可以有很多種寫法」,並且能很快找到較精簡的寫法。而在這過程裡,所有哭笑不得的老師,也都意外成為我的「教練」,當我真的縮減過頭,導致語感破碎、文法渙散的時候,他們的批改就會讓我知道「縮到這個程度別人會看不懂」。沒問題,如果十個字的版本不行,我下次會換成十一個字的版本試試看。
幾年後,我加入了高中的校刊社,在那裡正式接觸文學寫作。我們最早接觸的,要不是白先勇、張大春這類現代小說家,要不就是洛夫、夏宇、楊牧這些現代詩人,他們多少都受現代主義影響,力求「少即是多」的減法美學。因此,我們上繳給學長的習作,多半也都會被要求凝鍊、凝鍊再凝鍊。十六歲的我,不是很清楚為什麼這樣寫就等於好的文學,但對我來說似乎不太難——就是我從小到大養成的那套寫作習慣嘛。而且,這套寫法很自然能博得我的好感,因為它要求我少寫,而不是多寫。
因此,幾乎可以說:我是因為討厭寫字,所以才喜歡文學的。即使到了高中以後,我絕大多數的創作都直接以電腦寫下,再也不需要4H鉛筆或更難塗改的原子筆,但我自幼豢養在心底的小編輯仍然時時陪著我。我可以偶爾請他去休息一下,讓我寫一些比較「鬆」的東西,比如臉書貼文或YouTube頻道腳本;但如果需要,比如修我自己的稿子,或者在批閱學生作業時,他就會隨時探頭出來,和我一起計算「最省力解」。
慢慢的,我也有好一陣子忘記自己必須使用4H鉛筆,當然更沒有去細究,到底是什麼根源,讓我栽入文學成為一名寫作者。
直到有一年,母親帶弟弟去一家診所,做漸漸時興起來的「感覺統合能力檢測」。似乎是弟弟出現了某些症狀,有人建議帶去檢查一下。那時我是大學年紀,純粹是陪同進了診間。醫生拿起小槌敲敲各處關節,又指定小弟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動作,很快給出了診斷。就在我們起身準備離開時,醫生叫住了我,他要我坐下來接受檢查。
「我?」
醫生點頭。接著就是一系列敲敲打打,肢體指令。
到一段落,醫生露出了意味深長的微笑。我有點緊張。他是不是看出什麼了,所以才特別要檢查我?
醫生說:「書念得不錯,對不對?」
呃?不會吧,這難道可以從我的膝反射裡看出來?
母親有點驕傲地承認我成績確實不錯,並且愛看書,從小就還滿乖的。
「是啊,他當然要愛看書,因為他沒有其他選擇了。」醫生又微微一笑:「體育課都跟不上,沒辦法跟人家玩對不對?是不是很容易跌倒?或者,是不是常被人說笨手笨腳,找不到東西、打破這個摔壞那個?」
時至今日,我都是一名堅定的無神論者;但在那一瞬間,我感覺面前的這位不是醫生,而是某個神機妙算的半仙。
醫生淡淡說出他的判斷:你的肢體反應速度比常人慢很多,肌肉協調能力也不好,平衡感也有問題。一般的肢體動作還好,但小肌肉控制能力不太好,應該沒有辦法做太精細的動作。這是非常典型的、需要早療的案例。只是現在長到這個年紀,很多狀況已經定型,或者你都用自己的方式克服了。別人頂多覺得你有點笨拙,不過,只要日常生活沒有太大的問題,那就沒什麼關係了。現在也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治療。現在講這個,只是要跟你說:
「都沒有人看出來對吧?辛苦你啦。」
我已經忘記那天是怎麼結束的了。他講的都對,我確實有那些奇奇怪怪的狀況,而我一直都覺得是我自己體能不好、專注力不夠,所以才會三不五時總有一些小災難。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是很在意那些問題。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我之所以十分感激這位醫生的贈言,主要就一個原因——謝謝他讓我知道,為什麼我必須使用4H鉛筆。他讓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錯,全部都不是。
並且,我還因為自己的「缺陷」,獲得了文學這項禮物。
如果沒有文學,沒有寫作,我整個童年令人厭煩的習字經驗,就只是在毫無意義的陷坑裡屢起屢仆而已了。四個格子一組田,每一個待填的格子,都有著幽深的泥濘。多年以後,我終於長大到不害怕泥濘,也幸運地等到了電腦作業時代的全面來臨。早生幾百年的我,不見得有機會成為書法家;但要是我早生二十年,我可能也沒機會成為作家。
但還好,我其生也晚,趕上了。
只能用4H鉛筆
依照日本工業規格(JIS),鉛筆的筆芯硬度共有十七個等級。最軟的是6B,接著是5B、4B⋯⋯直到B,數字越小顏色越淺,筆芯越硬。而在另一端,最硬的是9H,同樣會依序降到2H、H為止,數字越小顏色越深,筆芯越軟。在我念小學時,大多數的同學都使用介於光譜正中央的HB或F,只有在畫畫的時候,會選擇顏色比較深的2B或3B。我則跟大家相反:我用的是校門口文具店買不到的3H和4H。
聽說,那是特別要畫細細淡淡的線條時,才會用到的鉛筆。
但我拿它寫作業,寫作文——我最討厭寫作文了。
精確一點說,我討厭的是寫字。而這跟我使用的鉛...
作者序
【推薦序1】
目擊證人在這裡
蔡宜文(《蔡宜文的多元宇宙》Podcast主持人)
社會學家Bourdieu將品味視為是一個人有意或無意間所透露出來的無數訊息,這些訊息會不停地相互加乘,讓內行的觀察者把這個人,分在哪一個群體、哪一個社會位置的區塊(——我很訝異自己會在這篇序的一開始就提到Bourdieu,我相信宥勳也會很訝異,因為他很清楚Bourdieu的任何一個理論不是用一篇序言的文字可以講清楚的)。
作為讀者,在閱讀散文時,就好像被迫成為一個內行的觀察者,你被迫觀看敘事者做了什麼事情,他做這些事情時到底在想什麼,甚至,你被迫看到他援引什麼樣的理論跟譬喻來描述上述這些東西。在散文集中,你透過許多篇章的累積(即使你知道散文集中不同篇章的敘事者可能並非同一個)去琢磨,這個敘事者是哪一群人?是自覺曲高和寡懷才不遇痛斥新自由主義的三十歲後左派?還是強調努力就能成功三句話不離自己如何在二十九歲達成財富自由的網路創業家?這些人在散文中使用到的歌曲、喝到的那杯飲料、引用誰說的話,都會完全不同。特別是這種與作者人生有強烈連結的抒情散文,就好像漫威電影這幾年習慣的方式,把時間線拉開,突然讓你看到過去跟現在的角色在你的面前共同演出。然後如果你足夠死忠、足夠是他們的人,你就可以比別人多挖到幾個彩蛋,多得到幾個蛛絲馬跡,最終你就會得到:這個人是不是跟「我」一樣的人,他會不會是我的朋友,我會不會想跟他一起打《世紀帝國》,當革命到來的時候是要先殺他還是找他一起推翻暴政。
但我看《只能用4H鉛筆》時不同,因為我不只是這些散文某個神祕的觀察者,沒有辦法只坐在評審台,像《超級名模生死鬥》的主持人Tyra Banks對作者說:「你入選了,你可以繼續待在『來當我朋友』的比賽中。」
——因為,他本來,就是我的朋友。
在社群網絡蓬勃發展的時代,有一種公關危機是「不符合人設」,也就是網路上的名人們每當他們爆出其言行舉止跟他們在網路上表現相差甚遠之時,就會出現他們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出來澄清某某某私下就是這個樣子,他就跟他網路上呈現的一樣,天真無邪、大膽無畏。而我在寫作本序時,總在想宥勳找我來寫這本書的序,是不是就是期待我作為本書的目擊證人,畢竟作為在〈第一次減肥就失敗〉尾聲以《世紀帝國》競賽選手出場的大學同學,我完全能作證,那些動輒三四百塊的滷味、雞排、鹹酥雞毀滅的不只有他的減肥計畫。
目擊證人跟觀察者不同,目擊證人的重點是確認「這件事情」有無發生,而這件事情並不是每一件發生在散文中的細節,不是宥勳是否有前往京都或東京考察甜點,更不是宥勳是否大幅減少他的體積(這個大家只需要去看他的YouTube頻道就知道了),是一個神祕的系統讓宥勳成為現在這個版本的自己。而他則是這套系統的生產者與實踐者,由各種小小的事件組合起來,例如某天我發現原本是某家超大杯全糖古早味紅茶愛好者的宥勳,跟我說他喝不下去,味道太奇怪了。如果我是個稱職的觀察者,在這一瞬間我可能選擇分析說,這就是品味養成的過程,透過對於茶飲的品味,他已經離開了只是因為熱量、冰、甜或咖啡因的需求來品嘗食物,進入到另一個社會階級的品味:為了味道或特殊的體驗。
但我是一個目擊證人,我當下只會忍不住吐槽:「這是誰?朱宥勳嗎?」我甚至不會用到什麼階級分析,吐槽的前提是覺得合理。因為每次戀愛對他來講,就好像在職進修,進修到的味覺不會還給老師,愉快跟傷痛也不會。
去除掉作為目擊證人這點,這本書最讓我感到愉快的地方,是看到一個男人發現自己有身體。這句話聽起來很奇怪,請大家不要以為女性主義者都認為男人是一群沒有身體的頭,而是異性戀男性是沒有性別的:性別是別人的事情,是女人跟LGBTQ+或其他字母符號的事情。這世界的預設值就是男人,就好比沒有男性文學,男性寫的東西,就是文學;沒有男總統,男人當的總統,就是總統。在身體上也是,男性的身體被視為是預設值,沒有月經、沒有例行性的疼痛、沒有特別需要處理的兩坨脂肪,上述這些才是人體運行的特例,所以才需要特別的設備或制度上的協助。而男性就是,沒有問題,就算你覺得有問題,那也是你自己的問題,你應該要自己解決。
因為你是男人,所以疼痛、畏懼或是身體的暴力也不應該是問題,至少你不應該覺得這是問題,否則你就不是一個夠格的男人。當然這個對於身體的忽視,他展現在不同的階級或群體上有不同的展現方式,例如在如同宥勳一般的文人中,其展現方式可能就是認為在意身體就如同在意金錢一般俗氣,你對於自我的認同應該奠基於物質之外,是形而上的,讓那些東西構成你,由你主動去選擇你要認同什麼,由「你」這個意識有意識地去建構自我,而不是由一個受限於物質與俗世的身體來建構你。再附加上如我跟宥勳的學長高穎超在研究中提到,在台灣「文武」的陽剛氣概鬥爭,正如同腦與身體的鬥爭,在搶奪誰才能定義正港真男人。當宥勳進入駕駛艙開始連結軀體的同時,不僅是重新降生,也是重新建構在他的系統內,男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宥勳重新把身體給找回來,不只是病痛的、不結實的、痛苦的、受傷的身體,還包括了接受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柔順健康且好用的身體。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這本書以宥勳的青少年生涯開場,第一次提到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是用來描述他所就讀的學校如同監獄一般規訓他的生活,讓他成為一個「外表」溫馴但沾染了體制陰暗與猥瑣的乖孩子,而在之後Foucault再次出場,卻是宥勳體會到柔順而有用的身體到底有多好用,甚至因此感到愉快。Foucault並無否定規訓會帶來愉悅,而在他後續的著作中也提到過,牧者式的權力(pastoral power)並不完全如同監獄或其他全控機構一樣,時時刻刻盯著人,然後要將這個柔順的身體作為特定的用途,是真的「為你好」,並希望你能在現世擁有一個健康快樂的身體、足夠的財富跟良好的生活品質,因此提供你要達到這些的知識,這樣的規訓,不好嗎?
我不知道。即使看完這本書,我還是難以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同樣致力於描述全控機構與自我如何形成的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提到,即使在精神病院這種強力剝除所有收容者任何關於自我符碼的機構中,仍然可以看到這些收容者極力地用各種方式,從與機構對抗中長出他們的自我:從宛如監獄的校園開出寫作的果實、從失戀中學到眼淚與味覺、在傷病中找到與身體共存的方式、從對抗學校機構到嘗試對抗陽剛氣概,宥勳的自我清晰地從對抗中呈現。
在這本書中每一篇文章、每一個符號,宥勳對我們傳送訊息(很難得地,並沒有太說教),讓我們看到他如何找回他的身體,同時也建立他更新版本的自我,即使要甘心放棄一些自由。
關於身體如何成為有用的身體這件事,或許人沒有絕對、百分百的能動性與自由意志,但也並不是全然被動接受權力的馴化,而是身在其中,嘗試跟體制討價還價,找到一個生活的最佳解,而這個最佳解並不泛用、且時刻變動,只有你知道,那就是目前的版本。這本書,就是宥勳ver2024的最佳解。
最後,我還是要像Tyra Banks一樣,將這篇序交給宥勳說:「你入選了,你可以繼續待在『來當我朋友』的比賽中。」——沒辦法,這就是讀者的尊榮。
【推薦序2】
從身體發力,用思考決鬥
洪明道(小說家/醫師)
在台灣北部成長、異性戀、男性,這幾個標籤放在一起,容易讓人覺得「這些事情我都聽過了」。《只能用4H鉛筆》圍繞在改變身體的主軸上,討論身體的諸多面向,其中經驗並不都那麼殊異。不過經過朱宥勳對自身經驗的剖析,卻讓人發現許多想不到的潛在關聯,有「事情原來可以這樣想」的快感。
身體的溯源報告
傳統的散文側重經驗。「和自己身體不熟」這樣的主題,一般散文可能會用盡文字臨摹體感,又或刻畫情緒和傷害,以求渲染力使讀者共感。但朱宥勳沒有這樣做。他在書中展示他爬梳身體來歷、掌握相關知識,進一步改造身體的過程。
書寫經驗時,朱宥勳有時用劇場的方式來展演,彷彿此時寫作者坐在舞台下,看著舞台上過去的自己。例如〈只能用4H鉛筆〉中額外標出人物、時間、地點,製造出距離感。有時他則像一個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農產品溯源那般追溯自己身體的歷史。
追溯之旅上至出生,下至大學時期飲食習慣,包含體感記憶,也涉及量測和計算。「數學不會就是不會」,網路上時常有人如此形容數學的冷硬。在寫作中,數字的確很難文學化。〈看醫生遊戲〉透過長輩重述印象深刻的畫面,讓讀者更能理解早產是怎麼一回事。這便是寫作者施展之處,一個有趣的事件,比任何體重數字和評估指標還讓人有感。
在個人的經驗中,朱宥勳夾雜大量細節、事實和科學知識。在〈身體駕駛員〉,朱宥勳描述腳踝疼痛的求醫過程。這個困擾在醫療體系中難以解決,最後透過運動重新與肌肉接上線,才有顯著改善。朱宥勳不只純然寫「什麼有效什麼沒有效」的個人經驗,而更盡力去理解背後的解剖學、身體力學,再用文字記述連接身體的經歷。
這樣的寫法相當「朱宥勳」,竭盡所能想弄懂規律和原理,予以歸類、系統化。至少以我所有的知識來讀,這本書關於身體、醫學的內容是沒有什麼差錯的,求真的態度不得不讓人佩服。
在序中,儘管朱宥勳自承經驗有限、為避免俗濫,一直沒有出版散文集。然而,這本文集也不是典型著墨經驗和情感的散文。他不是要掏心掏肺和讀者跋感情(pua̍h kám-tsîng)的,而是分析個人經驗和集體知識後,有所發現而記下的思考過程。
重拳擊出說服力
抒情散文尊重個人經驗和情感,不會有文學評論說「該名作者的經驗不正確」。這卻往往讓人誤以為,散文是可以全然不考慮真確性的。這裡的「真確性」,是指作者能否理解事實,或援引恰當的根據提出觀點。為了抒情之便而犧牲真確性,在散文中並不罕見,但多被容許。
《只能用4H鉛筆》化用許多身體、醫學的科學知識。這些知識不僅很難有模糊空間,還特別難寫。身體的知識時常「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或無法推論出線性的因果關係。如果我們真能縮小到可以進入體內,觀察身體運作,我們看見的,不會像《工作細胞》那樣有好人有反派,或許會更像《瑞克和莫蒂》中的解剖樂園,複雜、混沌而時有偶然。某種程度來說,這類知識違反人腦習慣的理解模式,需要更高超的「技術」來讓讀者消化吸收。
一件事由專業研究者、科普作家、文學寫作者來寫,或許專業研究者或許較能掌握真確性,而文學寫作者在技術性占優勢。不過,《只能用4H鉛筆》在真確性和技術性兩邊達成平衡,書寫經驗也化用知識,並無偏廢。
另一方面,有些看似合理、容易被理解接受的宣稱,卻並非事實。〈碳水的辯證法〉中列舉了許多違背一般人直覺的事實,有意破除這類迷思,例如貌似健康的素食,熱量算起來常常比較高。這類違逆直覺的事實,需要相當技巧才能撬動讀者的大腦。單純道出事實,很難和讀者產生連結、說服讀者。就像遇上愛說教的前輩,即使他們所說內容再怎麼正確,總是很難讓人聽得入耳。
於是,朱宥勳透過不斷問答,一步一步拆解食物的卡路里組成。看這個段落時,我腦中會浮出立法院官員答辯的情景。這些段落帶領讀者跟著進入思考,最後再來個應用題,測驗讀者。這類科普書常用的寫作方式,放入散文中顯得特別,讀者不妨一試。
在事實之下,朱宥勳進一步追索與身體交織的歷史、社會,這是我在讀這本書時最受吸引的地方。
從個人身體而生的公共性
異性戀男生又是怎麼長大的?他們和自己身體的關係如何受社會形塑、影響?很少有作品像《只能用4H鉛筆》這樣一再挖掘。
朱宥勳直接用〈第一次減肥就失敗〉,探討肥胖和自己的關係。對醫療或公共衛生端來說,肥胖是個與慢性病相關、有待面對的實在問題。社會建構論者則強調肥胖是醫療化的結果。不同專業場域的人都建構出關於肥胖的理論,試圖做出指導或干預。〈第一次減肥就失敗〉並沒有被互相劃分、截斷的理論影響。在探究自身如何看待肥胖、思考和行動的過程,種種細節讓我看到更多複雜處。
朱宥勳更後退一步,思考社會加諸異男的情感教育。他以一種近乎做研究的方式,將經驗與記憶抽絲剝繭,審視其中的關聯性。在〈換皮〉則繼續延伸異男情感教育的影響,反省自己是否將漠視外表視為陽剛的表現。〈記得怎麼吃〉則聚焦在關係如何在身體留下刻痕,私人的內面情感則簡略帶過,這樣的取捨顯示出寫作者的決心。朱宥勳的確發揮了散文的長處,極盡所能思考與身體相關之事,像研究者一樣不斷比對假說,試圖找到一個最具解釋力的框架。
閱讀時,我偶爾會自私的想,若這些經驗並非單一個案,而是許多人的類似經歷的話,會是很好的研究題目。
〈只能用4H鉛筆〉、〈坐監實習生〉秉持類似的剖析方式,將自己身體遭遇的困境,連結到威權以上、民主未滿的社會環境。台灣由戒嚴轉至民主化的過程,學者提出了身體解嚴的概念。不過,身體民主化顯然難以瞬間發生
朱宥勳對這種過渡狀態做了細緻的觀察。威權式管教和限制學生自由,在〈坐監實習生〉中被寫得相當徹底。校園中規訓手段粗糙,與本來就有病根的身體硬碰硬,種下往後身體疼痛的遠因。讀這些篇章後,再看談白色恐怖的〈歷史的陌生水域〉,更能接近受難者的身體經驗。
自由的身體 自由的文
〈拳腳的應用題〉中,朱宥勳寫被教練調侃「你們讀書人⋯⋯」,讀到這裡我莞爾一笑。這本書的確有著藏不住「台灣文學狂熱」的氣息。在不預期處突然來個金句,不吝放閃的〈換皮〉以經典小說對話做暗語。譬喻或類比時,朱宥勳更時常以文學作參照。把肌肉的牽扯想成作品的鋪排,把味覺的對比想成創作的對比。
思考文學時我們很少特別想到身體。請益文學前輩「怎樣才能寫出好作品」時,很少人會收到「練好身體」這樣的回答。〈只能用4H鉛筆〉讓人意識到,身體的「不自由」可以根本的影響書寫。反過來想,《只能用4H鉛筆》重新掌握、改造身體的過程,可以視為是自由的追求。
這幾年,出現了像《殖民地之旅》、《遠足》難以被傳統散文吸納的作品。《台語現代散文選》則收錄了科學文章、得獎感言,在編選邏輯上翻新源於華語的「散文」概念。《只能用4H鉛筆》這樣的散文集不是讀者習慣的,對抒情散文讀者,這可能太過理性、太過計算了一點。再加上要出入經驗、體感、知識和分析,有更多規則需要面對,更多不同性質的事物需要接合,都需要相當磨練。如同書中所說,「從不自由當中,體會出另一種隨心所欲的自由」。《只能用4H鉛筆》便是在迎戰種種不自由後,呈現出的自由成果。
【自序】
身體在這裡
英國教育學家肯尼.羅賓森在他著名的TED Talk演講〈學校教育扼殺了創意嗎〉裡,有句話如此形容學者:「他們向下看著自己的身體,將其視為運輸『頭部』的一種交通工具,不是嗎?」
我不是學者,但我覺得這段話也非常適合拿來形容作家:高度開發頭部以上,用眼讀書、用腦思考、用嘴演講。頭部以下可有可無,能維持基本機能即可。我在三十歲以前,確實都是過著這樣的生活。直到身體的「基本機能」開始出問題了,我才被迫開始意識到它的存在。減重、健身、格鬥,三項全新事物進入我的生活,成為日常的節奏拍點,讓我終於把注意力挪轉回來,認真思索這尊我已居住數十年的身軀。
然後發現:我還真是不暸解它。
這本散文集,便是一趟自我暸解之旅。說實話,我過去一直沒有出版散文集——傳統意義上的「抒情散文」,不是報導性或論述性的「非虛構寫作」——的念頭。我也寫過一些抒情散文,卻始終有點懷疑:這樣述說自身,沒有太多公共性的文字,真的值得結集成書嗎?黃錦樹曾說過,散文不能多寫,因為人自身的經驗和情感是有限的,一多就容易「濫」。正是因為同意這樣的觀念,所以我更專注於小說和非虛構寫作,因為它們都有技藝上或知識上的「大義名分」;散文集就一擱再擱,畢竟我實在沒有把握,誰需要知道「我這個人」的諸般瑣事?
然而,開始思考「身體」之後,我才漸漸感受到散文這一體裁獨特的自由。散文可以自由出入於經驗、情緒和論述之間,「側錄」作者的思考流程。表面上,我是在對讀者絮絮叨叨;實際上,我必須借助這一過程,才能把事情想清楚。尤其身體之事太過迫近,若不繞道文字,實在難以取出後設的距離感,無法真正將它變成「外於我的、可以理解的對象」。
而在撰寫本書的過程裡,我也越來越意識到此中矛盾:一方面,我依賴文字來思考,但另一方面,身體的許多奧祕,卻是反文字、甚至反思考的。如同我在〈拳腳的應用題〉的自我詰問:我如何能以文字捕捉一記刺拳的質感?這幾乎就是在問,我如何光靠文字,讓人「嘗到」一道好菜的味覺、口感與質地?我們就是吞了一整本食譜,也不可能真嘗到一口八寶丸的。
所以,如果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本書時有瑣瑣碎碎、著迷於細節的傾向,還請見諒。提供更多的細節,是我唯一能夠逼近身體的真實,唯一能稍微捕撈吃穿行止之存在的方法,即使我從一開始就知道,「逼近」的極限值終究只能近似,而難以全等。
不過,借道於文字之途,也並非全無收穫。有些我習以為常的傾向,直到付諸文字之後,我才發現那些習性之深,幾乎深入骨髓。比如〈換皮〉和〈只能用4H鉛筆〉寫到自己斤斤計較算計生活裡的每一刻度;〈碳水的辯證法〉和〈身體駕駛員〉那種試圖將一切體驗理論化、系統化的態度;〈第一次減肥就失敗〉和〈記得怎麼吃〉裡「明知可不為卻還是如此」的「異男包袱」⋯⋯每寫一篇關於身體的故事,身體似乎就要再提醒我一次:在這個主題裡,我是沒有超然一切、超脫局限的可能性的。身體就是局限,就是居所。身體是可能性,也是不可能性。那就是作為一個人類,難以擺脫、只能共處的本源——腦子可以想得意興遄飛,身體就是會在它該在而能在的地方。
就讓我試著倒轉肯尼.羅賓森的挖苦吧。至少在這本書裡,身體不再屈於頭部的運輸,而是反過來:我將窮盡頭腦的能力,試著把關於身體的種種,運輸到文字裡來。關乎情感、關乎性別、關乎技術、關乎政治⋯⋯也不止於這些的。說得清楚、說不清楚的,都讓我們試試看吧。
是為序。
【推薦序1】
目擊證人在這裡
蔡宜文(《蔡宜文的多元宇宙》Podcast主持人)
社會學家Bourdieu將品味視為是一個人有意或無意間所透露出來的無數訊息,這些訊息會不停地相互加乘,讓內行的觀察者把這個人,分在哪一個群體、哪一個社會位置的區塊(——我很訝異自己會在這篇序的一開始就提到Bourdieu,我相信宥勳也會很訝異,因為他很清楚Bourdieu的任何一個理論不是用一篇序言的文字可以講清楚的)。
作為讀者,在閱讀散文時,就好像被迫成為一個內行的觀察者,你被迫觀看敘事者做了什麼事情,他做這些事情時到底在想什麼,甚至,你被迫看到...
目錄
推薦序 目擊證人在這裡 (蔡宜文)
推薦序 從身體發力,用思考決鬥 (洪明道)
自序 身體在這裡
只能用4H鉛筆
看醫生遊戲
坐監實習生
歷史的陌生水域
第一次減肥就失敗
記得怎麼吃
碳水的辯證法
身體駕駛員
拳腳的應用題
換皮
推薦序 目擊證人在這裡 (蔡宜文)
推薦序 從身體發力,用思考決鬥 (洪明道)
自序 身體在這裡
只能用4H鉛筆
看醫生遊戲
坐監實習生
歷史的陌生水域
第一次減肥就失敗
記得怎麼吃
碳水的辯證法
身體駕駛員
拳腳的應用題
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