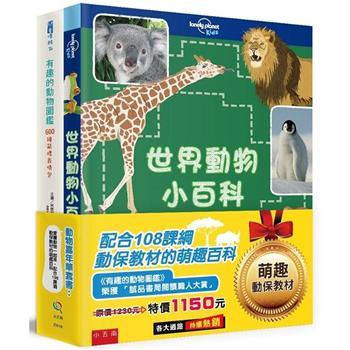我的尋羌之旅開始於1994年夏季。我一路跟隨文獻記載中的歷史記憶,追尋羌人來到汶川。然而便是在此,突然,前面那些歷史臆想以及我二十年來的羌族研究成為一場空幻夢境。面對真真實實的羌族,我覺得自己對人、社會、民族、歷史等等的知識匱乏得可笑。只是我十餘年的「尋羌」之旅找到的並非傳統,而是變遷。
我以這本配合照片的田野雜記,來呈現過去我的尋羌之旅中所見、所聞,介紹各地羌村民眾生活與溝中的文化、傳說。這不只為了紀念一些驟然消逝的過去,而更希望藉著它來呈現羌族的獨特之處——他們如一面誠實的鏡子,映照著人們難以察覺的自我本相。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尋羌:羌鄉田野雜記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尋羌:羌鄉田野雜記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明珂
哈佛大學博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通信研究員,台師大講座教授,中研院院士。研究領域為中國民族、游牧社會、族群認同與歷史記憶。曾長期在青藏高原東緣從事結合史學與人類學的羌、藏族田野,建立由邊緣理解中國之方法基礎。由理解邊緣族群而將其奇特化為熟悉,因而將吾人熟悉的知識視為奇特,並以同一邏輯重新理解它們。主要著作為《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等書。
王明珂
哈佛大學博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通信研究員,台師大講座教授,中研院院士。研究領域為中國民族、游牧社會、族群認同與歷史記憶。曾長期在青藏高原東緣從事結合史學與人類學的羌、藏族田野,建立由邊緣理解中國之方法基礎。由理解邊緣族群而將其奇特化為熟悉,因而將吾人熟悉的知識視為奇特,並以同一邏輯重新理解它們。主要著作為《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等書。
目錄
岷江上游
一元錢的命
在川藏之間
松潘
與世隔絕的村寨?
溝中的世界
杜杰的家人
高山草場
山神與地盤神
松潘城
黎光明
北川
蕎麥的故事
白馬將軍與走馬將軍
漢番邊界
胡耀邦贈送的藏袍
禹里羌鄉
茂縣
周老師與毛老師
老童與寨子裡的酒
永和河壩
毒藥貓
翻越史家山樑子
水磨坪與巴卓溝
射蟒英雄的故事
三龍溝
三龍諾窩寨
黑虎五族
黑虎將軍
黑虎溝的老端公
牛尾巴寨「人過年」
沙朗與尼薩
汶川
周倉揹石塞雁門
瓦寺土司
馬端公
釋比經文: 羌戈大戰
孝子與孽龍
理縣
爾瑪尼(黑羌族)
弟兄祖先故事
黑水
大黑水
蘇永和
小黑水的猼猓子
後記
一元錢的命
在川藏之間
松潘
與世隔絕的村寨?
溝中的世界
杜杰的家人
高山草場
山神與地盤神
松潘城
黎光明
北川
蕎麥的故事
白馬將軍與走馬將軍
漢番邊界
胡耀邦贈送的藏袍
禹里羌鄉
茂縣
周老師與毛老師
老童與寨子裡的酒
永和河壩
毒藥貓
翻越史家山樑子
水磨坪與巴卓溝
射蟒英雄的故事
三龍溝
三龍諾窩寨
黑虎五族
黑虎將軍
黑虎溝的老端公
牛尾巴寨「人過年」
沙朗與尼薩
汶川
周倉揹石塞雁門
瓦寺土司
馬端公
釋比經文: 羌戈大戰
孝子與孽龍
理縣
爾瑪尼(黑羌族)
弟兄祖先故事
黑水
大黑水
蘇永和
小黑水的猼猓子
後記
序
自序
1994 夏季在我學術生涯中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對曾是年少輕狂的我來說,在此之前兩年得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又在這一年得到馳名國際學界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終身聘職,40 歲以後的學術生命中還會有什麼可令人振奮的轉變?
然而就在這一年,我首次踏上大陸的土地。由北京到西安、西寧,一路上造訪各地考古與民族研究機構,到處遞出我印著 「哈佛大學博士」 的名片,賣弄著我在西方苦讀有成的學問。直到一天,我來到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見到我碩士、博士論文中的研究主題,羌族……。
我的尋羌之旅便始於這一年,1994 年夏季。在西安,陜西考古所的朋友領著我到處看西周早期遺址﹔我遙想,當年姬姓族如何與土著姜姓族合作開拓此基業。而後,我由西安搭上往西寧的火車。在穿越隴山時我望著車窗外,依稀看見兩千多年前西戎中的秦人吞併鄰近諸戎部落,殘餘的戎人攜老扶幼踰過汧水、隴山往西遷徙的景象。火車進入湟水河谷﹔當年一個神話般的戎人,無弋爰劍,受秦人追捕逃到此地,是什麼樣的神奇讓他以及他的後世子孫成為羌人的領袖豪酋?在西寧、湟中、湟源等地,我望著河谷上大片大片金黃色的油菜花田,彷彿見到漢代羌人各大部落彼此爭奪這些美好河谷,以及,後來當這些河谷成為漢軍屯駐的田地後,他們卑微地要求漢軍許他們在沒有人耕作的河谷放牧。由西寧返回西安後,我乘火車穿越秦嶺。在自古號稱難行的山崖蜀道上仍可見一截截殘存的巨木棧道﹔我想著,古羌人是否便是由此穿過秦嶺天塹,一波波地進入川西北成為兩漢魏晉時的白狼、白馬等羌部?
如此我一路跟隨文獻記載中的歷史記憶,追尋羌人來到汶川。然而便是在此,突然,前面那些歷史臆想以及我20 年來的羌族研究成為一場空幻夢境。面對真真實實的羌族,我覺得自己對人、社會、民族、歷史等等的知識貧乏得可笑。於是此後到2003,這10 年間我幾乎每年都要在羌族地區住上一兩個月,在真實的 「人」 與 「社會」 面前重頭做一個學生,重新尋找古代羌人與今之族。
2003 年我以羌族為主題的著作《羌在漢藏之間》出版。此後我的研究田野轉移到川西的大渡河流域,與紅原、若爾蓋等川西北草原地區。經常從馬爾康或紅原回成都,我都要刻意經過松潘、茂縣、汶川等地,探探老朋友們。
發生在2008 年五月間的汶川大地震,羌族人民的生命、財產、文化受到極嚴重的損失。而所有這一切的根基,環境生態,更受到難以恢復的破壞。在悲傷之餘,我的一些羌族朋友甚至有出於激憤的宿命觀﹔他們說,這毀滅性的自然災害似乎是針對著羌族而來。我不認為這是什麼神秘的宿命,它只是一種歷史與地理環境二者迭合造成的結果。汶川地震發生在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兩大高低地理板塊間的斷層帶上。在長程歷史發展下,此兩大地理板塊分別為藏、漢所佔有,而羌族正處在漢藏之間,因此也在此兩大地理板塊之間。
目前災後羌族社會文化復建陸續開展,羌族社會將有一番新面貌,文化也會有改變創新—這是1980 年代以來持續發生的變化,地震破壞及災後重建只是讓它突然加速而已。我以這本配合照片的田野雜記,來呈現過去我的尋羌之旅中所見、所聞,介紹各地羌村民眾生活與溝中的文化、傳說。這不只為了紀念一些驟然消逝的過去,而更希望藉著它來呈現羌族獨特之處—他們並無奇風異俗,只是有如一面誠實的鏡子,映照著人們難以查覺的自我本相。
1994 夏季在我學術生涯中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對曾是年少輕狂的我來說,在此之前兩年得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又在這一年得到馳名國際學界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終身聘職,40 歲以後的學術生命中還會有什麼可令人振奮的轉變?
然而就在這一年,我首次踏上大陸的土地。由北京到西安、西寧,一路上造訪各地考古與民族研究機構,到處遞出我印著 「哈佛大學博士」 的名片,賣弄著我在西方苦讀有成的學問。直到一天,我來到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見到我碩士、博士論文中的研究主題,羌族……。
我的尋羌之旅便始於這一年,1994 年夏季。在西安,陜西考古所的朋友領著我到處看西周早期遺址﹔我遙想,當年姬姓族如何與土著姜姓族合作開拓此基業。而後,我由西安搭上往西寧的火車。在穿越隴山時我望著車窗外,依稀看見兩千多年前西戎中的秦人吞併鄰近諸戎部落,殘餘的戎人攜老扶幼踰過汧水、隴山往西遷徙的景象。火車進入湟水河谷﹔當年一個神話般的戎人,無弋爰劍,受秦人追捕逃到此地,是什麼樣的神奇讓他以及他的後世子孫成為羌人的領袖豪酋?在西寧、湟中、湟源等地,我望著河谷上大片大片金黃色的油菜花田,彷彿見到漢代羌人各大部落彼此爭奪這些美好河谷,以及,後來當這些河谷成為漢軍屯駐的田地後,他們卑微地要求漢軍許他們在沒有人耕作的河谷放牧。由西寧返回西安後,我乘火車穿越秦嶺。在自古號稱難行的山崖蜀道上仍可見一截截殘存的巨木棧道﹔我想著,古羌人是否便是由此穿過秦嶺天塹,一波波地進入川西北成為兩漢魏晉時的白狼、白馬等羌部?
如此我一路跟隨文獻記載中的歷史記憶,追尋羌人來到汶川。然而便是在此,突然,前面那些歷史臆想以及我20 年來的羌族研究成為一場空幻夢境。面對真真實實的羌族,我覺得自己對人、社會、民族、歷史等等的知識貧乏得可笑。於是此後到2003,這10 年間我幾乎每年都要在羌族地區住上一兩個月,在真實的 「人」 與 「社會」 面前重頭做一個學生,重新尋找古代羌人與今之族。
2003 年我以羌族為主題的著作《羌在漢藏之間》出版。此後我的研究田野轉移到川西的大渡河流域,與紅原、若爾蓋等川西北草原地區。經常從馬爾康或紅原回成都,我都要刻意經過松潘、茂縣、汶川等地,探探老朋友們。
發生在2008 年五月間的汶川大地震,羌族人民的生命、財產、文化受到極嚴重的損失。而所有這一切的根基,環境生態,更受到難以恢復的破壞。在悲傷之餘,我的一些羌族朋友甚至有出於激憤的宿命觀﹔他們說,這毀滅性的自然災害似乎是針對著羌族而來。我不認為這是什麼神秘的宿命,它只是一種歷史與地理環境二者迭合造成的結果。汶川地震發生在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兩大高低地理板塊間的斷層帶上。在長程歷史發展下,此兩大地理板塊分別為藏、漢所佔有,而羌族正處在漢藏之間,因此也在此兩大地理板塊之間。
目前災後羌族社會文化復建陸續開展,羌族社會將有一番新面貌,文化也會有改變創新—這是1980 年代以來持續發生的變化,地震破壞及災後重建只是讓它突然加速而已。我以這本配合照片的田野雜記,來呈現過去我的尋羌之旅中所見、所聞,介紹各地羌村民眾生活與溝中的文化、傳說。這不只為了紀念一些驟然消逝的過去,而更希望藉著它來呈現羌族獨特之處—他們並無奇風異俗,只是有如一面誠實的鏡子,映照著人們難以查覺的自我本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