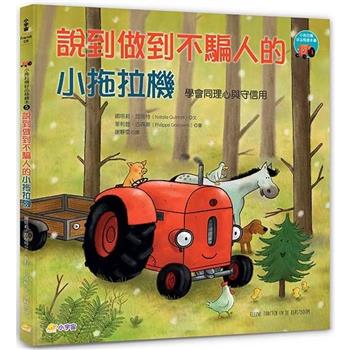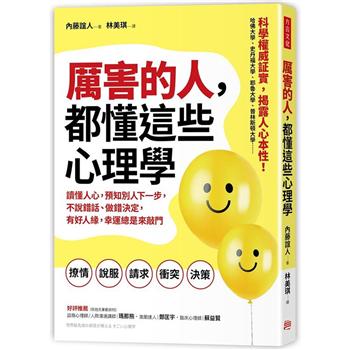當夢想無法成真時,我們將何去何從?
一部關於希望與失望、力量與脆弱的不朽經典,
深刻捕捉了人性在殘酷現實中的掙扎。# 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公認為20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文學著作之一
#七度改編登上百老匯、歌劇院、電視和大螢幕,並曾創下劇場最佳票房
#長踞全球中小學及大專院校的必讀書目
#真正還原史坦貝克小說原貌的全新譯本
《人鼠之間》講述的是美國大蕭條時代兩個流浪工人的夢想與悲劇,書中以資本主義社會對勞動者的剝削為背景,描繪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脆弱,以及在困境中人性的掙扎,甫出版即狂銷五十萬冊。
雖然這部作品出版至今已有九十年的時間,但它所描繪的主題,時至今日,依然沒有改變。
******
這是一個沒什麼希望的年代,過一天是一天,能有幾周的工作就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數十萬工人湧進加州,在季節性勞工的需求下,流浪於一座又一座農場間,求得生活的溫飽。
蘭尼和喬治就是這樣卑微的流浪工人,但他們不同,他們情同手足。
身材魁梧,卻善良純真得像個小孩子般的蘭尼,有一點弱智,總是惹上麻煩,必須依賴喬治的幫助和引導,才能生活在這個複雜又艱難的社會中。喬治嘴上抱怨被他拖累,卻決定讓蘭尼留在身邊。畢竟,有人需要、有人在乎,有人可以一起作夢,這讓喬治感覺自己還像個人。其實,喬治也知道,夢想本來就是謊言,只不過,它可以讓日子看起來沒那麼糟。
這次他們流浪來到一座農場,又說起那個夢想,但是,這一次有點不同,有更多人被感動而決定追隨。喬治受到感染,似乎也被自己的夢想催眠了。有大家一起談論,那個美好未來彷彿近在咫尺。最後,一聲槍聲驚醒一切,讓所有人都回到殘酷的現實……
作者簡介:
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1902-68)
一九六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被譽為「美國之聲」的美國作家,作品涵蓋長篇小說、短篇故事、劇作及散文。
史坦貝克十四歲就立志當作家,從那時起便投入大量時間寫作。他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進入史丹佛大學求學,但對學業興趣缺缺,數度休學,最終輟學追尋作家夢。輟學之後,他一邊寫作一邊四處打工維生,曾做過記者、營建工人、照服員、魚苗孵化場工人等,終於靠著《薄餅坪》在文壇嶄露頭角。他一生筆耕不輟,總共出版了二十五本書,其中包含十六部小說、六本散文集,以及數本短篇故事集。
加州的薩利納斯(Salinas)是他的故鄉,在那個以農產品生產與交易為主的小鎮上,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農場與大量移工。他熱愛這片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靠雙手打拚的人們。這份感情昇華成一種對所有社會底層人士的關懷,他藉由一本本社會小說提出嚴厲的社會批評,為那些受到政治與經濟壓迫的弱勢者發聲,讓人看見他們的困境與在困境中閃耀的人性光輝。
他在一九三○年代出版了著名的勞工三部曲:《人鼠之間》、《相持》(In Dubious Battle)和《憤怒的葡萄》。《憤怒的葡萄》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立茲小說獎,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後期作品包含《伊甸園東》、《查理與我:史坦貝克攜犬橫越美國》等。
譯者簡介:
蔡宗翰
自由譯者,現居高雄。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各界評論一致激賞
這個故事擁有所有優秀小說的共通元素──故事情節所影射的東西超越情節本身,但這隱含的主題(作夢的危險)卻一點也沒有阻礙到主要故事的發展。本書構思精巧、精鍊,以一個個行動快速且直截了當的推展;與史坦貝克其他四部加州小說同樣是上乘之作。──《書評文摘》(The Book Review Digest)
《人鼠之間》是一部驚悚小說,這個短篇小說長度的故事扣人心弦,讓你非一口氣讀完不可。──《紐約時報》書評
殘酷與溫柔交融在這奇異動人的文字之中……必然發生的命運步步進逼,讓讀者深深著迷。──《芝加哥論壇報》
一個簡短卻充滿力與美的故事。史坦貝克為現代硬漢柔情派的美國小說貢獻了一部小傑作。──《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名人推薦:各界評論一致激賞
這個故事擁有所有優秀小說的共通元素──故事情節所影射的東西超越情節本身,但這隱含的主題(作夢的危險)卻一點也沒有阻礙到主要故事的發展。本書構思精巧、精鍊,以一個個行動快速且直截了當的推展;與史坦貝克其他四部加州小說同樣是上乘之作。──《書評文摘》(The Book Review Digest)
《人鼠之間》是一部驚悚小說,這個短篇小說長度的故事扣人心弦,讓你非一口氣讀完不可。──《紐約時報》書評
殘酷與溫柔交融在這奇異動人的文字之中……必然發生的命運步步進逼,讓讀者深深著迷。──《芝加...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在索立鎮南邊幾公里的地方,薩利納斯河的河道緊貼山邊,水深且綠。水溫並不低,因為陽光把河水曬得暖暖的,在河邊黃色的沙地上濺起亮光,然後河水流進了一個狹窄的池子。河的一側,金色的邊坡愈往高處,愈發崎嶇,最後化作加比蘭山脈的堅石。但在靠山谷的另一邊,河岸成林。每年春天,柳樹新綠,低垂的葉梢撫著雪融後的奔流,葉間偶爾會夾雜一些從山上沖下來的殘枝碎屑;美國梧桐斑駁的白色枝條橫越池上。樹下的沙地覆滿厚厚一層脆裂的落葉,蜥蜴在其中竄梭,窸窣作響。到了傍晚,兔子會從灌木叢間現身,坐在沙地上。夜裡,平坦的河岸成了其他動物的天地:四處探路的浣熊、腳趾分明的農場獵犬、在漆黑中來喝水的鹿,都一一在濕軟的地上留下了足跡。
柳樹和梧桐之間,有一條被踩平了的小徑。無論是要到水池游泳的農場男孩,還是沿著公路走了一整天,傍晚時想在河岸湊合著歇一晚的流浪漢,都走這條路。小徑旁有一棵特別高大、樹根低橫的美國梧桐,樹前留有一堆灰燼,看來很多人在這兒生過火,他們的屁股已經把樹根坐得光滑。
***
熱了一天,樹葉間的微風揭開夜晚,暮色漸漸向山頂蔓延。在沙岸上,兔子靜靜地坐著,如一尊又一尊的小小灰色石雕。這時,從州際公路那兒,傳來了踩在清脆落葉上的腳步聲。一聽到聲響,兔子迅速無聲地躲了起來。一隻警覺的鷺鷥奮力飛起,然後重重落在河面上。有那麼一刻,周遭毫無動靜。最後,有兩個男人沿著小徑來到綠色的池子邊。
他們一前一後沿著小徑走了過來;來到開闊處,仍然維持一人在前,一人在後。兩人都穿著牛仔褲和帶有銅扣的牛仔外套,戴著黑色軟帽,肩上揹著捆實的毯子。走在前面的男人身材矮小,動作俐落,膚色黝黑,眼睛四處張望,五官分明。他全身上下都抖擻有神:不大但有力的雙手、精瘦的臂膀、直挺的鼻梁。在他背後的另一個人則和他完全相反:這個人個頭高大,有一張寬垮的臉,一雙蒼白的大眼,和一對下垂的寬闊肩膀。這位仁兄步伐沉重,像是一頭熊一樣拖著腳走路。行進時,他的手臂不會在身體兩側自然擺動,而是無力地垂在身旁。
走在前頭的那個人在空地上驟然停住,跟在後面的大個子差點撞了上去。前面的那人脫下帽子,用食指擦了擦帽子內裡的吸汗條,然後甩掉手上的汗水。後頭的大個子把毯子往旁邊一扔,趴下身體,直接就綠色的池子喝起水來。他大口暢飲,像匹馬悶著頭吸水。矮小的男人緊張地走到他身邊。「蘭尼!」他斥責道:「蘭尼,該死!不要喝那麼多。」蘭尼繼續悶頭喝著池水。矮小的男人彎下身子,搖搖大個子的肩膀,說道:「蘭尼,你再喝下去,就會像昨天一樣吐個稀巴爛。」
蘭尼把整顆頭都浸到水裡,帽子也沒脫。當他終於在岸邊坐了起來,帽子還不斷滴著水,把他的藍色外套都弄濕了,水還流到了背上。「真好喝。」他說:「喬治,你也喝一些,喝一大口。」他笑開了。
喬治卸下包袱,輕輕放在河岸邊。他說:「我不覺得這是可以喝的水,看起來髒到爆。」
蘭尼把大手伸到池子裡,甩甩手指,濺起一些水花,漣漪從池子的這邊盪到另一頭,然後又反彈回來。蘭尼看著漣漪說:「喬治,你看,看我變出了什麼東西。」
喬治跪坐在池邊用手舀水,很快地喝了幾口。「還不難喝。」他承認:「可是這看起來不是活水。蘭尼,給我記得,死水不可以喝。」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絕望。「你一渴,水溝的水也會喝。」他舀水潑潑臉,再用手搓一搓,下巴底下和脖子後面也都擦洗了一下。然後他戴上帽子,從河岸邊退開,雙手抱住膝蓋坐著。一直看著喬治的蘭尼,也有樣學樣。他退開,屈起膝蓋,然後雙手抱膝。他看看喬治,再看看自己有沒有做對。他也像喬治那樣,把自己的帽子拉低了一點。
喬治有些鬱悶地盯著池子。他眼睛四周的皮膚被陽光曬得通紅。他突然生氣地說:「我們根本可以直接搭到農場就好,那個混蛋公車司機根本胡說八道!『沿著公路走,一小段路而已,一下就到了。』該死,根本還要六七公里!他只是不想開到農場去。真是該死,有夠懶!說不定他根本不想在索立鎮停車。竟然就這樣把我們踢下車,什麼『一小段路而已』,根本放屁。我敢說,一定不只六七公里。幹他媽的,真是熱到昏頭。」
「喬治?」蘭尼怯怯地看著他。「幹嘛?」
「我們要去哪裡?」
喬治把帽沿往下扯,皺著眉頭看著蘭尼。「你已經忘了,對吧?我又要再跟你說一次嗎?老天啊,你這個腦袋有洞的混蛋!」
「我忘了,」蘭尼小聲地說:「我有要自己不要忘記。我真的有,喬治,我對上帝發誓。」
「好吧,好吧。我再告訴你一次。可是我不是成天沒事幹,跟你說這個那個,然後你又給我忘記,然後我又要再跟你說一次。」
蘭尼說:「我試過要記住,可是沒用。我記得兔子,喬治。」
「兔子個屁,你只記得兔子!現在你給我耳朵張大聽,記下來,這樣我們才不會他媽的又惹上麻煩。你還記得我們坐在霍華德街的水溝裡,還有看那塊公告板的事情嗎?」
蘭尼裂嘴大笑:「當然阿,喬治。那個我記得……可是……然後我們……?我記得有些女孩走過來,你說……你說……」
「管我到底說什麼!你記不記得我們去了莫瑞和雷迪的店,拿了工作箋和公車票?」
「哦,當然,喬治。那個我記得。」他的手迅速伸進外套側邊的口袋。他輕輕地說:「喬治……我的工作箋和車票呢?我一定是弄丟了。」他絕望地低頭看著地面。
「你這笨得要死的混蛋怎麼會有!兩張都在我這裡。你覺得我會讓你自己拿嗎?」
蘭尼鬆了一口氣,開口笑了。「我……我以為我放在外套的口袋。」他的手又伸進口袋裡。喬治眼神銳利地看了他一眼。「你給我從口袋拿什麼鬼東西出來?」
「我的口袋沒有東西。」蘭尼自以為聰明地說。
「我知道你口袋什麼屁也沒有。你拿在手上。你手裡是什麼,你給我藏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真的,喬治。」
「別裝,拿出來。」
蘭尼緊握著手,讓手離喬治遠遠的。「只是一隻老鼠,喬治。」
「一隻老鼠?活的老鼠?」
「呃,只是一隻死老鼠。喬治,不是我弄死的。真的!我只是找到而已。我找到的時候牠就已經死了。」
「給我!」喬治說。
「噢,喬治,給我拿著好不好?」
「交出來!」
蘭尼慢慢攤開手。喬治抓住老鼠,扔了出去,丟到池子另一邊的樹叢裡。「你幹嘛要一隻死老鼠?」
蘭尼說:「我可以一邊走一邊用大拇指摸著玩。」
「老兄,和我走在一起,你可不能摸著老鼠玩。你記得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嗎?」
蘭尼嚇了一跳,然後不好意思地用膝蓋遮住自己的臉。「我又忘記了。」
「老天啊。」喬治無奈地說:「好吧,專心聽好。之前我們不是在北邊的一間農場工作嗎?我們現在要去另一間農場。」
「北邊嗎?」
「雜草鎮。」「哦對。我記得。雜草鎮。」
「我們現在要去的那間農場,離這邊大概四百公尺。我們要去那裡見農場的老闆。現在,聽好了。我會把工作箋給他,你什麼話都不要說。你就好好站著,什麼話都不准說。如果他發現你是一個腦袋有洞的混蛋,我們就沒工作做了。如果他在聽到你說話之前先看到你做事,那我們就一切妥當。這樣清楚嗎?」
「當然,喬治。我懂了。」
「好。那我們去見農場老闆時,你要做什麼?」
「我……我……」蘭尼用力地想,整張臉繃得緊緊的。「我……我不要說話,站著就好。」
「好孩子,很好。你自己唸個兩三遍,這樣才不會忘記。」
蘭尼對自己喃喃唸著:「我不要說話……我不要說話……我不要說話。」
「好,」喬治說:「你也不要給我像在雜草鎮一樣做壞事。」
蘭尼很困惑:「像在雜草鎮一樣?」
「哦,所以你連這個也忘了?也好,我不要提醒你,不然你又來一遍。」
蘭尼好像突然理解什麼似的,整張臉都亮了起來。「他們把我們趕出了雜草鎮。」他驕傲地嚷嚷。
「媽的,把我們趕出去。」喬治厭惡地說道:「好險我們逃得快。他們到處找,但沒抓到。」
蘭尼開心地咯咯笑:「這個我可沒有忘。」
喬治躺在沙地上,雙手交叉放在腦後,蘭尼學他,還抬起頭來看自己有沒有做對。「老天,你真是個大麻煩。」喬治說:「如果你沒有在我屁股後面跟著,我可以過得輕鬆又愉快。我可以多輕鬆,甚至交一個女朋友。」
有一刻,蘭尼安靜了下來,然後他滿懷希望地說:「我們要去農場工作,喬治。」
「沒錯,你懂了。但是我們今天晚上要睡在這裡,我有我的理由。」
天色瞬間暗了下來,整座山谷已經沒有陽光,只剩加比蘭山脈的山頂還亮著。一條水蛇在水池裡滑來溜去,頭抬得高高的,像一座小潛望鏡一樣。蘆葦在水流中略微抽動。在公路遠處,有一個人在大叫,另一個人喊了回去。大梧桐的枝幹在一陣瞬間止息的微風中沙沙作響。
「喬治,為什麼我們不去農場吃飯呢?那裡有晚餐。」喬治翻了個身。「沒有為什麼。我喜歡這裡。明天我們就要工作了。我在路上有看到打穀機,看來又有一堆穀袋等著我們扛,累個半死。今天晚上我要躺在這裡看天空,我喜歡這樣。」
蘭尼跪坐起來,低頭看著喬治。「我們沒有晚餐吃嗎?」
「如果你去撿一些乾掉的樹枝來,我們就會有飯吃啦。我的包包裡有三罐豆子罐頭。你去撿樹枝準備生火。我會給你一根火柴。火升起來,豆子熱了,我們就可以吃了。」
蘭尼說:「我喜歡用番茄醬配豆子。」
「我們沒有番茄醬。快去撿樹枝,別到處亂晃,等一下天就黑了。」
蘭尼笨重地站了起來,消失在灌木叢中。喬治繼續躺著,輕聲吹著口哨。從蘭尼走去的那個方向傳來河水濺起的聲音。喬治停下口哨,豎起耳朵聽。「可憐的混蛋。」他輕聲說,然後重新吹起口哨。
過了一會兒,蘭尼笨重地從灌木叢竄出來,手裡拿著一根細細的柳樹枝。喬治坐起身,粗聲粗氣說:「給我把那隻老鼠拿出來!」
蘭尼比了一個複雜的手勢,裝出一派無辜的模樣。「喬治,什麼老鼠?老鼠不在我身上。」
喬治伸出手。「別裝,交出來,不要想混過去。」
蘭尼猶豫了一下,慢慢退後,不斷回頭看著矮樹叢,好像在想是不是應該乾脆就這麼跑走,讓自己自由。喬治冷冷地說:「你是要給我那隻老鼠,還是我要揍你一頓?」
「我要給你什麼,喬治?」
「該死,不要明知故問。把那隻老鼠給我。」蘭尼無奈地把手伸進口袋裡,有點哽咽地說:「為什麼我不能養老鼠?這隻老鼠又不是別人的。我也沒偷,牠就躺在路邊。」
喬治的手伸得直直的,威嚇著蘭尼。蘭尼就像一隻不想把球傳給主人的小獵犬,慢慢地走近,又退後幾步,又走近。喬治用力彈了一下手指。一聽到聲音,蘭尼立刻把老鼠放到喬治手上。
「我沒做什麼壞事,喬治。我只是摸著玩。」
喬治站起身子,用盡全力把老鼠丟進隱沒在暗夜中的灌木叢裡,然後走到池子邊洗洗手。「你腦袋裡裝什麼渣?你以為我沒看到你褲管是濕的嗎?一看就知道你走過河去找老鼠。」他聽到蘭尼的抽噎聲,轉過身來。「哭得像小嬰兒一樣!該死!像你這樣的大個子,哭個屁!」蘭尼的嘴唇顫抖,淚水盈滿了眼睛。「噢,蘭尼!」喬治把手放到蘭尼的肩膀上。「我不是故意要欺負你才丟掉老鼠的,蘭尼。那隻老鼠不乾淨。而且,你這樣摸著玩,牠已經爛成一團了。你如果找到一隻新的老鼠,我會讓你養一下子。」
蘭尼垂頭喪氣地坐下。「我不知道哪裡還有老鼠。我記得以前有個女士會給我老鼠,她把她有的每一隻都給我。但是那位女士現在不在這裡。」
喬治冷笑了一聲。「一位女士嗎?你連那位女士是誰都想不起來了嗎?那是你的克拉拉姨媽。她最後也不給你老鼠啦。你每次拿到都把牠們玩死。」
蘭尼哀傷地抬頭看著喬治。「牠們好小,」他充滿歉意地說:「我只是摸摸牠們,誰知道牠們就咬我的手,我一痛,就捏捏牠們的頭,然後牠們就死了——牠們好小一隻。我希望我們可以有兔子,喬治。兔子比較大隻一點。」
「兔子個屁!活老鼠都玩死了,還想要兔子?你根本不會養。你的克拉拉姨媽後來給你一隻橡皮老鼠,可是你怎樣都不要。」
蘭尼說:「那不一樣,又不好玩。」
落日餘暉從山頭褪去,山谷變得昏暗,暮色覆上了柳樹和美國梧桐。一條大鯉魚游到池水的表面,吸了氣,然後又神祕地潛入黑暗的水中,只留下漣漪陣陣向外擴散。頭頂上,樹葉又被吹動了起來,柳絮飄落,漂浮在水池上。
「你到底要不要去撿一些樹枝回來?」喬治命令道:「那棵大樹後面有很多被水沖下來的樹枝,現在去給我撿過來。」
蘭尼走到大樹後方,帶回來一堆乾枯的樹葉和小樹枝,扔到舊的灰燼堆上,他來來回回走了好幾趟。天幾乎已經全黑了,從水面上傳來鴿子振翅的聲音。蘭尼堆好後,喬治走向枝葉堆,點燃乾燥的葉子。火焰從樹枝間竄出,燒了起來。喬治解開行囊,拿出三罐豆子。他把豆子一一擺在火堆旁,盡可能地靠近,但沒有真的接觸到火焰。
「這些夠四個人吃了。」喬治說。
蘭尼從火堆旁看著他,緩緩地說:「我喜歡配番茄醬。」
「我們什麼都沒有!」喬治大吼:「你要的東西,都是我們沒有的東西。你幹他媽的該死!如果我自己一個人生活,可以過得多輕鬆!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每天上工下工,沒有麻煩,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情都沒有。到了月底,我可以拿我五十塊錢的薪水,到城裡花個痛快。我可以整個晚上泡在妓院;我可以在隨便一間飯店或餐廳大吃一頓,什麼鬼東西都點。該死,我每個月都可以這樣過,大喝威士忌,到處玩,要打撞球或玩撲克牌,什麼都行!」蘭尼跪了下來,隔著火看著憤怒的喬治,他的臉縮成一團,整個人嚇壞了。「但我現在這個樣子,」喬治生氣地說:「我還要照顧你!你什麼都做不久,而且還害我一起丟工作,我們為了討生活,只好到處跑,但這還不是最慘的,你一直惹麻煩,你一有事,我就要幫你脫身。」他幾乎是用吼的。「你這個婊子生的廢物!我每天都過得緊張兮兮。」然後喬治換了口氣,故意裝作小女孩彼此互相模仿的樣子:「我只是想要摸摸看那個女生的衣服,我只是想摸摸看,像摸小老鼠一樣。幹,她哪裡知道你只是想摸摸看她的衣服?她都已經用力扯開了,你還一直抓著,你以為她是老鼠嗎?她尖叫,每個人都跑出來要抓我們,我們只好在灌溉水溝裡躲一整天,還好最後有摸黑逃走,離開那個地方。一直都是這樣的蠢事,一直都是這樣。我好想把你和一百萬隻老鼠一起關在籠子裡,讓你玩個開心。」突然間,他氣消了。他看著火堆對面蘭尼痛苦的臉,然後愧疚地看著火焰。
第一章
在索立鎮南邊幾公里的地方,薩利納斯河的河道緊貼山邊,水深且綠。水溫並不低,因為陽光把河水曬得暖暖的,在河邊黃色的沙地上濺起亮光,然後河水流進了一個狹窄的池子。河的一側,金色的邊坡愈往高處,愈發崎嶇,最後化作加比蘭山脈的堅石。但在靠山谷的另一邊,河岸成林。每年春天,柳樹新綠,低垂的葉梢撫著雪融後的奔流,葉間偶爾會夾雜一些從山上沖下來的殘枝碎屑;美國梧桐斑駁的白色枝條橫越池上。樹下的沙地覆滿厚厚一層脆裂的落葉,蜥蜴在其中竄梭,窸窣作響。到了傍晚,兔子會從灌木叢間現身,坐在沙地上。夜裡,平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