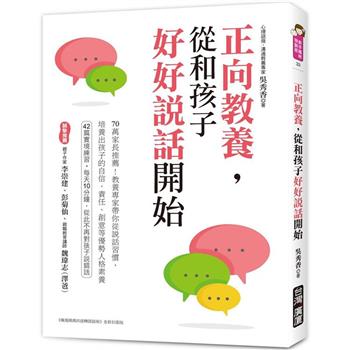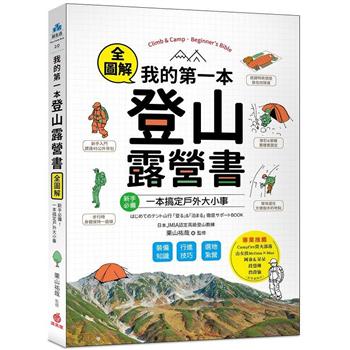一、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節選)
▲「趣味的研究」及「怨而不怒」說
據陳徒手所據的研究資料顯示,賀麟說俞平伯受周作人的影響更大,「俞平伯受胡適影響小,受周作人影響大,講究趣味、閒情,不喜歡讀政治書籍,弄不清為什麼要從俞平伯這兒批判胡適思想。」俞平伯的曾祖俞樾,與章太炎有師生之誼,周作人又曾師從章太炎,由師承及家世來看,周作人與俞平伯之間有天然的淵源,周作人與俞平伯之間又有師生之實,過往甚密。一九一五年秋,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學,時年十六歲,一九一七年,在選擇研究科目時,俞平伯選定小說為研究對象,指導老師為「周作人、胡適和劉半農」,在現存一九二一至一九六四年二人之間的通信中可見,俞平伯皆執弟子禮,以「師」或「先生」稱呼周作人,周作人以「平伯兄」回之。周作人為俞平伯《雜拌兒》作題記時,曾以趣味比喻俞平伯文章的獨特風致,「這風致是屬於中國文學的,是那樣地舊而又這樣地新。」在此基礎上,周作人進一步說明現代散文與明代「新文學家」的相似性,並試圖確認一種既古又新、既能消遣也能傳道聞道的表達方式。基於周作人與俞平伯過往甚密等原因,賀麟得出俞平伯受周作人影響更大的判斷,不難理解。但若深究歷史淵源,不難看出,賀麟對相關歷史事件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及誤判。陳友琴則認為,俞平伯的趣味主義不僅受胡適的影響,也受周作人的影響,「他的思想體系原是胡適、周作人的雙承。」賀麟與陳友琴對俞平伯趣味主義的理解,大體上是基於對個人主義的價值判斷,但二十世紀五○年代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重心在學術典範的更替及其他,即使周作人對俞平伯在散文創作及理論方面有大的影響,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俞平伯與周作人之間,關聯不是很大,周作人對俞平伯的影響,不足以成為當代學術典範更替的導火線。據孫玉蓉編注《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周作人與俞平伯之間的通信,就《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比較少。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胡適在《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周作人寄送《新月》給俞平伯,先借後奉送,俞平伯三月二十五日的回信,僅提及收到《新月》,並未就胡適一文討論,直到一九五三年之後,就《紅樓夢》研究、〈《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一文的刪改問題等,俞平伯與周作人之間有一些交流。這些通信及交往史,基本可以證明,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周作人對俞平伯的影響甚微。胡適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之影響的相關研究,具體可參見宋廣波著(編)《胡適與紅學》、《胡適紅學年譜》、《胡適論紅樓夢》等論著,此處不贅述。
在趣味主義及「怨而不怒」說方面,俞平伯有直接對應胡適的地方,胡適與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的互相呼應,有證可循。如果說胡適主要以趣味論及自然之道「去儒化」,那麼,俞平伯則把趣味主義與文學研究的特質聯繫起來,在審美的層面,進一步推進了趣味論及「怨而不怒」說。胡適考「信」,俞平伯談「美」,兩者推動《紅樓夢》研究在「信」與「美」之間的融合。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俞平伯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九期)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對《紅樓夢辨》待修正之處進行了一些說明,文中自陳其《紅樓夢》研究與胡適、顧頡剛之間的關聯:
「那時最先引動我的興趣的,是適之先生的初稿《紅樓夢考證》,和我以談論函劄相啟發的是頡剛。他們都以考據名癖的,我在他們之間不免漸受這種癖氣的薰陶。」
俞平伯特別強調小說並非信史,以示與索隱派、考證派之間的差別。文學是文學,文學非歷史,文學也不是科學論文,基於這些判斷,俞平伯提出趣味的研究對文藝的特殊意義:
「趣味的研究既沒有特殊的妙法,則何以區別於其他?我說,這種研究其對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你把研究釋為求得固定的知識,則它或本不成為研究,即說是在那邊鬧著頑亦可。我只自己覺得──毫無理由的直覺──這種研究大可存在。我們平心靜氣地仔仔細細地觀察一件事,希望能夠恰當好處(face the fact as it is),不把複綜的密縷看作疏剌剌的幾條,不把圓渾的體看作平薄的片。我們篤信自己觀察的事,但同時瞭解而承認他們應有他們的是處。人各完成其所謂是,而不妨礙他人的。這或者是一般研究的方法所共有,但我以為在今日此地,實有重新提撕一番的必要。作趣味的研究者,能謹守這些陳言更能不貴鹵莽的獲得而尚縝密的尋求;我以為即獨標一同路人,不為過誇。」
俞平伯認為《紅樓夢》是一篇「傑構」,是第一等的文學作品,不宜用猜謎法和考據癖氣去讀,並引胡適所譯奧瑪.開儼(Omar Khayyam, 1048-1131)的詩,希望胡適以小說,而非信史的眼光看《紅樓夢》,「覺得發抒活的趣味比依賴呆的方法和證據大為重要,而淨掃以影射人事為中心觀念的索隱派的『紅學』。」
俞平伯不贊同胡適以考證癖氣讀《紅樓夢》,自認方法論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有大的差異,但也許俞平伯並沒有意識到,他所提倡的「趣味的研究」,實為胡適《紅樓夢》等考證文章中引而不發之論。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胡適的《紅樓夢》研究之趣味論與俞平伯的「趣味的研究」並無本質的差別。兩者實質的差異,在目的及效果等方面,深究起來,無非是功利與非功利之別。胡適所追求的是教育現代化的效果,其趣味論承擔了方法論的功能,胡適以文學的趣味界分現代教育與傳統教化,在胡適這裡,趣味的實驗性及功能性被強化,趣味的審美性被淡化。而俞平伯的「趣味的研究」,雖然也是方法,但他思考的是文學審美、文學本體、文學規律等問題,與趣味的功能性研究相去甚遠。如果說胡適所實驗並試圖推動的是涵蓋內容龐大的典範,胡適在《紅樓夢》等小說上面花費大量的精力考證,目的在建立文學的典範,那麼,俞平伯的「趣味的研究」就是這一大的典範之下的分支內容,亦即大的典範之下的美學研究。兩者之間確實存在分歧,但沒有俞平伯想像得那麼大。
俞平伯認同前人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的論斷──《紅樓夢》就是一部記載閨房兒女的書,與毀謗無關。通過「趣味的研究」,俞平伯得出「怨而不怒」的風格論。此論可佐證,俞平伯與胡適在小說的價值判斷方面,殊途同歸。在俞平伯這裡,小說的個性、風格和價值(即俞平伯所說的態度)為一體,他將《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金瓶梅》並置討論:認為《水滸傳》過於憤慨,是激憤之作,並引張潮《幽夢影》(上卷)的說法,贊同「水滸是一部怒書」;《儒林外史》的牢騷太多;《金瓶梅》是一謗書。俞平伯認定《紅樓夢》是歷史上僅有的「怨而不怒」的小說:「以此看來,怨而不怒的書,以前的小說界上僅有一部《紅樓夢》。怎樣的名貴啊!」如果從風格方面論高低,「積哀思的」要比「含怒氣的」高一些,很難說《水滸傳》、《紅樓夢》的作者在才性上有優劣之分,但兩者風格和動機有差異,《水滸傳》有點過火兼鋒芒過露,《紅樓夢》則偏於溫厚,沒有那麼多的不滿和怒氣:
「哀而不怒的風格,在舊小說中為《紅樓夢》所獨有。究竟這種風格可貴與否,卻是另一問題;雖已如前段所說,但這是我底私見,不敢強天下人來同我底好惡。」
「無論如何,嫚罵刻毒的文字,風格定是卑下的。」
俞平伯稱「嫚罵」為「惡道」,像《廣陵散》這樣的,就不能當其為文學。值得注意的是,俞平伯也意識到:「哀而不怒」或「怨而不怒」說,「積哀思的」與「含怒氣的」之間的高低,皆屬於個人「私見」,「不敢強天下人來同我底好惡」,這些風格論,是屬於主觀色彩比較強烈的範疇,難成定論。
風格論、審美說不同於考據與實證,後者追求客觀追求科學精神,可坐實,可平息無謂之爭,半途而廢的可能性也符合科學規律──不是所有的考證都能得出確鑿無疑的結論,但風格論、審美說歸屬於文學性,文學性是多維度的,可爭議的空間非常大。胡適隱而不發之論,俞平伯視之為文學研究的根本,兩者之關聯,不可謂不大。一九二一年三月,胡適《紅樓夢考證》完成初稿,五月由亞東圖書館發行初版。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在材料方面多有溝通及互助,受顧頡剛努力的「感染」,俞平伯與顧頡剛通信,四月開始作關於《紅樓夢》的「討論文字」,在兩人通信的基礎上,俞平伯完成《紅樓夢辨》,在出版之際,俞平伯請顧頡剛作序,並在引論中自陳受益於顧頡剛的材料及保存信劄:
「頡剛啟發我的地方極多,這是不用說的了。這書有一半材料,大半是從那些信稿中採來的。換句話說,這不是我一人做的,是我和頡剛兩人合做的。」
關於胡適、俞平伯之間的關聯,顧頡剛談得很清楚:
「關於《紅樓夢》作者的歷史,續作者的歷史,本子的歷史,舊紅學的錯誤,適之先生在《紅樓夢考證》上說得很詳了。關於《紅樓夢》的風格,作者的態度,續作者的態度,續作者的依據,……平伯這部書上也說得很詳了。」
俞平伯追求趣味的自在及審美體驗的非功利性,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為文學樹立典範、為教育與學術尋找路徑。胡適趣味論與俞平伯「趣味的研究」之間,有很深的關聯,與其強調其分歧,倒不如強調其互補的關係,在互補的視野下,更能看出胡適《紅樓夢》考證所開創「新紅學」的整體性及延續性。
當歷史發展到需要以批判唯心主義來建構新的典範時,在偶然性與必然性共同作用下,《紅樓夢》研究成為新時代建構學術新典範、思想新典範的首要爭奪領域。批判唯心主義成為歷史必然趨勢的關口,學術界找到爭論空間極大的「趣味」及「怨而不怒」風格論,作為批判運動的突破口,並不是突發奇想、隨意為之的選擇。對趣味論與「怨而不怒」風格論的識別及批判,恰好證明,知識分子群體對歷史進程的參與,並非完全被動捲入,學者們參與歷史進程的主動性與積極性,被八○年代以後的歷史敘事有意無意地忽略。
▲餘論:趣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歷史關聯
二十世紀五○年代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以「現實主義」的方式追認了胡適「趣味論」的典範功能、進而「發掘」出俞平伯「趣味的研究」與胡適趣味論的相通之處。歷史留下來的懸案是:當美學事件被歷史追認為重大的典範更替以及歷史事件時,趣味主義何以被指認為自然主義乃至唯心主義(胡適的趣味論也被指認為是違背現實主義的自然主義)?趣味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歷史關聯何在?趣味主義何以成為五○年代建構「現實主義精神傳統性」的障礙?現實主義原則在理論批判中充當了什麼樣的作用?
從李希凡、藍翎等人的文章可以看出,現實主義原則在識別並批判趣味論及「怨而不怒」風格的過程中,起了關鍵的作用。李希凡、藍翎二人的文章認為:
「俞平伯先生除了引申或說明胡適的結論,並附帶一點『趣味』的『考證』外,自己更無任何獨創性的考證成績可言。」
在〈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附編者按)〉、〈走什麼樣的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新紅學派」的功過在哪裡?〉等文章裡,李希凡、藍翎率先批判俞平伯的「怨而不怒」風格論,稱其脫離「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否定現實主義作品,由此,批判者推及自然主義與唯心主義。鐘洛(袁鷹,本名田鐘洛)根據李希凡、藍翎二人在《文史哲》、《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上發表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的文章,進一步將俞平伯「怨而不怒」風格論歸之於形式主義、唯心主義、主觀主義。通過非此即彼的關聯方式,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建構文學的傳統性、人民性及傾向性。在這種關聯中,「事實」是核心的關鍵字。當然,「從事實出發」,更像一種可以各執其詞的立場。趣味論與「怨而不怒」說是胡適與俞平伯在審美研究方面的殊途同歸,但在如何界定事實方面,有極大的分歧。俞平伯對胡適《紅樓夢》研究的補充與提醒是,小說非信史,史學要面對的事實與文學所逼近的事實有大的區別,由此延伸的價值也是有差異的。批判者則更著重強調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繫,一致將其歸入自然主義及唯心主義的行列。俞平伯在〈《紅樓夢》底風格〉裡,指出《紅樓夢》的「唯一手段」是「寫生」:
「寫生既較逼近於事實,所以從這手段做成的作品所留下的印象感想,亦較為明活深切,即是在文學上的價值亦較高了。」
在批判者看來,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所謂的「逼近於事實」的「寫生」手段,屬於自然主義的「紀實」,並不同於現實主義對現實的積極反映及影響,這種寫生手段,沒有愛憎(不歌頌不批判,所以也不可能有「鬥爭性」):
「現實主義的創作總是通過自己的作品積極地反映現實,這種反映現實的態度本身就滲透著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美學評價。正因為是這樣,他們的作品才能積極地影響現實,喚起人們對現實的愛憎感,並為美好的理想去鬥爭。文學史上從來沒出現過缺乏明確社會見解的作品。所以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及其作者的自然主義評價是和現實主義相違背的。」
從歷史上對「事實」的定義來看,「事實」並非人們想像中的不可爭議的客觀存在,「事實」是不是直接等同於科學與真理,也只是一種難有定論的哲學預設。「事實」的概念本身也存在多義性。只能說,對「事實」的不同界定,會連接不同的價值判斷。正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所說:
「世界是由種種事實組成的:嚴格地說,事實是不能定義的,但是我們可以說事實是使命題真或假的問題,以此來解釋我們所指的是什麼。」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則通過界定原子事實、區分「世界」、「事實」、「事態」來完成對「事實」的定義,這同樣說明「事實」的「難以定義」。學界曾把「事實」區分為「自在事實」、「客觀事實」、「經驗事實」、「理論事實」等,試圖理清楚事實的自在性,以及在人類實踐活動和人類思維影響下「事實」如何得到呈現的不同情況。但「事實」的多義性使得學界很難達到一致的判斷。於是有學者從「事實」的特徵出發,來界定事實的涵義,比如探討其可靠性、不變性、特殊性(不可重複性)等。但這些努力,反而更能說明「事實」具有多義性。對「事實」執有不同看法,就會導致人們對「可知性」及真理有不同的認知。推崇現實主義者,堅信人類實踐活動對現實的反映能力及積極影響能力,堅信能掌握發展規律並相信存在通往絕對真理的可知論。通往絕對真理的可知論,在其相應的歷史時期,天然地具有排他性,「事實」的多義性在特定現實主義原則的框架裡,不被認可。被認定是「不歌頌不批判」的「寫生」手段,被認為不具備鬥爭性的趣味論及「怨而不怒」風格論,因其缺乏傾向性、積極性、鬥爭性(「怒」)而被現實主義否定,並被納入唯心論的範疇加以批判。歷史的發展,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歷史以弔詭之法指認了胡適趣味論與俞平伯「趣味的研究」之間的緊密聯繫。同時,歷史以一種非常規的方式,「證明」了趣味論的重要性。但非常規的方式,反而會遮蔽趣味論本身的重要性。對歷史的回溯,有利於重新思考趣味主義及「怨而不怒」風格論本身的重要性:趣味對教育現代化的意義、經學與文學分離的必要性、文學索隱與文學考證之間的矛盾、文學考證與文學審美之間的互補,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都是對趣味論及「怨而不怒」風格論等歷史話題的續接。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胡適論稿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胡適論稿
在最難實現科學考證的文學領域
以科學實證之法為白話文學樹模範
本書是胡傳吉教授對胡適的文史研究典範論研究,旁及與胡適有關的經史關係及學術史之現代變遷等論題。書中首先從胡適對《紅樓夢》的考證切入,認為胡適並非不懂小說美學,而是在「為文學樹立典範」的前提下,將實證主義、科學驗證難以證明的審美問題暫時擱置,作者以詳實的史料為基礎,論證胡適如何以趣味論「去儒化」,試圖為教育、學術尋找新的路徑。曾樸與胡適對於《孽海花》的論爭,也可視為是新舊文學對於如何「創造中國的新文學」的論辯。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析論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現代白話入「詩」背後的志向──以文學挑戰舊有秩序,藉由所有人都具備學習與理解能力的白話文,推動「人的發現」思潮,樹立現代理念,將人從舊有的等級制度、思維中解脫出來,推動中國的文藝再生。
作者簡介:
胡傳吉
中國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事中國文藝思想史及現代學術史研究,近年主要考察近現代中國文藝思想史、胡適與現代學術史等。著有:《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未完成的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思想史論》、《紅樓四論》、《中國文化思想錄》、《文學的不忍之心》、《中國小說的情與罪》等。
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魯迅研究月刊》、Neohelicon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八十餘篇,另在《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等報刊發表文學及文化評論百萬餘字,兼事水墨漫畫。
章節試閱
一、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節選)
▲「趣味的研究」及「怨而不怒」說
據陳徒手所據的研究資料顯示,賀麟說俞平伯受周作人的影響更大,「俞平伯受胡適影響小,受周作人影響大,講究趣味、閒情,不喜歡讀政治書籍,弄不清為什麼要從俞平伯這兒批判胡適思想。」俞平伯的曾祖俞樾,與章太炎有師生之誼,周作人又曾師從章太炎,由師承及家世來看,周作人與俞平伯之間有天然的淵源,周作人與俞平伯之間又有師生之實,過往甚密。一九一五年秋,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學,時年十六歲,一九一七年,在選擇研究科目時,俞平伯選定小說為研究對...
▲「趣味的研究」及「怨而不怒」說
據陳徒手所據的研究資料顯示,賀麟說俞平伯受周作人的影響更大,「俞平伯受胡適影響小,受周作人影響大,講究趣味、閒情,不喜歡讀政治書籍,弄不清為什麼要從俞平伯這兒批判胡適思想。」俞平伯的曾祖俞樾,與章太炎有師生之誼,周作人又曾師從章太炎,由師承及家世來看,周作人與俞平伯之間有天然的淵源,周作人與俞平伯之間又有師生之實,過往甚密。一九一五年秋,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學,時年十六歲,一九一七年,在選擇研究科目時,俞平伯選定小說為研究對...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
自二○一六年,我開始對「胡適思想批判」學案進行系統研究,後成文約三十萬字,隨讀隨記的過程中,有了這些「補遺」式的思考。
〈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原載《文藝爭鳴》二○二三年第十期。因歷史變遷,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由美學觀念延伸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二十世紀五○年代,李長之、蕭山、譚丕模、鮑正鵠、羅根澤、馮至、吳組緗、李澤厚、霍松林、白盾、田餘慶、戴鎦齡、塗樹平、詹安泰、馮沅君、胡念貽、陳煒謨、趙衛謨、郭預衡、楊招棣、陳友琴等文史學者,不約而同地將趣味主義置於現實主義的對立面。由歷史...
自二○一六年,我開始對「胡適思想批判」學案進行系統研究,後成文約三十萬字,隨讀隨記的過程中,有了這些「補遺」式的思考。
〈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原載《文藝爭鳴》二○二三年第十期。因歷史變遷,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由美學觀念延伸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二十世紀五○年代,李長之、蕭山、譚丕模、鮑正鵠、羅根澤、馮至、吳組緗、李澤厚、霍松林、白盾、田餘慶、戴鎦齡、塗樹平、詹安泰、馮沅君、胡念貽、陳煒謨、趙衛謨、郭預衡、楊招棣、陳友琴等文史學者,不約而同地將趣味主義置於現實主義的對立面。由歷史...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一、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
「作為方法」的《紅樓夢》考證
「去儒化」與文學教育的現代化
「趣味的研究」及「怨而不怒」說
餘論:趣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歷史關聯
二、曾樸與胡適的論爭──「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考辨
胡適嗜讀小說與為白話文學樹模範的關聯
《孽海花》之爭
論翻譯:「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之辯
三、人的問題與科學主義──論〈文學改良芻議〉與「實驗主義」
情與力對人的意義
科學精神與「創造的智慧」
四、現代白話詩與「人的發現」
附錄:經史分離...
一、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
「作為方法」的《紅樓夢》考證
「去儒化」與文學教育的現代化
「趣味的研究」及「怨而不怒」說
餘論:趣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歷史關聯
二、曾樸與胡適的論爭──「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考辨
胡適嗜讀小說與為白話文學樹模範的關聯
《孽海花》之爭
論翻譯:「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之辯
三、人的問題與科學主義──論〈文學改良芻議〉與「實驗主義」
情與力對人的意義
科學精神與「創造的智慧」
四、現代白話詩與「人的發現」
附錄:經史分離...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