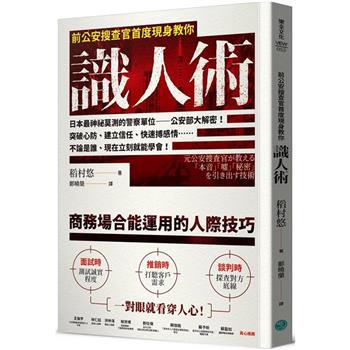本書為青年詩人炎石首次較完整的作品集結,收錄其2011年至2022年間新詩作品。詩人的夜鶯之喉舌彈北國詩人少有的呢喃細密之音,對語音之美深入味蕾的細咂,附麗其修遠之心,並借助古典資源與當代景觀並置,形成的獨一無二的嗓音和抒情性,足以在當下詩歌版圖中蓬勃一片沃土。近來的詩作,則發願於古老詩學旨歸:詩可以怨。
詩人奉「屏體」為餘生新詩之正體,並以「即怨」臨摹古典抒情之關懷,淹留於杜甫、卞之琳的磁場和氣場,精準和迅速地對表當代政治時間。與此同時,走鋼絲般迤邐地「朝著語言危險的風景」深入又深入,展現了絕美的風姿和風度。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詩歌是撫慰人心最好的工具,那麼炎石詩歌既美且悲的韻致,極好地氤氳並擴大了詩作為詩的魅力。其不被評論之眼細觀的處境,恰是其詩歌複雜性的明證。細忖裸奔之人的速度與激情,實需庸俗之眼閉而再睜尚回神於恍惚之間。
本書特色
★「陸詩叢」精選中國最新世代且最具代表性的詩人,集結各方刊物與學院的高度認可,眾所期待,隆重推出。
★獨創「屏體詩」,以每行十一字為限,在白話文鬆散特性下,保有古詩格律之美,可視為古典詩在現代的延續。
★作者炎石啟蒙恩師、中國知名詩人黃梵,特別撰寫專序,見證詩人的成長與蛻變。
各界推薦
黃梵(詩人、小說家)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冠狀的春:炎石詩選2011-2022 (電子書)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冠狀的春:炎石詩選2011-2022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炎石
一位詩的原教旨主義者。九○年生於陝西山陽,○九年赴南京讀書,一○年創辦進退詩社,並主編《進退》詩刊。一二年發起「南方進步詩人獎」,首開「同代人觀測同代人」之視角。一七年定居西安,二○年發起「新秦詩」寫作,並主持同名新詩民刊。二二年發起「一代人寫一代人」活動,邀請兩百位詩人以顧城之眼,對疫情下中國展開新一輪凝視。隨著AI音樂技術興起,發起「新詩無限音樂合作社」,致力於推動新詩音樂化。
主編簡介
楊小濱
詩人,藝術家,評論家。耶魯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政治大學教授,《兩岸詩》總編輯。曾獲《現代詩》第一本詩集獎、納吉.阿曼國際文學獎、胡適詩歌獎等。著有詩集《穿越陽光地帶》、《景色與情節》、《為女太陽乾杯》、《楊小濱詩X3》(《女世界》、《多談點主義》、《指南錄.自修課》)、《到海巢去》、《洗澡課》,論著《否定的美學》、《歷史與修辭》、《中國後現代》、《語言的放逐》、《迷宮.雜耍.亂彈》、《無調性文化瞬間》、《感性的形式》、《欲望與絕爽》,曾主編《中國當代詩叢》。近年在兩岸及北美舉辦藝術展,並出版觀念藝術與抽象詩集《蹤跡與塗抹:後攝影主義》。
茱萸
哲學博士。詩人,青年學者,批評家。現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現代漢詩研究與當代文學批評。著有《花神引》、《爐端諧律》、《儀式的焦唇》、《漿果與流轉之詩》等詩集、論著及編選集多種。獲過多項頗有影響力的文學獎以及美國亨利.露斯基金會中國詩人譯介項目獎金,曾受邀出席台灣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美國佛蒙特中心駐留計劃及韓國第三屆中韓詩人論壇等文學活動。部分詩作被譯為英、日、俄、韓及西班牙語;入選過《中國新詩百年大典》、《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詩歌卷》、《現代漢詩110首》等重要選本。
炎石
一位詩的原教旨主義者。九○年生於陝西山陽,○九年赴南京讀書,一○年創辦進退詩社,並主編《進退》詩刊。一二年發起「南方進步詩人獎」,首開「同代人觀測同代人」之視角。一七年定居西安,二○年發起「新秦詩」寫作,並主持同名新詩民刊。二二年發起「一代人寫一代人」活動,邀請兩百位詩人以顧城之眼,對疫情下中國展開新一輪凝視。隨著AI音樂技術興起,發起「新詩無限音樂合作社」,致力於推動新詩音樂化。
主編簡介
楊小濱
詩人,藝術家,評論家。耶魯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政治大學教授,《兩岸詩》總編輯。曾獲《現代詩》第一本詩集獎、納吉.阿曼國際文學獎、胡適詩歌獎等。著有詩集《穿越陽光地帶》、《景色與情節》、《為女太陽乾杯》、《楊小濱詩X3》(《女世界》、《多談點主義》、《指南錄.自修課》)、《到海巢去》、《洗澡課》,論著《否定的美學》、《歷史與修辭》、《中國後現代》、《語言的放逐》、《迷宮.雜耍.亂彈》、《無調性文化瞬間》、《感性的形式》、《欲望與絕爽》,曾主編《中國當代詩叢》。近年在兩岸及北美舉辦藝術展,並出版觀念藝術與抽象詩集《蹤跡與塗抹:後攝影主義》。
茱萸
哲學博士。詩人,青年學者,批評家。現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現代漢詩研究與當代文學批評。著有《花神引》、《爐端諧律》、《儀式的焦唇》、《漿果與流轉之詩》等詩集、論著及編選集多種。獲過多項頗有影響力的文學獎以及美國亨利.露斯基金會中國詩人譯介項目獎金,曾受邀出席台灣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美國佛蒙特中心駐留計劃及韓國第三屆中韓詩人論壇等文學活動。部分詩作被譯為英、日、俄、韓及西班牙語;入選過《中國新詩百年大典》、《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詩歌卷》、《現代漢詩110首》等重要選本。
目錄
【序】沒有魔術可以掏出/黃梵
【輯一】蝴蝶
有趣的是
西瓜上市
蝶戀花
鏡子
縫紉機
好日子
乒乓球
屋簷上的冰
早餐
洋瓷碗
一棵桑樹
蝴蝶
人籟
往事
水裡做什麼
布簾
表白
午後
秋夜
【輯二】述夢
無題.其一
無題.其二
憶山蟹並寄江西吳臨安
某日與唐和才遊興慶宮公園
再遊興慶宮公園
述夢
感懷
感遇
故人入我夢中
在流徽榭
一天
又一天
江南暮春
暮春遣懷
那飛的是浮萍
紅蘋果
傍晚
春去了
第八套廣播體操
溪水邊
散步
幽會
春登
【輯三】詠懷
詠懷.其一
詠懷.其二
詠懷.其三
詠懷.其四
詠懷.其五
詠懷.其六
詠懷.其七
詠懷.其八
詠懷.其九
詠懷.其十
詠懷.其十一
詠懷.其十二
詠懷.其十三
詠懷.其十四
詠懷.其十五
詠懷.其十六
詠懷.其十七
詠懷.其十八
詠懷.其十九
【輯四】變奏
夠一夢
送張晚禾去北京
夜奔記
從理工大漫步至午門
一張不肯開口的雲
秋夜裡
交通史
霧霾詩
友誼河
圓明園
晚歸的路上
離別的霧
魚的變奏
一個短篇
熱風
回憶的兩公里
現代雪景圖
自然減速帶
踏莎行
值班作
清平樂
再遊玄武湖公園
新年詩
為一瓶七兩半而作
相遇
一位首都詩人的葬禮
蘭壽
【輯五】別裁
遊戲別裁.孤獨的試煉
遊戲別裁.瘋狂的戴夫
杜詩別裁.登高之後
杜詩別裁.望嶽別裁
杜詩別裁.登高別裁
杜詩別裁.葛洪別裁
北京慢.北海公園
北京慢.南鑼鼓巷
北京慢.夜訪魯院
北京慢.遊什剎海
北京慢.東四胡同
北京慢.北海鴛鴦
塔元雜詩.其一
塔元雜詩.其二
塔元雜詩.其三
塔元雜詩.其四
塔元雜詩.其五
塔元雜詩.其六
塔元雜詩.其七
塔元雜詩.其八
【輯六】屏體
擬距離的組織
遊園
四月
冠狀的春
雲中飲
幽州台下歌
憶遊東海
憶遊湖州
憶遊廈門
論詩.其一
論詩.其二
河堤路上觀落日作
七夕夜作
喜報
口琴
登清涼山
握流水
灞河夜行,贈陳東東
悼一位長者
【輯七】即怨
為一位通勤青年而作
為一位韭菜青年而作
為一位負極青年而作
為一位歸零老人而作
為一位躺平青年而作
為廣場舞大媽而作
出上海記
碼上還鄉
碼上出站
取現難
為足療女而作
西北有高樓
為貴陽大巴事而作
擬李金髮棄婦詩
為蘭州三歲孩童而作
即怨.其一
即怨.其二
即怨.其三
即怨.其四
【附】
後記
我的新詩師
【輯一】蝴蝶
有趣的是
西瓜上市
蝶戀花
鏡子
縫紉機
好日子
乒乓球
屋簷上的冰
早餐
洋瓷碗
一棵桑樹
蝴蝶
人籟
往事
水裡做什麼
布簾
表白
午後
秋夜
【輯二】述夢
無題.其一
無題.其二
憶山蟹並寄江西吳臨安
某日與唐和才遊興慶宮公園
再遊興慶宮公園
述夢
感懷
感遇
故人入我夢中
在流徽榭
一天
又一天
江南暮春
暮春遣懷
那飛的是浮萍
紅蘋果
傍晚
春去了
第八套廣播體操
溪水邊
散步
幽會
春登
【輯三】詠懷
詠懷.其一
詠懷.其二
詠懷.其三
詠懷.其四
詠懷.其五
詠懷.其六
詠懷.其七
詠懷.其八
詠懷.其九
詠懷.其十
詠懷.其十一
詠懷.其十二
詠懷.其十三
詠懷.其十四
詠懷.其十五
詠懷.其十六
詠懷.其十七
詠懷.其十八
詠懷.其十九
【輯四】變奏
夠一夢
送張晚禾去北京
夜奔記
從理工大漫步至午門
一張不肯開口的雲
秋夜裡
交通史
霧霾詩
友誼河
圓明園
晚歸的路上
離別的霧
魚的變奏
一個短篇
熱風
回憶的兩公里
現代雪景圖
自然減速帶
踏莎行
值班作
清平樂
再遊玄武湖公園
新年詩
為一瓶七兩半而作
相遇
一位首都詩人的葬禮
蘭壽
【輯五】別裁
遊戲別裁.孤獨的試煉
遊戲別裁.瘋狂的戴夫
杜詩別裁.登高之後
杜詩別裁.望嶽別裁
杜詩別裁.登高別裁
杜詩別裁.葛洪別裁
北京慢.北海公園
北京慢.南鑼鼓巷
北京慢.夜訪魯院
北京慢.遊什剎海
北京慢.東四胡同
北京慢.北海鴛鴦
塔元雜詩.其一
塔元雜詩.其二
塔元雜詩.其三
塔元雜詩.其四
塔元雜詩.其五
塔元雜詩.其六
塔元雜詩.其七
塔元雜詩.其八
【輯六】屏體
擬距離的組織
遊園
四月
冠狀的春
雲中飲
幽州台下歌
憶遊東海
憶遊湖州
憶遊廈門
論詩.其一
論詩.其二
河堤路上觀落日作
七夕夜作
喜報
口琴
登清涼山
握流水
灞河夜行,贈陳東東
悼一位長者
【輯七】即怨
為一位通勤青年而作
為一位韭菜青年而作
為一位負極青年而作
為一位歸零老人而作
為一位躺平青年而作
為廣場舞大媽而作
出上海記
碼上還鄉
碼上出站
取現難
為足療女而作
西北有高樓
為貴陽大巴事而作
擬李金髮棄婦詩
為蘭州三歲孩童而作
即怨.其一
即怨.其二
即怨.其三
即怨.其四
【附】
後記
我的新詩師
序
序
沒有魔術可以掏出
黃梵(詩人、小說家)
我記憶中十多年前的炎石,可以說,已經成長為現在的炎石,找到了詩和言說的祕密。那條從教室到地鐵站的道路,他稱為「詩之路」,被他一次次鋪滿提問,這些提問也促我思考、回答,或埋下研究之心。記得有一陣子,他只讀古詩,理由是,相對新人,他更傾心古人。他的疑惑並非孤立,歌德曾抱怨「當代」作家缺乏高尚的人格。黃燦然說,阿諾德也如是埋怨當代作家。炎石不過想避開當代作家的弊端―重智慧輕人格―獲得正本清源的洗滌。我為他的這一做法,心急如焚。古代已不可複現,想置身潔淨的環境,終是幻想。唯完善的人格能從不潔中長成,方能證明它的力量。至於智慧,哦,當代智慧摻合了太多聰明,我倒體會到炎石的老實和執拗,這份難得,容我稍後來解。
輯三的「詠懷」篇,可視為他對古人一以貫之的景仰,只是,這份景仰也出自他的現代生活經驗。「我要去喝酒啦!一個人又何妨/明月裡多少老朋友,秋風中多少舊相識」、「讓我們學過的詩詞/以及寫過的詩句/在對影的別景裡觸碰出露痕」、「他看見壯年正向他揮手告別。他的傷心/或許只有方向盤看得見」。他喝的何嘗不是古人的酒,哪怕是當代的酒,也被他喝出了古風。難怪寂寞時,他會與古人比賽憂愁。他年輕時的困頓也在愁字,先是從古書讀出愁,後是從生活歷練出愁。愁是古人疏離紅塵的大道,被年輕的炎石習之,終成為他新詩的底色。現在生活的愁既讓他看到,人作為的不易,也讓他看到,其作為的珍貴和愧疚,「一生艱苦,原只為磨一粒珍珠」、「西西弗斯的巨石,已越推越小」、「等一生劇終了,才獻出那珍珠」(〈杜詩別裁.登高別裁〉)。命運是因為力所不逮嗎?還是無法選擇的選擇?「兩個天賦,執著把一個人分開。//沒有成為一名化學家我也愧疚」(〈杜詩別裁.葛洪別裁〉),他將之歸為天賦,實則是兩個自我的博弈。終有落敗的一方,讓愁是註定的。與愁一起承自古代的「古老」,還成為他一些詩歌必不可少的形式。比如,他近年提倡的屏體詩。「當摩登的上海也恍若荒原,/伸出去的長竿比流水更遠」(〈四月〉),「酒有限卻依然高於海平面,/肚有容快去撐一艘萬里船。」(〈雲中飲〉),「從此遠行在隨身攜帶的海,/卻頻頻駛入格子間而擱淺。」(〈憶遊廈門〉)。
他為屏體詩選擇每行十一字,等於承認古詩奇數言的優勢,同時又體恤白話的鬆散。十一字令他既受限,又擁有受限中的自由,將才能置於最易登峰的悖論境地。他加給現代詩的整飭,與內容的不羈,堪稱鮮明對照。當他說「將海灌入胸懷」、「在隨身攜帶的海」時,讓我想到了詩讓浪漫派獲得的誇張「特權」。比如,雪萊在《西風頌》中說,「它忙把海水劈成兩半,為你開道」(王佐良譯),李白在〈秋浦歌〉中說,「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我們對雪萊和李白浪漫誇張的信賴,源自格律詩形式的護駕。由此可以看清,炎石屏體詩的處境。他提供的整飭句式,可以讓他有一定的浪漫誇張「特權」,「海終有一天會被我填滿嗎?」(〈憶遊東海〉),但整飭帶來的音樂形式,終不如平仄等起伏,讓人容易銘記。所以,他在屏體詩中仍需把類似浪漫派的誇張,轉變成也適合散文的現代詩誇張,比如,「等待著南瓜車把青春送還」(〈遊園〉),「從瓶中解封一個又一個海」、「酒有限卻依然高於海平面」(〈雲中飲〉),「雨後荷花仍赴碧水裡裁衣」(〈憶遊湖州〉)等。屏體詩可以視為古代在現代的延續,整飭令詩人可以獲得浪漫「特權」,而未經規劃的起伏、節奏等,又將詩人推向現代,去尋求更耐散文化的詩意。我以為,炎石諳悉形式化的風險,在現代詩的草創期,任何徹底形式化的努力,都會遭遇類似新月派的滑鐵盧。屏體詩既仰慕古代格律,又拒絕徹底格律化,可謂現階段的智慧之選。炎石以屏體詩來進行新詩創作,誰能說未來不會結出碩果呢?
記得多年前胡弦曾托我,勸炎石留在《揚子江詩刊》,但他的選擇,讓我們都吃驚不小。他只在《揚子江詩刊》和江蘇文藝出版社作短暫停留,就選擇幹空調專業老本行,做一名業餘寫詩的工程師。我問過他緣由,他的回答頗為老實,認定詩人應該先有生活後有詩。言外之意,他還需要投身更具挑戰的生存湍流。他的老實還體現在,對古代人格、道德的實踐,於一個現代詩人,極其難能可貴。他對妻子的愛超越了家常裡短,似乎在大學相戀的開頭,情感裡就藏著倫理的理想,並賦予它知行合一的信念。但大學讀古書的執拗,令他更傾心易於落敗的傳統。整本詩集的感受方式,包括傾心短制、杜甫情結等,皆彌散著現代生活中的古代氣息。古代人格的思想烙印,因他老實巴交的踐行,規定了他的寫作命運,故他常稱自己是一位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被內心的「人格」之風,刮至邊緣,意外擺脫了一切附和之需,獲得生活和詩的巨大專注力,這何嘗不是邊緣的報償?
記得十幾年前,他曾帶著七客、吳臨安、獨孤長沙等「進退」成員,到我辦公室交流。之後,我為他們的《進退集》寫過短序,有一段話同樣適合炎石,「進退所有成員都受到中國古詩、典籍和西方現代詩的雙重誘惑,他們都堅決拋棄晦澀的詩風,令古代明晰的意象、交遊和超驗言說脫羈而出,同時也避免了用白話回到古詩的危險;他們不理會現代主義中過分私密的密碼體系,從而為中國詩創造出更生動靈巧的話語模式,為世界範圍的後現代詩風注入新的中國要素。」很難想像,炎石們用俠士的錚錚鐵骨,重新定義了現代頹廢。他曾在教室燒詩,在鐘山裸奔,他達成了常人難以理解的內心平衡,現代和古代的平衡。這是現代的疑惑,既在順從現代經驗,又在尋求古代根源。「這水是從黃浦江裡來的吧/那茶杯來自杜尚,那黑鐵壺//來自日本?」(〈詠懷.其十三〉),黃浦江和黑鐵壺都在提示歷史,提示仍在消磨著我們的古代、近代,而杜尚,是很多人心裡的現代夢,當這些都合為一體,那種期待會發生什麼的心理,卻被炎石的詩抑制。他說,「我的杯透明/沒有一點兒魔術可以掏出」(〈詠懷.其十三〉)。這就是炎石老實的地方,他不認為我們能改變什麼,哪怕掏出騙人的魔術,他也不幹。這何嘗不是他的詩學?「你可曾想過新詩也是古詩?/此刻我閱讀彷彿你已死去。」(〈論詩.其一〉)毀壞德性的現代生活,當代全球的民族主義生態,不正如維科所預言的那樣,在積蓄回到古代的力量麼?他作為詩人的直覺表達,難說沒有回答「為什麼」!「為什麼蝴蝶飛過沒有聲音?/它就這樣飛來飛去了二十三年,/沒有說一個『喂』字」(〈蝴蝶〉)。
序成之際,得知他喜得貴子,可謂好事成雙。兒子和詩集,皆為他的愛所育成,可視為他生活的雙子星。
2024年5月9日
於南京江寧
我的新詩師
炎石
○九年我去南京一所理工科學校念書,沒多久我瞭解到竟還有文藝選修課這樣的事,就抱著中學時代熾熱至今的愛好,選修了一門關於西方藝術的課程。說來這是巧合,卻更是緣分,在這門一週一節,並總是在晚上展開的課上,我從山城的唐詩宋詞鑒賞辭典第一次走進西方藝術史。我是在這門選修課的中期,才知道他(黃梵老師)是一位詩人的。那時我苦於沒有詩的夥伴,常常在宿舍樓外一個網吧,與素不謀面的青年們聊著。終於一次課後,我鼓足了勇氣,拿著幾頁新列印的詩稿,等簇擁的學生都稀疏了以後,才遞過去並緊張地說道,「老師,我也寫詩,這是我的一些作品,請您指導」。
又一週課後的九點鐘,我踏上了那條日後頻繁與他送往的「詩之路」,即從四工教學樓經圖書館到校訓碑,沿著和平園前的梧桐道直抵二號門,門外不遠就是名為「孝陵衛」的地鐵站。這段大約20分鐘的路程,一步步深化著我們的師生情誼。在逸夫樓暗香浮動的晚春,他說他認真讀過我的詩,並認為很有潛力,但要從事詩歌寫作,筆名還得好好考慮,這對一位詩人來說很重要,還講起他從「黃帆」改為「黃梵」的故事。
再一週在走得更遠的一個地點,即藝文館前那片著名的水杉林前,他對我取的兩個筆名都不滿意,並建議我可以叫「炎石」,「炎」是你名,而「石」符合你的性格,「炎石」就很不錯。如今看來,確實很不錯,如同被施了魔法,這筆名統攝住了我。二○年初,我又著意重啟寫作,擬換個新名與過去告別,但試用了一陣還是作罷。
與黃老師結緣後,我又持續選了他多門課程,直到無法再選。現在回顧過去十數年的寫作,我現在寫詩之所以如是,與黃老師的關係很大。他有一首〈中年〉我印象深刻,我幾乎是讀著〈中年〉來到中年的,正是這一首詩的詩法影響了我,我始知詩可以這樣作而非那樣。後來我陸續受到柏樺、飛廉,以及個人新詩溯源工作啟動後,直接受卞之琳與杜甫的影響,但我的詩仍隱含著黃詩味道的。我一直想談談他的詩(我已寫得越來越有資格去談),但因他是我的新詩師,我總在等一個合適的時刻。我會為他的詩被低估而感到不平,但他耐受得住並不此為意,同時又小說又教詩歌課的,使得我的詩弟詩妹也滿天下了。
一四年畢業後,因為要穩定工作與生活,我基本剎住了新詩的寫作。一七年從南京灰溜溜地離開,也未第一時間告訴他。在我不再陪伴他「詩之路」後的很多年,我們之間僅有的幾次聯繫,一次在我去安康的綠皮火車上,他問我近來寫作如何,那時我寫得很少羞慚無言;還有一次就是「屏體詩」寫成後,我再次像學生時代那般,每有新作就發送給他指導,這一次他高興甚至有些激動,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分開後十年裡,僅有的一次見面,還是在去年我到南京開會,再次去他已位於江寧的新家,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師母,我跟往常一樣話說得很少。正午時分頂著南京的暑日,我陪他再次走了段短短的「詩之路」,在碰到返程來接的師母後,一腳油門我們就到了那張鋪滿美食的餐桌上。後來,我每月都會去南京開會,但已沒有去拜訪他的念頭,那個訥於言的青年如今已是訥於言的中年,但是一想到那些可以在詩裡夷平的高樓,就想著我們師生相見在詩裡,會更從容、更親切一些。
黃老師曾在《南方週末》開設過專欄,寫過一篇〈校園詩人〉的文章,裡面有這樣一句話,「雖然炎石認為他寫詩考慮東方,始於我的《東方集》,但我覺得他會比我走得更遠、更扎實,因為他比我更死心眼。死心眼甚至影響了他對前途的抉擇。」我的寫作和黃老師的淵源,如果我不提這段經歷,很多人是並看不出來的,但飲水思源我還是要提的,這淵源不止是詩本身的,更是我們對於詩這件事所持有的態度上的。
2023年6月20日
沒有魔術可以掏出
黃梵(詩人、小說家)
我記憶中十多年前的炎石,可以說,已經成長為現在的炎石,找到了詩和言說的祕密。那條從教室到地鐵站的道路,他稱為「詩之路」,被他一次次鋪滿提問,這些提問也促我思考、回答,或埋下研究之心。記得有一陣子,他只讀古詩,理由是,相對新人,他更傾心古人。他的疑惑並非孤立,歌德曾抱怨「當代」作家缺乏高尚的人格。黃燦然說,阿諾德也如是埋怨當代作家。炎石不過想避開當代作家的弊端―重智慧輕人格―獲得正本清源的洗滌。我為他的這一做法,心急如焚。古代已不可複現,想置身潔淨的環境,終是幻想。唯完善的人格能從不潔中長成,方能證明它的力量。至於智慧,哦,當代智慧摻合了太多聰明,我倒體會到炎石的老實和執拗,這份難得,容我稍後來解。
輯三的「詠懷」篇,可視為他對古人一以貫之的景仰,只是,這份景仰也出自他的現代生活經驗。「我要去喝酒啦!一個人又何妨/明月裡多少老朋友,秋風中多少舊相識」、「讓我們學過的詩詞/以及寫過的詩句/在對影的別景裡觸碰出露痕」、「他看見壯年正向他揮手告別。他的傷心/或許只有方向盤看得見」。他喝的何嘗不是古人的酒,哪怕是當代的酒,也被他喝出了古風。難怪寂寞時,他會與古人比賽憂愁。他年輕時的困頓也在愁字,先是從古書讀出愁,後是從生活歷練出愁。愁是古人疏離紅塵的大道,被年輕的炎石習之,終成為他新詩的底色。現在生活的愁既讓他看到,人作為的不易,也讓他看到,其作為的珍貴和愧疚,「一生艱苦,原只為磨一粒珍珠」、「西西弗斯的巨石,已越推越小」、「等一生劇終了,才獻出那珍珠」(〈杜詩別裁.登高別裁〉)。命運是因為力所不逮嗎?還是無法選擇的選擇?「兩個天賦,執著把一個人分開。//沒有成為一名化學家我也愧疚」(〈杜詩別裁.葛洪別裁〉),他將之歸為天賦,實則是兩個自我的博弈。終有落敗的一方,讓愁是註定的。與愁一起承自古代的「古老」,還成為他一些詩歌必不可少的形式。比如,他近年提倡的屏體詩。「當摩登的上海也恍若荒原,/伸出去的長竿比流水更遠」(〈四月〉),「酒有限卻依然高於海平面,/肚有容快去撐一艘萬里船。」(〈雲中飲〉),「從此遠行在隨身攜帶的海,/卻頻頻駛入格子間而擱淺。」(〈憶遊廈門〉)。
他為屏體詩選擇每行十一字,等於承認古詩奇數言的優勢,同時又體恤白話的鬆散。十一字令他既受限,又擁有受限中的自由,將才能置於最易登峰的悖論境地。他加給現代詩的整飭,與內容的不羈,堪稱鮮明對照。當他說「將海灌入胸懷」、「在隨身攜帶的海」時,讓我想到了詩讓浪漫派獲得的誇張「特權」。比如,雪萊在《西風頌》中說,「它忙把海水劈成兩半,為你開道」(王佐良譯),李白在〈秋浦歌〉中說,「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我們對雪萊和李白浪漫誇張的信賴,源自格律詩形式的護駕。由此可以看清,炎石屏體詩的處境。他提供的整飭句式,可以讓他有一定的浪漫誇張「特權」,「海終有一天會被我填滿嗎?」(〈憶遊東海〉),但整飭帶來的音樂形式,終不如平仄等起伏,讓人容易銘記。所以,他在屏體詩中仍需把類似浪漫派的誇張,轉變成也適合散文的現代詩誇張,比如,「等待著南瓜車把青春送還」(〈遊園〉),「從瓶中解封一個又一個海」、「酒有限卻依然高於海平面」(〈雲中飲〉),「雨後荷花仍赴碧水裡裁衣」(〈憶遊湖州〉)等。屏體詩可以視為古代在現代的延續,整飭令詩人可以獲得浪漫「特權」,而未經規劃的起伏、節奏等,又將詩人推向現代,去尋求更耐散文化的詩意。我以為,炎石諳悉形式化的風險,在現代詩的草創期,任何徹底形式化的努力,都會遭遇類似新月派的滑鐵盧。屏體詩既仰慕古代格律,又拒絕徹底格律化,可謂現階段的智慧之選。炎石以屏體詩來進行新詩創作,誰能說未來不會結出碩果呢?
記得多年前胡弦曾托我,勸炎石留在《揚子江詩刊》,但他的選擇,讓我們都吃驚不小。他只在《揚子江詩刊》和江蘇文藝出版社作短暫停留,就選擇幹空調專業老本行,做一名業餘寫詩的工程師。我問過他緣由,他的回答頗為老實,認定詩人應該先有生活後有詩。言外之意,他還需要投身更具挑戰的生存湍流。他的老實還體現在,對古代人格、道德的實踐,於一個現代詩人,極其難能可貴。他對妻子的愛超越了家常裡短,似乎在大學相戀的開頭,情感裡就藏著倫理的理想,並賦予它知行合一的信念。但大學讀古書的執拗,令他更傾心易於落敗的傳統。整本詩集的感受方式,包括傾心短制、杜甫情結等,皆彌散著現代生活中的古代氣息。古代人格的思想烙印,因他老實巴交的踐行,規定了他的寫作命運,故他常稱自己是一位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被內心的「人格」之風,刮至邊緣,意外擺脫了一切附和之需,獲得生活和詩的巨大專注力,這何嘗不是邊緣的報償?
記得十幾年前,他曾帶著七客、吳臨安、獨孤長沙等「進退」成員,到我辦公室交流。之後,我為他們的《進退集》寫過短序,有一段話同樣適合炎石,「進退所有成員都受到中國古詩、典籍和西方現代詩的雙重誘惑,他們都堅決拋棄晦澀的詩風,令古代明晰的意象、交遊和超驗言說脫羈而出,同時也避免了用白話回到古詩的危險;他們不理會現代主義中過分私密的密碼體系,從而為中國詩創造出更生動靈巧的話語模式,為世界範圍的後現代詩風注入新的中國要素。」很難想像,炎石們用俠士的錚錚鐵骨,重新定義了現代頹廢。他曾在教室燒詩,在鐘山裸奔,他達成了常人難以理解的內心平衡,現代和古代的平衡。這是現代的疑惑,既在順從現代經驗,又在尋求古代根源。「這水是從黃浦江裡來的吧/那茶杯來自杜尚,那黑鐵壺//來自日本?」(〈詠懷.其十三〉),黃浦江和黑鐵壺都在提示歷史,提示仍在消磨著我們的古代、近代,而杜尚,是很多人心裡的現代夢,當這些都合為一體,那種期待會發生什麼的心理,卻被炎石的詩抑制。他說,「我的杯透明/沒有一點兒魔術可以掏出」(〈詠懷.其十三〉)。這就是炎石老實的地方,他不認為我們能改變什麼,哪怕掏出騙人的魔術,他也不幹。這何嘗不是他的詩學?「你可曾想過新詩也是古詩?/此刻我閱讀彷彿你已死去。」(〈論詩.其一〉)毀壞德性的現代生活,當代全球的民族主義生態,不正如維科所預言的那樣,在積蓄回到古代的力量麼?他作為詩人的直覺表達,難說沒有回答「為什麼」!「為什麼蝴蝶飛過沒有聲音?/它就這樣飛來飛去了二十三年,/沒有說一個『喂』字」(〈蝴蝶〉)。
序成之際,得知他喜得貴子,可謂好事成雙。兒子和詩集,皆為他的愛所育成,可視為他生活的雙子星。
2024年5月9日
於南京江寧
我的新詩師
炎石
○九年我去南京一所理工科學校念書,沒多久我瞭解到竟還有文藝選修課這樣的事,就抱著中學時代熾熱至今的愛好,選修了一門關於西方藝術的課程。說來這是巧合,卻更是緣分,在這門一週一節,並總是在晚上展開的課上,我從山城的唐詩宋詞鑒賞辭典第一次走進西方藝術史。我是在這門選修課的中期,才知道他(黃梵老師)是一位詩人的。那時我苦於沒有詩的夥伴,常常在宿舍樓外一個網吧,與素不謀面的青年們聊著。終於一次課後,我鼓足了勇氣,拿著幾頁新列印的詩稿,等簇擁的學生都稀疏了以後,才遞過去並緊張地說道,「老師,我也寫詩,這是我的一些作品,請您指導」。
又一週課後的九點鐘,我踏上了那條日後頻繁與他送往的「詩之路」,即從四工教學樓經圖書館到校訓碑,沿著和平園前的梧桐道直抵二號門,門外不遠就是名為「孝陵衛」的地鐵站。這段大約20分鐘的路程,一步步深化著我們的師生情誼。在逸夫樓暗香浮動的晚春,他說他認真讀過我的詩,並認為很有潛力,但要從事詩歌寫作,筆名還得好好考慮,這對一位詩人來說很重要,還講起他從「黃帆」改為「黃梵」的故事。
再一週在走得更遠的一個地點,即藝文館前那片著名的水杉林前,他對我取的兩個筆名都不滿意,並建議我可以叫「炎石」,「炎」是你名,而「石」符合你的性格,「炎石」就很不錯。如今看來,確實很不錯,如同被施了魔法,這筆名統攝住了我。二○年初,我又著意重啟寫作,擬換個新名與過去告別,但試用了一陣還是作罷。
與黃老師結緣後,我又持續選了他多門課程,直到無法再選。現在回顧過去十數年的寫作,我現在寫詩之所以如是,與黃老師的關係很大。他有一首〈中年〉我印象深刻,我幾乎是讀著〈中年〉來到中年的,正是這一首詩的詩法影響了我,我始知詩可以這樣作而非那樣。後來我陸續受到柏樺、飛廉,以及個人新詩溯源工作啟動後,直接受卞之琳與杜甫的影響,但我的詩仍隱含著黃詩味道的。我一直想談談他的詩(我已寫得越來越有資格去談),但因他是我的新詩師,我總在等一個合適的時刻。我會為他的詩被低估而感到不平,但他耐受得住並不此為意,同時又小說又教詩歌課的,使得我的詩弟詩妹也滿天下了。
一四年畢業後,因為要穩定工作與生活,我基本剎住了新詩的寫作。一七年從南京灰溜溜地離開,也未第一時間告訴他。在我不再陪伴他「詩之路」後的很多年,我們之間僅有的幾次聯繫,一次在我去安康的綠皮火車上,他問我近來寫作如何,那時我寫得很少羞慚無言;還有一次就是「屏體詩」寫成後,我再次像學生時代那般,每有新作就發送給他指導,這一次他高興甚至有些激動,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分開後十年裡,僅有的一次見面,還是在去年我到南京開會,再次去他已位於江寧的新家,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師母,我跟往常一樣話說得很少。正午時分頂著南京的暑日,我陪他再次走了段短短的「詩之路」,在碰到返程來接的師母後,一腳油門我們就到了那張鋪滿美食的餐桌上。後來,我每月都會去南京開會,但已沒有去拜訪他的念頭,那個訥於言的青年如今已是訥於言的中年,但是一想到那些可以在詩裡夷平的高樓,就想著我們師生相見在詩裡,會更從容、更親切一些。
黃老師曾在《南方週末》開設過專欄,寫過一篇〈校園詩人〉的文章,裡面有這樣一句話,「雖然炎石認為他寫詩考慮東方,始於我的《東方集》,但我覺得他會比我走得更遠、更扎實,因為他比我更死心眼。死心眼甚至影響了他對前途的抉擇。」我的寫作和黃老師的淵源,如果我不提這段經歷,很多人是並看不出來的,但飲水思源我還是要提的,這淵源不止是詩本身的,更是我們對於詩這件事所持有的態度上的。
2023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