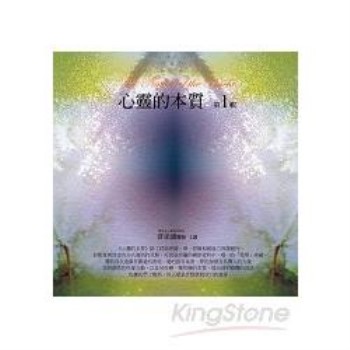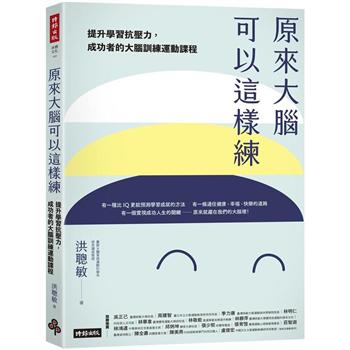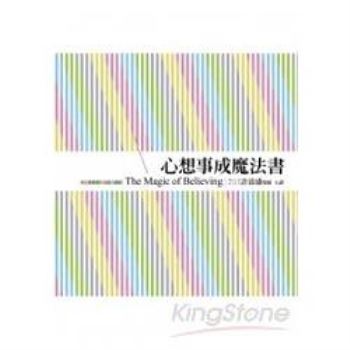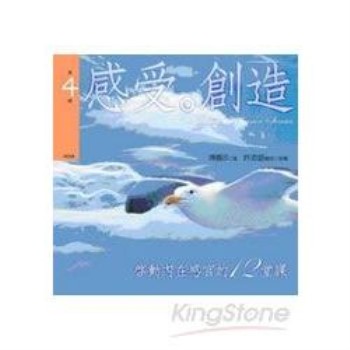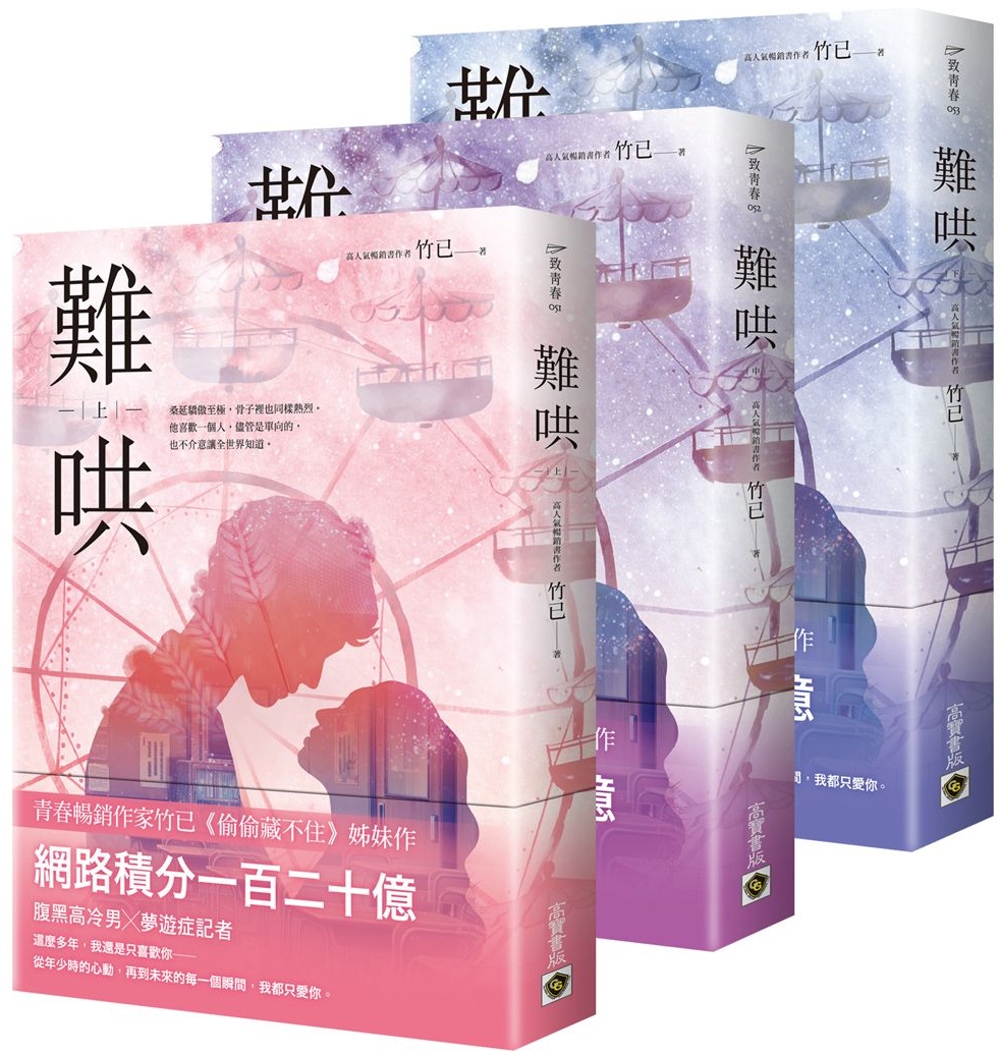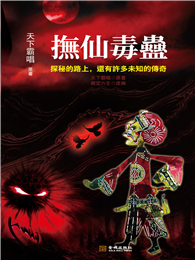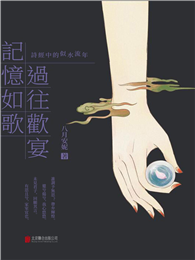本書集結作者數十年來對加拿大華裔、華文文學與華文媒體的研究成果,聚焦張翎《金山》、陳河《沙撈越戰事》、曾曉文《蘇格蘭短裙和三葉草》、笑言《香火》、李群英《殘月樓》、崔維新《玉牡丹》等多部經典作品和瘂弦先生華文文學的理論,探究加拿大華人作家如何通過文學想像重構加拿大華人的歷史軌跡,轉化族裔聲音成為文學表達,分析並反思新移民在加拿大的文化定位及其身分認同的變遷──從客居者到落地生根,從邊緣到主流的過程中,如何創造出華裔–加拿大文化(Chinese-Canadian Culture)。
本書特色
★縝密梳理加拿大華裔百年文學,了解海外華人及華裔文學不容錯過的學術著作!
各界推薦
陳思和(上海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歷史想像和離散經驗:百年加拿大華裔文學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歷史想像和離散經驗:百年加拿大華裔文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徐學清
博士。約克大學語言、文學和語言學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為加拿大華裔文學和媒體,女性文學。曾發表五十多篇中英文學術文章,著有《孔子》,合編出版五本書籍。目前的研究項目是在溫哥華出版發行的《大漢公報》,項目題目是“Daily Narrative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Canada: The Chinese Times (1910-1992, Vancouver)”。該項目由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委員會基金資助。
徐學清
博士。約克大學語言、文學和語言學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為加拿大華裔文學和媒體,女性文學。曾發表五十多篇中英文學術文章,著有《孔子》,合編出版五本書籍。目前的研究項目是在溫哥華出版發行的《大漢公報》,項目題目是“Daily Narrative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Canada: The Chinese Times (1910-1992, Vancouver)”。該項目由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委員會基金資助。
目錄
推薦序/陳思和
第一輯 加華文學中的歷史敘述
加拿大華人歷史的重新書寫:華裔小說中的歷史性和文學想像
加拿大華文文學的史詩敘事
金山的夢幻和淘金的現實:論張翎的長篇小說《金山》
史海中命運的浮沉
離散中身分的確認
人性、獸性和族性的戰爭:讀陳河的《沙撈越戰事》
《大漢公報》敘述中的孫中山:跨地方的觀點
華英日報和馮德文牧師
第二輯 故園,離散和文化身分
文化身分的重新定位:解讀笑言的《香火》和文森特‧林的《放血和奇療》
從客居到永居:《大漢公報》詩歌中「家」的觀念的變化(1914-1960)
1914-1923:客居者的鄉愁/思
1923-1947:忍辱抗爭
1947-1960:落地生根
何處是家園:談加拿大華文長篇小說
新移民與母語文化
邊緣與主流
文化記憶與身分的多質性
衝突中的調和:現實和想像中的家園
《楓情萬種》前言
第三輯 作家、作品論
瘂弦與世界華文文學
具有光線,音響和色彩的文字──讀張翎授權華語文學網發表的十部中篇小說
文化的翻譯和對話:張翎近期小說論
敘事結構
它–敘述(it - narratives)
張翎小說的世界性
論張翎小說
陳河小說中的異國文化書寫
評《蘇格蘭短裙和三葉草》
孫博小說論
尋找過程中文化身分的定位
天堂與地獄
海歸和出洋:洋博士與小留學生的逆向潮動
同性和異性的愛
第四輯 性別與女性敘述
《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前言
母親手中的生殺大權:比較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三部小說
《新的智慧》:文化衝突中的暴力母親
《殘月樓》:男權家長制對母性的摧殘
《餘震》:跨越男尊女卑的「牆」
母親形象的解構:從聖母到惡母
貞節觀和性強暴:論《勞燕》
以男權為中心的性暴力征服的文化
從貞貞到阿燕:對傳統貞潔/貞節觀念的反叛
解構歧視女性的貞潔/貞節文化觀
曾曉文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表述
女性在移民生涯中的雙重困境
女性身分危機
女性意識的覺醒,走向獨立和自立
艾莉絲‧孟若
生平與創作
《你以為你是誰》(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創傷記憶和戰爭的孩子:論《歸海》
第五輯 華文文學與理論探討
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華文文學的雜糅──與陳思和商榷
世界華文文學和中國文學
一元、三元和多元的關係
落葉歸根、落地生根及靈根自植
附錄
旅外華語文學之我見──兼答徐學清的商榷/陳思和
〈旅外華語文學之我見〉
我對於徐學清教授商榷的回應
文學創作中的抄襲與互文性
第一輯 加華文學中的歷史敘述
加拿大華人歷史的重新書寫:華裔小說中的歷史性和文學想像
加拿大華文文學的史詩敘事
金山的夢幻和淘金的現實:論張翎的長篇小說《金山》
史海中命運的浮沉
離散中身分的確認
人性、獸性和族性的戰爭:讀陳河的《沙撈越戰事》
《大漢公報》敘述中的孫中山:跨地方的觀點
華英日報和馮德文牧師
第二輯 故園,離散和文化身分
文化身分的重新定位:解讀笑言的《香火》和文森特‧林的《放血和奇療》
從客居到永居:《大漢公報》詩歌中「家」的觀念的變化(1914-1960)
1914-1923:客居者的鄉愁/思
1923-1947:忍辱抗爭
1947-1960:落地生根
何處是家園:談加拿大華文長篇小說
新移民與母語文化
邊緣與主流
文化記憶與身分的多質性
衝突中的調和:現實和想像中的家園
《楓情萬種》前言
第三輯 作家、作品論
瘂弦與世界華文文學
具有光線,音響和色彩的文字──讀張翎授權華語文學網發表的十部中篇小說
文化的翻譯和對話:張翎近期小說論
敘事結構
它–敘述(it - narratives)
張翎小說的世界性
論張翎小說
陳河小說中的異國文化書寫
評《蘇格蘭短裙和三葉草》
孫博小說論
尋找過程中文化身分的定位
天堂與地獄
海歸和出洋:洋博士與小留學生的逆向潮動
同性和異性的愛
第四輯 性別與女性敘述
《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前言
母親手中的生殺大權:比較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三部小說
《新的智慧》:文化衝突中的暴力母親
《殘月樓》:男權家長制對母性的摧殘
《餘震》:跨越男尊女卑的「牆」
母親形象的解構:從聖母到惡母
貞節觀和性強暴:論《勞燕》
以男權為中心的性暴力征服的文化
從貞貞到阿燕:對傳統貞潔/貞節觀念的反叛
解構歧視女性的貞潔/貞節文化觀
曾曉文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表述
女性在移民生涯中的雙重困境
女性身分危機
女性意識的覺醒,走向獨立和自立
艾莉絲‧孟若
生平與創作
《你以為你是誰》(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創傷記憶和戰爭的孩子:論《歸海》
第五輯 華文文學與理論探討
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華文文學的雜糅──與陳思和商榷
世界華文文學和中國文學
一元、三元和多元的關係
落葉歸根、落地生根及靈根自植
附錄
旅外華語文學之我見──兼答徐學清的商榷/陳思和
〈旅外華語文學之我見〉
我對於徐學清教授商榷的回應
文學創作中的抄襲與互文性
序
推薦序
上海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陳思和
徐學清是我在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那是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江湖上各路落魄英雄都匯集高校,真是一時多少豪傑。而學清卻是少數應屆考上的女生,不僅年輕,而且清純稚嫩,除了埋頭用功,廣泛涉獵中外圖書,不怎麼參與學校裡的公眾性活動,也沒有什麼一鳴驚人的舉動(那時我班級裡才子才女多多,經常有一鳴驚人之舉)。我之所以留下了她「廣泛涉獵」的印象,是那時候我經常在圖書館裡遇到她,當她看到我正在借閱或者準備閱讀某本書,她會主動告訴我,這本書她已經讀過,好看,或者不好看,給予我指導性意見。她確實讀了很多書。後來,她考上了潘旭瀾教授的研究生,開始發表當代文學研究文章,再後來,她到北京工作,又出國深造。等我再遇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加拿大約克大學的文學教授,帶領一批洋學生到復旦大學來訪學。那時我正擔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職務,接待時發現來客竟是舊時同窗,意外之喜不勝形容。
但是我了解到徐學清研究加拿大華裔文學還是後來的事情。大約是在2016年,或者還更早些。瘂弦先生主編的加拿大《世界日報》副刊《華章》特設「名家談──華人文學之我見」專欄,徐學清代瘂公約稿,囑我寫一篇短文。我把文章寄去後很快就登了出來,但學清給我來信說,她看了我的文章,不同意我把北美華文文學看作中國當代文學一部分的觀點,我就鼓勵她把商榷意見寫出來,這樣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入討論下去。她很快就寫好了,而我的回應文章卻拖了很久,後來在編輯的催促下也匆匆寫出,一起發表在《中國比較文學》2016年的第3期。我們都很重視這次論爭,相約把對方文章收入自己的論文集。我在新一本編年體文集《未完稿》裡收了她的文章,這次學清的論文集裡也收錄了我的文章。其實學術觀點無所謂對錯,我更珍惜的是同窗同行能夠在學術層面各抒己見,通過討論與爭鳴來釐清一些學術觀點。但是我們的文章都寫得不夠充分,對對方學術觀點缺乏透徹理解,因此,也不能真正說服對方。
直到我最近系統地閱讀了徐學清的論文集,終於比較清楚了她在學術上的真正追求和目標,才了解到她所堅持的學術觀點是有充分理由的。我意識到我們畢竟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國家,分別是兩個國家的公民。之前我一直沒有用這樣的角度來看海外華文作家。我考察華文文學的維度是寫作語言、文本以及出版地與讀者,所以把海外華文文學看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旅外部分。但徐學清的論述讓我明白了另外一個維度,作為從中國到海外深造、並留在海外高校工作的學者,她不可能像我這樣持單一的視角,僅僅看到中國當代作家對海外的輸出、以及他們重新面對國內寫作的事實。徐學清研究華文文學的背後,還有另一個更大背景存在,這正是我所欠缺、疏忽的領域──華裔文學。這是一個長期生活在海外,用在地國語言進行創作的族群,他們應該算作在地國的少數民族作家,他們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徐學清在討論加拿大華裔文學中的歷史書寫時,把李群英的《殘月樓》,崔維新的《玉牡丹》和張翎的《金山》併置於同一個層面上進行分析。李群英和崔維新兩位作家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討論中國文學不可能把他們在加拿大出版的英語作品羅列進來。而徐學清站在研究加拿大文學的立場上,她研究新移民張翎的作品時,很自然就把這兩位前輩華裔作家的作品作為張翎的「背景」來進行比較研究。為此我特意上百度搜索兩位作家的信息,他們都屬於第二代移民,李群英的代表作《殘月樓》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提名,被列為加拿大華裔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崔維新也被譽為「加拿大最有講故事天賦的人」,晚年還獲得國家最高榮譽加拿大勳章。這兩位華裔作家都以非凡的英語寫作能力被融入加拿大國家主流文化,他們的文學創作理所當然成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又如在〈母親手中的生殺大權:比較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三部小說〉一文中,徐學清在李群英與張翎的創作外,又加入了伊迪思‧伊騰斯(Edith Maud Eaton)寫於上個世紀初的作品。伊迪思有華人血統,但出生於英國,父親也是英國人。她的小說描寫了華人的文化背景,與李群英、張翎可以說是三個時代的作家,她們所反映的中國文化也有不同時代的背景。這就構成了可比較性,也是徐學清研究的著眼點。我們從徐學清所構置的伊迪思、李群英、崔維新、張翎的華人作家譜系裡能夠看到以下幾個特點:一,他們都是加入了加拿大國籍的華人(伊迪思‧伊騰斯只有1/2的華人血統),除了張翎外,他們都是第二代移民;二,除了張翎,他們都用英語寫作(張翎最近也開始用英語寫作),並且在在地國獲得成功,融入了主流文化;三,他們雖有不同的移民背景,但都屬於加拿大的少數民族文學的作家。張翎與她們的不同之處,是張翎在中國擁有大量的讀者,而且至今為止她的主要讀者還都是來自中國。應該說,張翎的這些特點,在當下第一代移民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徐學清作為一個加拿大籍的華人學者,她的研究對象是加拿大華人文學(或者說華裔文學),華人文學在加拿大源遠流長,已經有了立足的地位。徐學清的研究目的,正在致力於推動加拿大多元文化發展,希望在多元文化格局裡,彼此平等交流、融匯,華人文學及其文化能夠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她把張翎、陳河這樣一批優秀作家列入加拿大華人文學的行列,當然無可厚非。邏輯上來說,少數民族作家應該是雙語作家,正如中國的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作家,他們當然可以自由選擇用漢語寫作還是用他們本民族的語言來寫作。但困境也同樣存在,正如中國的主流文化很難接受用少數民族語言寫作的文學作品一樣,在加拿大的主流文化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接受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華文文學、華人文學、華裔文學,畢竟是三個不一樣的學科概念。我與徐學清的爭論,到現在才算是可以分清楚了,我是站在華文文學的研究立場上,以中國當代文學為背景來討論問題,徐學清是站在加拿大華人文學的研究立場上,以加拿大的華裔文學為背景來討論問題,學術觀點的分歧是由不同學術分野而形成的。
我讀學清的書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她對加拿大華人文學有精湛的研究,對伊迪思‧伊騰斯這樣老一輩的混血移民二代作家,對文森特‧林、李群英、崔維新等當代的移民二代作家以及當下移民作家如張翎、陳河等都有深入的研究,由此編織了一份豐富清晰的加華文學譜系圖。徐學清的研究成果對於我有關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思考也幫助多多,讓我越來越認識到世界華文文學、國別+華人文學、國別+華裔文學是三個必須有所區別的學科概念。通常我們研究的世界華文文學,主要是指第一代移民中與母國還存在著密切關聯的作家的華語創作,海外華文作家的主要特徵是以華語從事創作,其創作內容、語言以及文學的流通和傳播,仍然與母國密切相關。我之所以認為他們的創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旅外部分,也就是要見證這一特徵。但是這是一個註定會消失的特徵,隨著海外華文作家與在地國文化越來越密切的相融,或者他們中有的一開始就從事在地國語言寫作,那麼,他們將會朝著華人文學的方向轉換。國別+華人文學是一個特別寬泛的概念,它包括在地國所有華人血統的作家創作,不管用什麼樣的語言從事寫作,也不管屬於第幾代移民的作品。第三個概念是國別+華裔文學,華裔文學是指已經融入在地國主流文化的族裔文學,一般來說,第一代移民作家的創作很難稱作為華裔文學,「裔」本來就是指血統上的「後人」,不是第一代。因此,張翎、陳河的創作不能歸入加拿大華裔文學範疇,但他們的創作可能會給族裔文學帶來新鮮血液。第一代移民作家的創作屬於世界華文文學,也屬於國別+華人文學;然而李群英、崔維新等二代移民作家的創作不能屬於世界華文文學,但屬於國別+華人文學,或者屬於國別+華裔文學。像伊迪思‧伊騰斯的創作,可以歸為國別+華裔文學的範疇,但不屬於華文文學,也不屬於華人文學。
我拉拉扯扯地寫下這些文字,談不上對徐學清著述的評價,只是談我自己的一點學習體會。我想說的是,徐學清從加拿大華裔文學、加拿大華人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具有當下性的加拿大華文文學,是對華文文學研究的一種擴充。華裔文學是中國學界幾乎不關注的領域。記得十多年前,我曾經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引進一位美籍華人學者,是研究美國華裔文學的專家。她來到復旦工作以後,舉辦大型的美國華裔文學國際研討會,邀請湯亭亭等著名作家來復旦講座,轟轟烈烈,一時傳為佳話。可惜當時學術界對這個領域非常陌生,這位學者後來也因為各種原因離開復旦回國去了。但我一直覺得,對於世界各國華裔文學的深入研究,是中國比較文學特別需要加強的領域,因為它是連接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國文學的紐帶,可以由此引申出許多值得研究的課題。徐學清關於加拿大華裔文學及其與第一代移民華文作家關係的研究,是一個有活力,具有廣闊前景的學科,我期望她的學術事業由此得到更大的發展。
──2024年3月12日於復旦大學圖書館
上海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陳思和
徐學清是我在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那是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江湖上各路落魄英雄都匯集高校,真是一時多少豪傑。而學清卻是少數應屆考上的女生,不僅年輕,而且清純稚嫩,除了埋頭用功,廣泛涉獵中外圖書,不怎麼參與學校裡的公眾性活動,也沒有什麼一鳴驚人的舉動(那時我班級裡才子才女多多,經常有一鳴驚人之舉)。我之所以留下了她「廣泛涉獵」的印象,是那時候我經常在圖書館裡遇到她,當她看到我正在借閱或者準備閱讀某本書,她會主動告訴我,這本書她已經讀過,好看,或者不好看,給予我指導性意見。她確實讀了很多書。後來,她考上了潘旭瀾教授的研究生,開始發表當代文學研究文章,再後來,她到北京工作,又出國深造。等我再遇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加拿大約克大學的文學教授,帶領一批洋學生到復旦大學來訪學。那時我正擔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職務,接待時發現來客竟是舊時同窗,意外之喜不勝形容。
但是我了解到徐學清研究加拿大華裔文學還是後來的事情。大約是在2016年,或者還更早些。瘂弦先生主編的加拿大《世界日報》副刊《華章》特設「名家談──華人文學之我見」專欄,徐學清代瘂公約稿,囑我寫一篇短文。我把文章寄去後很快就登了出來,但學清給我來信說,她看了我的文章,不同意我把北美華文文學看作中國當代文學一部分的觀點,我就鼓勵她把商榷意見寫出來,這樣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入討論下去。她很快就寫好了,而我的回應文章卻拖了很久,後來在編輯的催促下也匆匆寫出,一起發表在《中國比較文學》2016年的第3期。我們都很重視這次論爭,相約把對方文章收入自己的論文集。我在新一本編年體文集《未完稿》裡收了她的文章,這次學清的論文集裡也收錄了我的文章。其實學術觀點無所謂對錯,我更珍惜的是同窗同行能夠在學術層面各抒己見,通過討論與爭鳴來釐清一些學術觀點。但是我們的文章都寫得不夠充分,對對方學術觀點缺乏透徹理解,因此,也不能真正說服對方。
直到我最近系統地閱讀了徐學清的論文集,終於比較清楚了她在學術上的真正追求和目標,才了解到她所堅持的學術觀點是有充分理由的。我意識到我們畢竟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國家,分別是兩個國家的公民。之前我一直沒有用這樣的角度來看海外華文作家。我考察華文文學的維度是寫作語言、文本以及出版地與讀者,所以把海外華文文學看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旅外部分。但徐學清的論述讓我明白了另外一個維度,作為從中國到海外深造、並留在海外高校工作的學者,她不可能像我這樣持單一的視角,僅僅看到中國當代作家對海外的輸出、以及他們重新面對國內寫作的事實。徐學清研究華文文學的背後,還有另一個更大背景存在,這正是我所欠缺、疏忽的領域──華裔文學。這是一個長期生活在海外,用在地國語言進行創作的族群,他們應該算作在地國的少數民族作家,他們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徐學清在討論加拿大華裔文學中的歷史書寫時,把李群英的《殘月樓》,崔維新的《玉牡丹》和張翎的《金山》併置於同一個層面上進行分析。李群英和崔維新兩位作家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討論中國文學不可能把他們在加拿大出版的英語作品羅列進來。而徐學清站在研究加拿大文學的立場上,她研究新移民張翎的作品時,很自然就把這兩位前輩華裔作家的作品作為張翎的「背景」來進行比較研究。為此我特意上百度搜索兩位作家的信息,他們都屬於第二代移民,李群英的代表作《殘月樓》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提名,被列為加拿大華裔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崔維新也被譽為「加拿大最有講故事天賦的人」,晚年還獲得國家最高榮譽加拿大勳章。這兩位華裔作家都以非凡的英語寫作能力被融入加拿大國家主流文化,他們的文學創作理所當然成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又如在〈母親手中的生殺大權:比較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三部小說〉一文中,徐學清在李群英與張翎的創作外,又加入了伊迪思‧伊騰斯(Edith Maud Eaton)寫於上個世紀初的作品。伊迪思有華人血統,但出生於英國,父親也是英國人。她的小說描寫了華人的文化背景,與李群英、張翎可以說是三個時代的作家,她們所反映的中國文化也有不同時代的背景。這就構成了可比較性,也是徐學清研究的著眼點。我們從徐學清所構置的伊迪思、李群英、崔維新、張翎的華人作家譜系裡能夠看到以下幾個特點:一,他們都是加入了加拿大國籍的華人(伊迪思‧伊騰斯只有1/2的華人血統),除了張翎外,他們都是第二代移民;二,除了張翎,他們都用英語寫作(張翎最近也開始用英語寫作),並且在在地國獲得成功,融入了主流文化;三,他們雖有不同的移民背景,但都屬於加拿大的少數民族文學的作家。張翎與她們的不同之處,是張翎在中國擁有大量的讀者,而且至今為止她的主要讀者還都是來自中國。應該說,張翎的這些特點,在當下第一代移民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徐學清作為一個加拿大籍的華人學者,她的研究對象是加拿大華人文學(或者說華裔文學),華人文學在加拿大源遠流長,已經有了立足的地位。徐學清的研究目的,正在致力於推動加拿大多元文化發展,希望在多元文化格局裡,彼此平等交流、融匯,華人文學及其文化能夠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她把張翎、陳河這樣一批優秀作家列入加拿大華人文學的行列,當然無可厚非。邏輯上來說,少數民族作家應該是雙語作家,正如中國的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作家,他們當然可以自由選擇用漢語寫作還是用他們本民族的語言來寫作。但困境也同樣存在,正如中國的主流文化很難接受用少數民族語言寫作的文學作品一樣,在加拿大的主流文化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接受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華文文學、華人文學、華裔文學,畢竟是三個不一樣的學科概念。我與徐學清的爭論,到現在才算是可以分清楚了,我是站在華文文學的研究立場上,以中國當代文學為背景來討論問題,徐學清是站在加拿大華人文學的研究立場上,以加拿大的華裔文學為背景來討論問題,學術觀點的分歧是由不同學術分野而形成的。
我讀學清的書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她對加拿大華人文學有精湛的研究,對伊迪思‧伊騰斯這樣老一輩的混血移民二代作家,對文森特‧林、李群英、崔維新等當代的移民二代作家以及當下移民作家如張翎、陳河等都有深入的研究,由此編織了一份豐富清晰的加華文學譜系圖。徐學清的研究成果對於我有關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思考也幫助多多,讓我越來越認識到世界華文文學、國別+華人文學、國別+華裔文學是三個必須有所區別的學科概念。通常我們研究的世界華文文學,主要是指第一代移民中與母國還存在著密切關聯的作家的華語創作,海外華文作家的主要特徵是以華語從事創作,其創作內容、語言以及文學的流通和傳播,仍然與母國密切相關。我之所以認為他們的創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旅外部分,也就是要見證這一特徵。但是這是一個註定會消失的特徵,隨著海外華文作家與在地國文化越來越密切的相融,或者他們中有的一開始就從事在地國語言寫作,那麼,他們將會朝著華人文學的方向轉換。國別+華人文學是一個特別寬泛的概念,它包括在地國所有華人血統的作家創作,不管用什麼樣的語言從事寫作,也不管屬於第幾代移民的作品。第三個概念是國別+華裔文學,華裔文學是指已經融入在地國主流文化的族裔文學,一般來說,第一代移民作家的創作很難稱作為華裔文學,「裔」本來就是指血統上的「後人」,不是第一代。因此,張翎、陳河的創作不能歸入加拿大華裔文學範疇,但他們的創作可能會給族裔文學帶來新鮮血液。第一代移民作家的創作屬於世界華文文學,也屬於國別+華人文學;然而李群英、崔維新等二代移民作家的創作不能屬於世界華文文學,但屬於國別+華人文學,或者屬於國別+華裔文學。像伊迪思‧伊騰斯的創作,可以歸為國別+華裔文學的範疇,但不屬於華文文學,也不屬於華人文學。
我拉拉扯扯地寫下這些文字,談不上對徐學清著述的評價,只是談我自己的一點學習體會。我想說的是,徐學清從加拿大華裔文學、加拿大華人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具有當下性的加拿大華文文學,是對華文文學研究的一種擴充。華裔文學是中國學界幾乎不關注的領域。記得十多年前,我曾經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引進一位美籍華人學者,是研究美國華裔文學的專家。她來到復旦工作以後,舉辦大型的美國華裔文學國際研討會,邀請湯亭亭等著名作家來復旦講座,轟轟烈烈,一時傳為佳話。可惜當時學術界對這個領域非常陌生,這位學者後來也因為各種原因離開復旦回國去了。但我一直覺得,對於世界各國華裔文學的深入研究,是中國比較文學特別需要加強的領域,因為它是連接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國文學的紐帶,可以由此引申出許多值得研究的課題。徐學清關於加拿大華裔文學及其與第一代移民華文作家關係的研究,是一個有活力,具有廣闊前景的學科,我期望她的學術事業由此得到更大的發展。
──2024年3月12日於復旦大學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