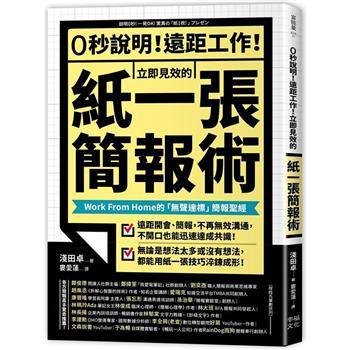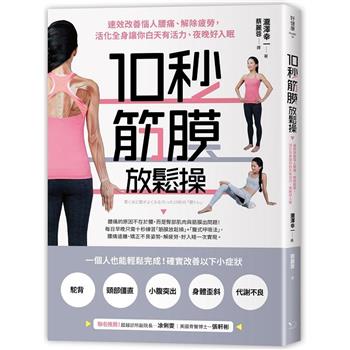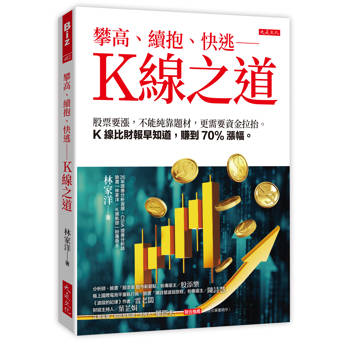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多是多少,文學即社會?少是多少,文學如衛生紙?
如今他那枯草覆蓋的墳頭,還能否發出螢火,只有深邃夜空的北極星知道。」
喀喇崑崙的皚皚雪山,葉爾羌河的潺潺流水,高原荒漠的執勤和演練
老夫聊發少年狂,訴說被風沙掩埋的故事……
如今他那枯草覆蓋的墳頭,還能否發出螢火,只有深邃夜空的北極星知道。」
喀喇崑崙的皚皚雪山,葉爾羌河的潺潺流水,高原荒漠的執勤和演練
老夫聊發少年狂,訴說被風沙掩埋的故事……
▎西陲兵事.咫尺生死兩茫茫
──「就是和戰友死在一起,也值了!」
「放屁!值什麼值?」我不知為何突然變得如此激動。「大家不要忘了,『崑崙之鷹』是有任務的。我們這一趟爬冰臥雪,所有的辛苦和犧牲,就為了測繪組,更確切地說,為了那些測繪數據。能將那些數據帶回去,所有的犧牲都是值得的;如果那些數據回不去,就是我們都死了,所有人都死得一文不值。現在又不是戰爭年代,上級還會安排下一次測繪。在幾百萬人的部隊,在十多億人口的國家,我們充其量只是些磚塊、石子、木頭棒子,沒有誰不可代替。但在家裡,我們都是兒子,是父母的心頭肉,是唯一的。我們爹我們媽養我們一場,就為了抱一本烈士證,在夜深人靜時傷心流淚嗎?」
▎母親的婚禮
──「小娃娃,我們鬥不過人家,以後別咬人了!」
「我都是因為太喜歡你了,太愛你了,才出此下策。」白炳文雙腿一屈,突然跪在地上,抱住她的腿哀求起來。「按說我這是挖戰友的牆角,確實不道德,所以才不敢在部隊辦婚禮。我想過一段時間再告訴你,等穆成班師回來,他就是揍我一頓,最終也會接受這個現實的。原諒我吧!雖然你一開始就沒看上我,但我一見你就喜歡得不行,我真的不能沒有你啊……」
▎密林深處
──「孩子,別去了,讓媽媽在烈火中永生吧!」
婷婷?一個陌生而熟悉的名字。我像被電了一下,手一鬆,一羅篩麩皮翻倒進白麵裡,不得不重新過篩。我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但在和麵的時候,還是禁不住老往女子的臉上看,打量她大大的眼睛,微翹的鼻梁和一頭黑長的頭髮,打量她黑馬甲上那一朵無名的紅花。我覺得她和我腦海裡那個同名的人確有幾分相像,又不是很像。要不是婷婷一直提醒我「梁叔叔快和呀」,我肯定自己會精神穿越,回到風華正茂的青年時期。良久,我漸漸平靜下來,才有一句沒一句的問:「你媽媽呢?你爸爸呢?」
本書特色
本書以記錄一九七〇、八〇年代西陲邊塞軍營生活為主,展現了作者曾過往的軍旅生涯及所見所感。以親身經歷和生動筆觸,描繪了戰友們的故事,既有對戰爭無情的控訴,也有對和平年代的思考。不僅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象,也深入探討了人性、命運與理想的矛盾。收錄了〈西陲兵事〉、〈守山〉、〈密林深處〉、等多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