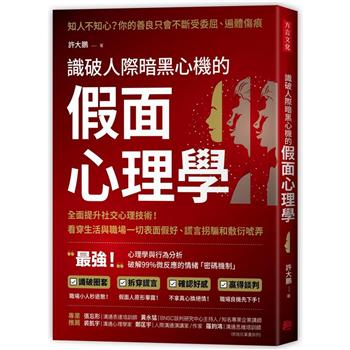阿里和娜拉
阿里要當父親了,
然而,娜拉卻不是當然的母親。
阿里唱的是一支快樂的悲歌,但是,娜拉唱的卻是一闕此生無盡的哀曲!
1
有一天晚上,已經八點多了,日勝還留在公司裡開會,我家門鈴忽然響了起來。我懷著警戒的心將門拉開一條小縫,朝外張望。站在門外微弱燈光底下的,是一個高瘦的阿拉伯人。他披著一方紅白相間的頭巾,穿著一襲奶油色的及地長袍,又圓又大的眼珠,在黑夜裡閃閃發亮。
「你找誰呀?」我問,雙手把門扳得緊緊的。
「請問,林先生在家嗎?」他問,清澈的目光裡,沒有半點令人起疑的邪惡。
我立即把門拉開了,說:
「他還在公司裡,今晚恐怕很晚才能回來。你有什麼事嗎?」
一抹失望,明顯地在他黧黑的臉飛掠而過;猶豫了一會兒,他才說: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就是想找他聊天。」
「呃——你把名字留下,我請他聯繫你好了。」
「哦,就請妳告訴他,警官阿里來找過他。」
說完,他微笑地朝我點點頭,轉身離開,高高的身子在月色下拖了一條長長的影子。
次晚,他又來了。我邀他進屋子裡,在屋內明亮的燈光下打量他,我發現他蓄有兩撇八字鬚,鼻子微翹,皮膚很黑,黑得發亮,但比他皮膚更黑更亮的,是他的眸子,這一雙眸子,看人時精銳、不看人時憂鬱。使人覺得舒服的,是他儀表的整潔,奶油色的長袍飄散著肥皂粉特有的芬芳,指甲修剪得圓圓齊齊的,沒有夾雜半點汙垢。
我為他倒了汽水,坐下來與他聊天。阿里的英語不是如水般的流暢,但是,他敢講,碰上不懂的詞彙,便以手勢助陣,所以,在溝通上全無問題。
他開門見山地問我:
「妳喜歡吉達嗎?」
坦白地告訴他,我才來了短短一個星期,還處在適應的狀態中。
「我們的國家,有許多美麗的傳統和風俗,住久了,妳一定會喜歡的。」他說,聲音裡透著驕傲:「阿拉伯人熱誠好客,一旦熟悉了,便把你當家人,掏心掏肺,很好相處。」
在聊天裡,我知悉阿里16歲便輟學而投入警界服務了,經過漫長十年艱辛的掙扎與不懈的努力,終於由一個雜務纏身的小警員擢升為身負要職的警長了。
「我的父親很早去世,母親含辛茹苦將我們四兄弟姐妹撫養成人。」他緩緩地說,眼睛迷濛地沉浸在久遠的往事裡:「我在家裡排行最小,母親一直希望我能把書讀好,再找份理想的工作。遺憾的是,我當年無知,老是逃學,著實傷透了她的心。現在想想,很是後悔,但是,時光又不能倒流,沒辦法啊!」
「你目前的表現,不就是她最大的安慰嗎?」我說。
「嘿,我這算是哪門子的表現呢?」他輕輕地笑了笑,但笑意只淺淺地停留在他的嘴角,不曾滲透進他的眸子裡;頓了頓,又說:「我現在正努力學習英文,希望過一兩年把語文的基礎打好後,便可以改行做生意了。」
在生意上賺大錢,便算是很有表現嗎?我想問,但不曾。彼此交情尚淺固然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我不願意唐突地以自己的價值觀加諸於他人。甲之熊掌,乙之貓爪。青菜蘿蔔,各有所愛啊!
那天晚上,他在我們家談了兩個多小時才告辭。憑直覺,阿里似乎是個不快樂的人,和日勝提起,他卻淡淡地說:
「他也許只是不滿意自己的職業,隨便發點牢騷罷了!」
2
阿里每天早上九點半上班,下午兩點半便下班了。工作時間短,閒暇多,加上他住在我家附近,因此,常常在晚飯過後找我們聊天。來的次數多而逗留的時間又長,很快地,我們由相識而相知、由陌生而稔熟,談話的內容,也不僅僅停留於表面了。深入地探索他的內心世界,我發現我的直覺並不曾欺騙我。阿里真的不快樂,使他不快樂的,不是他的工作,而是他的婚姻。
阿里的妻子娜拉,才15歲,比阿里小了整整10歲。他們結婚雖然已經半年了,但同住的日子加起來還不到一個月。不是他的妻子不願意和他長相廝守,而是有人從中作梗,這個人,居然是娜拉的母親——阿里的岳母!
「我的岳父,是一所小學的校長,為人隨和。我的岳母呢,就完全不同了,她工於心計。結婚以前,對我一直客客氣氣的,但一收取了聘金而正式成親後,她便換了一副嘴臉,常常在娜拉面前將我批評得一文不值。這還不打緊,我們結婚不到一個星期,她便藉口娜拉年齡太小,不諳家務而把她叫回家去住。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娜拉每週只獲准來我這裡住一天,妳看看,這哪裡像是婚姻呢?」他神情激動地說。
「娜拉本人有什麼打算呢?」我問。
「母命難違嘛,她還能怎樣!」他答,聲音裡透著無奈。
「那——她對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哦,她很喜歡我。」他說,憂鬱的眼睛突然有了隱隱的笑意:「妳知道嗎,我足足熬了兩年才娶到她的!」
「咦,你們不是父母做媒撮合的嗎?」我好奇地問。
「不是的,是我自個兒上門求親的!」他得意洋洋地說。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呢?」我追問。沙烏地阿拉伯風俗保守,男女婚前自由戀愛,是聞所未聞的!
「我們並不認識彼此。」他說,眼裡的笑意慢慢加深了:「兩年前,有一天,我駕車經過一條小巷,剛好她從屋子的後門走出來,沒有戴面罩,我不經意地和她打了一個照面,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剎那,我的心弦起了莫名的顫動,好像有個聲音告訴我:是她,就是她! 這樣強烈而又奇特的感覺,我這一生,從來、從來不曾有過。我多方打聽她的姓名,好不容易打聽出來後,便上門求親了。她的父母要求聘金四萬里亞爾(Riyal),我一個月的薪水才四千里亞爾,一時怎麼湊得出這麼大筆錢!我要求她父母給我兩年的時間,沒想到他們一口便答應了。那以後,娜拉休學在家等我迎娶,我也努力去賺錢。半年前,我不但湊足了聘金,也為娜拉買了好些首飾。為了迎娶她,我將屋子內內外外裝修得煥然一新。你看,我為她做了那麼多,她一個星期竟然只在我家待一天!」 他一口氣把話說完後,眼裡的笑意沒有了,只留下了一絲絲的苦澀。
「你的岳母既然不講理,你為什麼不向岳父提出交涉呢?」我忿忿不平地問道。
「啊,岳父什麼都聽岳母的。他太隨和了,隨和得完全沒有主見!」他意興闌珊地說。
身為警官的阿里,在執行任務時,威風凜凜,但處理自己的家事,卻變得一籌莫展。
3
自從阿里將他婚姻的隱情向我們剖白以後,娜拉就成了我們家裡一個「無時不在」的隱形人物了。每次阿里來我家時,總把她掛在嘴上。愛,像是一條蛇,在他心裡竄來竄去,他的眉毛眸子嘴唇全都是歡喜。
有一天晚上,阿里又娜拉長娜拉短的,我忍不住問道:
「阿里,你什麼時候有空,帶我回家見見娜拉,好嗎?」
「沒有問題呀!」他爽快地答應了,但接著又遲疑了起來:「娜拉不懂英語,你們怎麼交談呢?」
「用手語呀!」我飛快地答。
他大聲地笑了起來,我的話其實一點兒也不好笑,但是,只要一提到娜拉,他就不自覺地高興起來。
星期五是阿里的休息日,也是夫妻倆的「相聚日」。晚上八點,他到我家來載我。神清氣爽的阿里,整張臉靜靜地散發著一種迷人的燦爛,一般,只有熱戀中的人才會綻放這種亮光。
車子由山脊上無聲地滑下來,駛入大街,駛了約莫十分鐘,拐進一條滿布沙石的泥路,顛顛簸簸地爬了一陣子,來到一條小徑,兩旁全是土堆瓦砌的典型阿拉伯房屋,扁扁的燈光從門縫裡洩了出來,透著家的溫暖氣息。車子喘著氣,停在一幢米色的房子前。
阿里微笑地說:「到啦!」
我們下車後,他在那扉漆成藍色的鐵門上重重地叩了幾下,鐵門拉開了一條細細的縫,有兩道目光從裡面射了出來。接著,鐵門大大地被拉開了。門內,是一張不算年輕的臉。臉的特徵是圓、是扁。扁扁圓圓的臉在笑,然而,這一抹笑意卻無論如何也掩飾不了臉上的疲憊。15歲的少女,怎麼會憔悴如斯呢?我想。心裡的感覺很複雜——有一點同情,有一點失望,又有一點茫然。我完全沒有辦法把眼前這個憔悴的形象和阿里口中描述的那個娜拉聯想在一起。
阿里關上門以後,轉身為我介紹:「這是我的姐姐法蒂瑪。」啊,原來她不是娜拉!嘿,我居然自作聰明地張冠李戴。阿里說:「她的丈夫最近遇上車禍去世,她和兩個孩子暫時寄居在我家。」
法蒂瑪以她粗糙的雙手熱切地握著我的手,拚命地點頭微笑。阿里以目光在屋內搜尋了一會兒,問法蒂瑪:「娜拉呢?」她說了幾句阿拉伯話,阿里點點頭,轉頭對我說道:「娜拉到我母親家裡拿咖啡豆,一會兒就回來!」
「你母親住在哪裡?」
「就在附近,她和我哥哥一起住。」
我在大廳的沙發坐了下來,窗戶長年關著,屋內沒裝冷氣,風扇咿呀咿呀地在轉,但卻驅趕不了屋內膨脹的熱氣。廳裡的裝飾,可以用「花團錦簇」四個字加以形容—— 地毯是深青色的,上面五彩花卉怒放著;沙發是硃紅色的,喜氣洋洋;四面的牆壁呢,漆上了鮮豔的橙色,我好像掉進了一個五彩繽紛的調色盤裡,被熱鬧的色彩浸得滿身斑斕。
等了約莫10來分鐘,叩門聲響起了。阿里跑去開門,一個全身披著黑紗的女子進來了。我趕緊站了起來,阿里溫柔地將她牽到我面前,說:
「娜拉,我的妻子。」
她伸手掀開了罩在臉上的黑紗,我突然怔住了。黑紗下面,是一張光采動人的臉。她的美,全集中在她的眸子。那是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眸子,好似深潭靜水,裡面藏著一抹絢爛的彩虹,彩虹裡層層疊疊的全都是阿里的影子。然而,在那種夢幻的色彩裡,卻又難以掩飾地透著壓抑和渴望、痛苦和憧憬。
她眸子裡那豐富的內容,把我看呆了。
她放下了手中的咖啡豆,趨前來吻我的面頰,嘴唇溫軟一如玫瑰的花瓣,我甚至聞到了玫瑰的香氣。
阿里看著她說:
「娜拉,妳去泡阿拉伯咖啡,好不好?」
她默默地點了點頭,拿起了那包咖啡豆,朝廚房走去;阿里孀居的姐姐和兩個女兒則陪我們一起聊天。由阿里充當翻譯,偶爾我也用「手語」直接和她們交談,笑聲像陽光、像雪花、像雨點,灑落一地。
廚房裡,飄出了炒咖啡豆的聲音與香氣,阿里對著廚房,愣愣地出神。
過了大約半個小時,娜拉捧著托盤走出來。把托盤放在矮几上,她低著頭,將壺內金黃色的液體倒入小小的杯子裡;然後,雙手遞上一杯給我,棕黑色的臉,綴滿了宛若鑽石般的晶亮汗珠。
阿拉伯咖啡與我們慣常喝的那種香濃的黑咖啡全然不同,咖啡豆是米黃色的,在泡製時,加入了一種香料,味道如薑,辛辣濃烈。儘管味蕾難以接受那個怪異的味道,但基於禮貌,我強迫自己一口接一口地啜飲。娜拉坐在阿里旁邊,以清麗的眸子默默地看我。她滿頭濃黑的頭髮,結成了許多條細細的辮子,垂在腦後,這樣的裝扮,使原本年輕的她,顯得更加的年輕;然而,裹在鵝黃色長裙內那豐滿的身子,卻又遠比她實齡來得成熟。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沙漠裡的故事:在茫茫沙海中,尋找人生的綠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29 |
華文創作 |
$ 263 |
中文書 |
$ 269 |
現代小說 |
$ 269 |
小說 |
$ 269 |
中文現代文學 |
$ 269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沙漠裡的故事:在茫茫沙海中,尋找人生的綠洲
從笑聲到淚水,理想與現實的碰撞
感受生命的波瀾與共鳴
命運在追尋中交錯,夢想在拚搏中綻放
人生如書,每一頁都獨特而真摯
【駱駝「塔巴」】
我是在新加坡認識塔巴的,後來雖然在沙烏地阿拉伯和他成了熟稔的朋友,但是,初次與他晤面時那種突兀的感覺,迄今還清晰地留存於心頭。
記得就在我準備遠赴沙漠生活前的一個星期,日勝興沖沖地告訴我,他已邀約塔巴與我共進晚餐。塔巴原籍英國,是電氣工程師,到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已有十多年,現在利用年假到新加坡旅行,是我探聽沙漠生活實況的最佳對象。
我們在一家環境清幽的海鮮餐廳定了位子,由於一路上交通阻塞,抵達那裡時,塔巴已坐在臨海的一張桌子旁等著我們了。
他站起來與我握手,我的心猛然跳了一下——明明素未謀面,怎麼卻似曾相識呢?
他的鼻子很大,壓在臉上,像一座山;兩個朝天的鼻孔黑洞洞的,深不見底。那雙微微向外凸著而眼梢朝下的眸子,深邃而又暗沉,裡面好像裝滿了沉甸甸的悲傷。他看人時很專注,但由於太專注了,彷彿看的是對方的靈魂而不是面孔,令人渾身不自在。才40來歲,但卻蒼老得不成樣子,兩道深深長長的皺紋由眼尾迤迤邐邐地一直延伸到嘴唇旁邊,像被人狠狠地砍了兩刀似的。
塔巴是一個寡言少語的人,談及沙漠生活時,他輕描淡寫地說道:
「我不願以個人的觀感來影響你,你的眼睛將會給你最好的答案。」
【合乃流淚了】
由新加坡到沙烏地阿拉伯旅居的第一個星期裡,不適應那焚燒似的酷熱,我老是覺得昏昏沉沉、沒精打采的。
地板蒙塵、髒衣盈籮。日勝說:「幫妳找個幫傭,好吧?」懶於料理家務的我,忙不迭地點頭。
次日中午,正當我哄孩子泥泥午睡時,小白屋的敲門聲響起了,叩門的人好像在敲打樂器一樣,三下、一下、兩下、三下,敲出了一種很快樂的旋律。
站在門外的,是一個精神抖擻的男子,皮膚像是兌了牛奶的咖啡,有一種飽滿的褐色。他一手提著水桶,一手抓著拖把,滿臉都是愉悅的笑意。
我狐疑地看著他,問:「有什麼事嗎?」他向我禮貌地欠了欠身,以流利的英語說道:「夫人,我是來幫妳拖地、洗衣的。」我一面讓他進來,一面在心裡嘀咕:日勝怎麼會請一個大男人來幫我做家務呢,真是的!
他腳步輕快地走向洗手間,經過泥泥的房間,看到泥泥睡眼朦朧地坐在床上,他向泥泥扮了個滑稽的鬼臉,泥泥哈哈大笑,清脆的童音在屋子裡來來回回地撞擊,把原有的沉寂與沉悶擊碎了。
【彩蝶】
在沙漠裡居住,心緒常常會不由自主地陷入低潮。從視窗望出去,前前後後都是一望無盡的沙丘。永無變化的陽光,跋扈而專橫地趴在沙丘上,細細碎碎的沙礫,裊裊地冒著煩人的熱氣。
在這種單調而寂寞的生活裡,遠方親友的來信,便成了精神生活最好的調劑品。每天送信來給我的,不是郵差,而是公司裡負責福利工作的職員陳亞東。
在吉達市,所有的屋子都沒有門牌;就算是街道吧,也只是主要的大街設有街名,其他的許多橫街小巷,都是沒有名字的,因此,所有的函件都必須寄到郵政總局去。每天傍晚,陳亞東便得去那裡把公司兩百餘名員工的信件取回來分派。
這天,我焦急地等到傍晚七點多,陳亞東還是蹤影全無。這種情形,已經持續好幾天了,我的心,好像掉進了無底洞裡,虛虛晃晃的。
日勝八點多回來後,我忍不住發了牢騷:
「這些日子,老接不到信,不知道是不是郵政服務出了問題!」
日勝一聽,立刻抱歉地拍了拍額頭,應道:
「真對不起,你有好些信被我擱在辦事處,忘了取回來。」
「怎麼不讓陳亞東送來呢?」
「哦,公司辭退他了。」日勝解釋道:「他和大部分泰國工人合不來,鬧得很不愉快,早在幾個月前,公司便想解僱他了;但是,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只好一拖再拖。」
【失蹤】
我和瑪格麗特是在一種極為詭譎的情況下結識的。在日後的交往中,我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提起初識那一天的情形;而每回提起便忍俊不禁,然而,笑過以後回想,背脊卻依然會發涼。
瑪格麗特來自英國,和我一樣,她也是因為夫婿到沙烏地阿拉伯工作而旅居吉達的。
記得那天是星期四,我到「百麥加」去買椰棗泥。這是阿拉伯人嗜食的一種甜食,他們將熟透的椰棗搗成泥狀,烘烤成甜品,香而不膩;放一塊在嘴裡,能讓粗糙的舌頭變得圓潤柔滑,是一種極為美妙的享受。
「百麥加」是一條既闊又長的大街,許多小巷如蜘蛛網般分岔出去,大街小巷裡密密麻麻的盡是大小商店和流動攤子,出售各式各樣傳統的阿拉伯食物、衣服、用品。不論白天或晚上,都擠滿了不知從哪兒竄出來的人;人氣、汗氣、吵聲、鬧聲,流滿了整個空間。
天氣熱得驚人,走不一會兒,便汗流浹背了。
賣椰棗泥的攤子很多,好幾十公斤的椰棗泥好似一個小丘般黏在一起,蒼蠅麇集,看起來不太衛生,單看不吃,胃口已失。天氣炎熱,攤販的汗水百川歸海地掉進了椰棗泥裡,最為可怕的是,買回家的椰棗泥,多出了一些不該有的鹹味兒,嘿嘿!
本書特色:本書收錄了 8 篇以沙烏地阿拉伯為背景的寫實小說。作者曾旅居沙烏地阿拉伯一年,在黃沙滾滾的沙漠,作者邂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帶著各自的夢想為生活打拚。在和這些不同國家的人互動交往時,她深切地感覺到每一個人就像是一本厚重的書,每一本書的內容都是絕無僅有的,與他們的回憶成了她生命裡不可抹滅的烙印。
作者簡介:
尤今,原名譚幼今,一位南洋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曾任職於國家圖書館和報界,也曾執教於中學和初級學院,現專事寫作。尤今已出版多部作品,並多次獲得文學獎項的榮譽。 尤今的作品每年都被新加坡多所學校選為課外讀物,她的作品也成為許多大學研究生的研讀本。尤今酷愛旅行,迄今已將足跡印在地球上 100 多個國家。
章節試閱
阿里和娜拉
阿里要當父親了,
然而,娜拉卻不是當然的母親。
阿里唱的是一支快樂的悲歌,但是,娜拉唱的卻是一闕此生無盡的哀曲!
1
有一天晚上,已經八點多了,日勝還留在公司裡開會,我家門鈴忽然響了起來。我懷著警戒的心將門拉開一條小縫,朝外張望。站在門外微弱燈光底下的,是一個高瘦的阿拉伯人。他披著一方紅白相間的頭巾,穿著一襲奶油色的及地長袍,又圓又大的眼珠,在黑夜裡閃閃發亮。
「你找誰呀?」我問,雙手把門扳得緊緊的。
「請問,林先生在家嗎?」他問,清澈的目光裡,沒有半點令人起疑的邪惡。
我立即把門拉開...
阿里要當父親了,
然而,娜拉卻不是當然的母親。
阿里唱的是一支快樂的悲歌,但是,娜拉唱的卻是一闕此生無盡的哀曲!
1
有一天晚上,已經八點多了,日勝還留在公司裡開會,我家門鈴忽然響了起來。我懷著警戒的心將門拉開一條小縫,朝外張望。站在門外微弱燈光底下的,是一個高瘦的阿拉伯人。他披著一方紅白相間的頭巾,穿著一襲奶油色的及地長袍,又圓又大的眼珠,在黑夜裡閃閃發亮。
「你找誰呀?」我問,雙手把門扳得緊緊的。
「請問,林先生在家嗎?」他問,清澈的目光裡,沒有半點令人起疑的邪惡。
我立即把門拉開...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2017年年尾,到亞塞拜然旅行,邂逅了一名來自美國的遊客傑佛遜。
一碰面,便談得異常投緣。過去五年,他一直都待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而我呢,在1980年代曾在這個國家生活了一年多,那份奇特的記憶,已經定格為生命裡一個永不褪色的畫面了。
我們不約而同地談起了去年9月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頒布的一紙敕令,根據批示,沙國女性至遲於2018年6月便可以把雙手放在方向盤上馳騁四方了。這個訊息,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女性駕車,居然成了轟動國際的新聞,原因在於沙烏地阿拉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禁止女性駕車的國家。在這個男女授受不...
一碰面,便談得異常投緣。過去五年,他一直都待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而我呢,在1980年代曾在這個國家生活了一年多,那份奇特的記憶,已經定格為生命裡一個永不褪色的畫面了。
我們不約而同地談起了去年9月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頒布的一紙敕令,根據批示,沙國女性至遲於2018年6月便可以把雙手放在方向盤上馳騁四方了。這個訊息,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女性駕車,居然成了轟動國際的新聞,原因在於沙烏地阿拉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禁止女性駕車的國家。在這個男女授受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阿里和娜拉
駱駝「塔巴」
合乃流淚了
彩蝶
神經佬沙猜本
失蹤
哭泣的豆子
暗香盈處原是夢
阿里和娜拉
駱駝「塔巴」
合乃流淚了
彩蝶
神經佬沙猜本
失蹤
哭泣的豆子
暗香盈處原是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