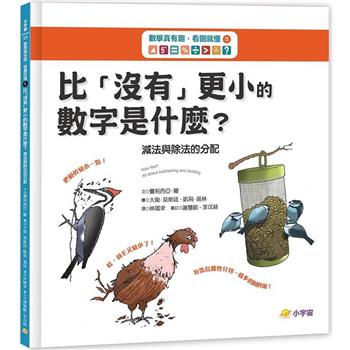雀兒喜是我見過最奇特的女孩,「無法理解」是最適合她的形容詞,聽說她一年四季總是戴著手套和圍巾,偶爾她會沒有戴圍巾,但一定會穿著高領衣,好像她的脖頸接觸到空氣就會生病似的,但這並不是她奇特的主因,畢竟這裡是國際間頗具盛名的音樂學院,來就讀的學生全是以職業音樂家為目標,如她那般保護喉嚨的學生並不少見。
雀兒喜是美國籍留學生,長得一副亞洲人面孔,她的談吐與她的外貌印象不合,初次見到她的人常誤以為她只有十六、七歲而已,可實際和她談過話就會明白,她心思縝密、應答穩重,好似面前的女孩不是年輕學生,而是一位看盡世間百態的長者。
雀兒喜主修聲樂美聲,她的歌喉美妙如天賜,可惜這裡的老師們都有藝術家包袱,他們不習慣稱讚表現好的學生,既使已經達到百分之百要求,老師們仍有辦法吹毛求疵。
教授德文的本諾老師經常說:「我在你們這年紀時,已在新天鵝堡演奏《漂泊的荷蘭人》了!你們若不拚命爭取,就等著被趕下舞台吧。」據傳,說出這話的本諾老師,聽完雀兒喜的演唱後破口大罵,把她裡外嫌得一文不值。但學生們都知道,當你讓一位老師無法克制地想要挫你銳氣,代表你優秀到令他們感受到威脅。
可惜她的好成績並未讓她有好人緣,事實上,在競爭激烈的學院生活中,一位閃亮學生散發的光芒,會使籠罩在成績落後學生身上的陰影更黑暗。
雀兒喜是位古怪的人,她會在下雨時特意出門淋雨,說起話來老氣橫秋,一點也沒有年輕女孩該有的活力,總是會在天未亮的清晨離開寢室不知去哪,直到第一堂課才匆匆現身。她很喜歡看書,幾乎到求知若渴的地步,她每週會讀完至少四本書,有次我看見她在背誦「九九乘法表」,我問她以前沒學過嗎?她只是微笑沒有多說什麼。天資聰穎與古怪行徑,兩者相加無疑令她的人際關係降到冰點。
說起來,為什麼我會知道這麼多雀兒喜的事呢?
因為雀兒喜是我的新室友。
得知新室友是演唱《莎樂美》的校園紅人,師生間的流言蜚語自然而然流進耳中,人們出於資深的優越感,總想給初來乍到的新人下馬威,從中獲得我無法理解的快感。拜此所賜,我還沒與雀兒喜本人交談過,就已經把她的豐功偉業聽了個遍。
到了宿舍入住日,我拖著行李箱,踏進葉迦娣音樂學院的女生宿舍。
聽很多人說,我們宿舍請知名設計師操刀,雖然我不理解室內設計的領域,但從踏進宿舍大樓那刻,我倒是理解這裡作為頂尖學府的驚人財力。明亮挑高的交誼大廳,頂上燈具採用音樂廳式的水晶吊燈,我的短靴踩在灰紋大理石地板上,發出清脆的回音,一旁沙發區設有咖啡機和投幣販賣機。想當然,如此重視學生居住品質的宿舍,有學生專屬健身房和游泳池,也在情理之中,假使我拍照傳給媽媽,說這裡是四星級飯店,恐怕也不會被質疑。
穿堂兩側掛著傑出校友的相片和畫像,我逐一唸出上面的人名,「鄧齊里、葉格利歐諾、札利諾娃……」每位都是家喻戶曉的音樂界巨星,是葉迦娣學院引以為傲的明星校友。
女宿舍監陳姐是位氣質高雅的女性,聽說她已經超過四十歲了,真是難以置信,她的臉龐在我看來只有三十五歲左右。她看著我的入學資料,惋惜地說:「曾經我也和妳一樣充滿創造力,但世界就是如此不留情面,但既然妳還在舞台上不願下來,我想上天會給妳出路的。」
「嗯。」我淡漠地應答。
我原本在倫敦攻讀鋼琴,因一場意外,從此失去左手小指和無名指,當時父母親都勸我放棄音樂,那些柔情勸說的話語,最終被我用一紙轉學簡章堵住。
我還不想走下舞台,既然彈不了鋼琴,那就讓我用音符起舞,我告訴他們,我會用其他方式贏得屬於我的掌聲。
葉迦娣音樂學院,是我的第二個戰場。我將在這裡,用作曲能力活下去。
舍監陳姐為我介紹穿堂上的名人照片,她說:「穿堂上的校友們都曾住在這棟宿舍中,我很期待有朝一日能將妳的相片掛上去,李蘋柔同學。」
我望向牆上的相片,想像著其中一幅的臉,變成自己棕色短髮的平凡相貌、吝嗇笑容的緊抿雙唇、排外的警戒眼神,以及一張不常表露情緒的僵硬表情,冷淡看著每一位路過的師生。我的臉肯定不適合招生。
陳姐說她曾擔任五星級高檔酒店的駐點演奏家,可惜她的音樂之路並不順遂,最後在多方介紹下,來到葉迦娣學院。在這所學校,連宿舍舍監都是音樂家,我不禁想像打掃校園的清潔人員,或許是前首席指揮之類的人物。
話又說回來,比起校內軼聞,或許我該優先擔心自己的處境。
上課第一天,坐在隔壁的女孩大聲對我說:「妳住雀兒喜那房?我可沒妳的勇氣。」
另位女同學湊過來,邊笑邊說:「妳是雀兒喜的第三位室友了,祝妳有愉快的學院生活,新同學。」
她們嘻嘻笑笑說了很多雀兒喜的八卦,多數都不好聽。其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一句話是──妳該慶幸,妳已經先斷過手指了,新.同.學。
幾天後,有救護車衝進學校載走滿手鮮血的同學,耳聞他剛被選為這季音樂劇的首席小提琴,就莫名在道具間被發現手筋被割斷,一旁掉落沾血的道具劍,彷彿在說是他自己不小心弄傷的,可任何人都清楚,這麼嚴重的傷勢,不可能是道具劍造成的。
我想葉迦娣就是這樣的地方。
當每位學生都是實力強悍的佼佼者,勝負往往在咫尺之間,只稍一個失誤就會被替換掉,若不幸勢均力敵,那便是看誰能在聚光燈下存活。如果我手裡握的劍不夠鋒利,遲早有一天,我也會躺上救護車,在擔架床上懊悔自身軟弱。
雀兒喜深知這所學院的生存之道,她在舞台上的傲慢和野心,是一種宣示,也是一種防護機制。
我抱著複雜的心情,打開寢室門,迎接我與校園女王雀兒喜的首次會面。
宿舍的雙人寢室採用左右對稱設計,房間盡頭是一扇大窗戶,以窗戶為中心,左右各有書桌、床鋪、衣櫥等基本家具。左方空床上疊著乾淨的床單和枕頭,右方的床上坐著我的室友。
在這溼熱的天氣下,雀兒喜如傳言所述,面不改色穿著高領衣,套著黑手套的手指輕輕翻動手上的書頁,她將長長的黑髮撥到耳後,露出美麗的側臉,低垂的視線細細品味書中文字,靜謐的氣氛讓我不禁屏住呼吸,深怕打擾到她的閱讀時光。
外頭將她傳得似神似鬼,但在這間寢室內,她僅僅是一位喜愛看書的漂亮女孩,我對這位室友稍稍改觀。
聽見開門的動靜,「妳來了。」雀兒喜冷漠地說。從她冷酷的視線能感覺到她的緊繃。
我做好被威嚇的心理準備,「妳好,我是李蘋柔。」
「我是雀兒喜,請自便,有問題可以問我。」
雀兒喜的視線掃過我的手指,從她的態度來看,她和我一樣,提前聽說了很多事情,包含我曾截肢的不堪往事,她沒有對我冷嘲熱諷,也沒有像惡狼看見熟肉一樣撲上來猛咬,看樣子我的新室友,沒有傳言中那麼難相處?至少在我眼中,她和班上的八卦女生比起來好多了。
剛到新學校很難熬,我不認識任何人,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新來的轉學生」,那些打量的眼光如芒刺在背。我能感受到同學們輕蔑的視線,他們可憐我的殘缺,卻又因我不具威脅性而鬆口氣。
某日,我趁著空堂時間在校內四處走走認識環境,無意間撞見有兩人起爭執,她們看上去像母女,還在思索她們在吵什麼時,母親已經一巴掌打下去,響亮的巴掌聲引來周圍學生的側目,那位母親情緒失控喊道:「──妳以為我們借了多少錢才讓妳進這學校!擔當獨唱這要求很過分嗎?怎麼這點事都辦不到!這下好了,所有錢都投資在妳身上,連妳爸爸住院我們都付不出錢,沒用的東西!」
被打的女孩似乎是聲樂系的,她母親真不知輕重,居然打聲樂人的嘴巴。
僅僅一瞬,我與那女孩對上視線了。她瞪著我,臉上寫滿憤怒與不甘心,好像是我害她落到如此下場。
糟了。
我迅速離開,渾身冷汗直冒,那女孩瞪我的眼神十分怨毒,充斥著無處發洩的憤恨,不知道她會做出什麼事來。我因為太慌亂,又不熟悉學校環境,多繞了遠路才終於走回宿舍。
只差一點,就快回到寢室了。
「喂。」一個聲音叫住我。
我的後領被一股力道往後拖!整個人重心不穩後仰,還沒意識到發生什麼事,一隻手用力捏住我的嘴,阻止我大聲呼救。我回頭一看,對上一雙面無表情的臉,是剛才被母親打的女孩。
「新同學,看得很開心?」頰上還留著紅掌印的女孩冷笑道:「我記得妳是雀兒喜的新室友?那個賤人!都是因為她!她不在的話,我一定可以拿下那個角色,都是因為她我家才會……該死,該死該死該死!」
「唔唔!」我猛搖頭,試圖告訴她我什麼都不知道,但她抓得又狠又緊,完全不給我逃跑的機會。
女孩的語氣變得甜膩,她拿出一把大鐵鎚,哄小孩似的說:「妳幫我一個忙,好嗎?」我嚇壞了,更加拚命掙扎,「我只要喉嚨還在就行了,管它是手還是腳,只要重傷我就能拿到保險費。」
她鬆開我的瞬間,發狠把鐵鎚往自己小腿砸下去!
「啊啊啊!她打我!轉學生打我!來人救命啊!」她丟下鐵鎚發出尖叫。
我嚇得腿都軟了。
她的尖叫立刻引來很多圍觀人,看熱鬧的同學拿出手機,拍照、錄影聲此起彼落,喀擦喀擦的聲音將我團團圍住,我感覺像是被脫光衣服丟進人群中,嚇得腦中一片空白。
「不是我……」微弱的辯解聲傳不出去。
我看見那女孩一邊痛苦大叫,一邊露出扭曲的笑容,彷彿在說「沒辦法拉上雀兒喜,至少要拖她的室友陪葬」。
突然間,人群中傳來一道洪亮的女性聲音。
「不是她做的。」
具有威嚴的聲音讓吵雜的眾人噤了聲,所有人看向發聲者。
來人是雀兒喜。
襲擊我的女孩看到雀兒喜出現,放聲大叫:「妳閉嘴!就是轉學生攻擊我的!」
「我都看見了。」雀兒喜直接否定她,一字一句地清晰陳述:「是妳強拉走轉學生,用鐵鎚打自己又誣陷她。」
雀兒喜的證言適時幫了我一把。後來學校老師聞聲趕來,那位襲擊我的同學被拉走時,整個人失魂落魄的,嘴裡唸唸有詞、雙眼無神,之後再沒有聽說她的消息了。
從那次以後,我嘗試和雀兒喜交談,我想知道飽受各種評論的她,真實是怎樣的人。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室友雀兒喜的夜詠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94 |
其他科幻/奇幻小說 |
$ 332 |
華文奇幻魔法/科幻冒險 |
$ 370 |
中文書 |
$ 378 |
華文奇幻/科幻小說 |
$ 378 |
其他科幻/奇幻小說 |
$ 37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室友雀兒喜的夜詠
★斜槓作家「蕗舟」最新校園百合奇幻作品!
★收錄實體版限定番外〈專屬妳的花園舞會〉♡
★Irene309、武佳栩、草子信、魚落井──純愛推薦!
悶騷自卑轉學生‧李蘋柔 × 孤傲神祕校園女王‧雀兒喜
一場意外截去李蘋柔兩根手指,就此斷送她的鋼琴家夢想,為求重新開始,她轉進頂尖藝術名校繼續奮戰,未曾料想到,她的宿舍新室友──聲樂系明星雀兒喜,將徹底顛覆她的生活。
雀兒喜是位行徑古怪卻才華洋溢的少女,演唱風格既霸道又傲慢,神祕的氣質使蘋柔深受吸引,可隨著兩人關係日漸深厚,她發現雀兒喜身上隱藏著巨大祕密……
Ma il mio mistero è chiuso in me,(有個祕密隱藏在我心中)
il nome mio nessun saprà! (我的名字無人知曉)
「雀兒喜夢想實現那刻,就是世界毀滅的時刻。」
作者簡介:
作者/蕗舟
熱愛靈異神怪及懸疑故事,經常聽鬼故事當睡前消遣,其實很容易被嚇到,沒辦法一個人看恐怖電影。
2021年踏上寫作之旅;2022年加入Penana駐站作家,以《燈籠奇譚:漣下燈》獲第一屆kadokado百萬小說創作大賞短篇組複選;2023年以《府城青年旅館之謎》獲第一屆臨淵齋短篇通俗小說決選;2024年以《吳服店假人殺人案》獲第二十二屆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入圍。
著有長篇小說《雨珈琲怪談夜話》、《長生不老的我流浪到台灣》。
繪者/VISE
雖然在畫圖卻更喜歡寫故事的業餘插畫家,品味被留在上個世紀,喜歡復古或華麗的東西,也喜歡繪製各式各樣的女性角色。
章節試閱
雀兒喜是我見過最奇特的女孩,「無法理解」是最適合她的形容詞,聽說她一年四季總是戴著手套和圍巾,偶爾她會沒有戴圍巾,但一定會穿著高領衣,好像她的脖頸接觸到空氣就會生病似的,但這並不是她奇特的主因,畢竟這裡是國際間頗具盛名的音樂學院,來就讀的學生全是以職業音樂家為目標,如她那般保護喉嚨的學生並不少見。
雀兒喜是美國籍留學生,長得一副亞洲人面孔,她的談吐與她的外貌印象不合,初次見到她的人常誤以為她只有十六、七歲而已,可實際和她談過話就會明白,她心思縝密、應答穩重,好似面前的女孩不是年輕學生,而是一位看...
雀兒喜是美國籍留學生,長得一副亞洲人面孔,她的談吐與她的外貌印象不合,初次見到她的人常誤以為她只有十六、七歲而已,可實際和她談過話就會明白,她心思縝密、應答穩重,好似面前的女孩不是年輕學生,而是一位看...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推薦序】追逐夢想的序曲/魚落井(Penana駐站作家,代表作品《垃圾》)
你敢站在舞台上,向世界大聲宣告你的夢想嗎?
舞台的紅絨幕布拉開,熾亮的射燈下,雀兒喜啟唇歌唱。舞台下的黑暗中,她的室友李蘋柔因那美妙的歌聲而渾身起了鷄皮疙瘩,為之神魂顛倒;我也為之傾倒,不由自主地翻到下一頁,追逐那神祕詭譎的旋律,與兩位女主角若即若離的身影──
蕗舟是我見過最奇特的作者,「無法預測」是最適合她的形容詞。她總是能以文字為音符,譜寫出無法輕易揣摩走向的精彩情節,細膩的筆觸奏出觸動人心的和弦,叫讀者沉浸在曲子的氛圍裡...
你敢站在舞台上,向世界大聲宣告你的夢想嗎?
舞台的紅絨幕布拉開,熾亮的射燈下,雀兒喜啟唇歌唱。舞台下的黑暗中,她的室友李蘋柔因那美妙的歌聲而渾身起了鷄皮疙瘩,為之神魂顛倒;我也為之傾倒,不由自主地翻到下一頁,追逐那神祕詭譎的旋律,與兩位女主角若即若離的身影──
蕗舟是我見過最奇特的作者,「無法預測」是最適合她的形容詞。她總是能以文字為音符,譜寫出無法輕易揣摩走向的精彩情節,細膩的筆觸奏出觸動人心的和弦,叫讀者沉浸在曲子的氛圍裡...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各界名家推薦】
【推薦序】追逐夢想的序曲/魚落井
一 ♪ 名為雀兒喜的女孩
二 ♪ 游泳池祕事
三 ♪ 怪異魅影
四 ♪ 魚頭棋子
五 ♪ 燈下黑
六 ♪ 伴君如伴虎
七 ♪ 海民院聚
八 ♪ 掌控
九 ♪ 聯合徵選季
十 ♪ 暗夜探查
十一 ♪ 逼霧現身
十二 ♪ 強者孤寂
十三 ♪ 陰風湖的她們
十四 ♪ 雀兒喜的結心儀式
十五 ♪ 骸心浮島
十六 ♪ 室友雀兒喜的夢想
番外 ♪ 專屬妳的花園舞會
後記
【推薦序】追逐夢想的序曲/魚落井
一 ♪ 名為雀兒喜的女孩
二 ♪ 游泳池祕事
三 ♪ 怪異魅影
四 ♪ 魚頭棋子
五 ♪ 燈下黑
六 ♪ 伴君如伴虎
七 ♪ 海民院聚
八 ♪ 掌控
九 ♪ 聯合徵選季
十 ♪ 暗夜探查
十一 ♪ 逼霧現身
十二 ♪ 強者孤寂
十三 ♪ 陰風湖的她們
十四 ♪ 雀兒喜的結心儀式
十五 ♪ 骸心浮島
十六 ♪ 室友雀兒喜的夢想
番外 ♪ 專屬妳的花園舞會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