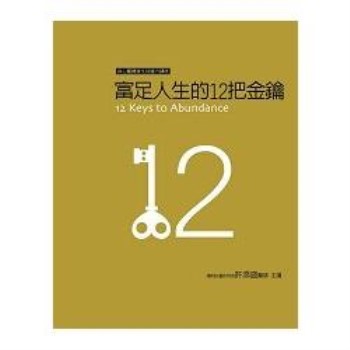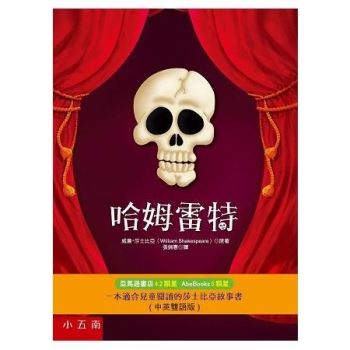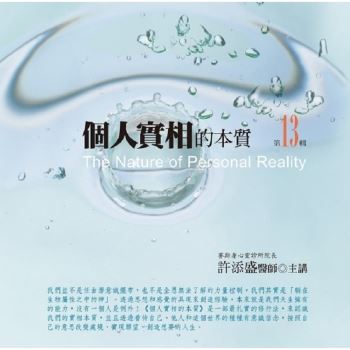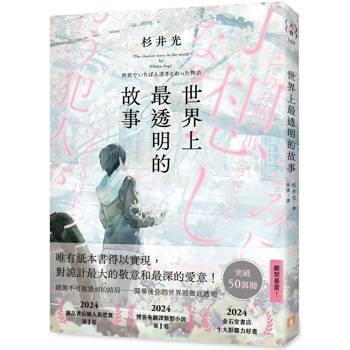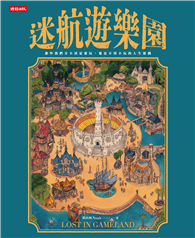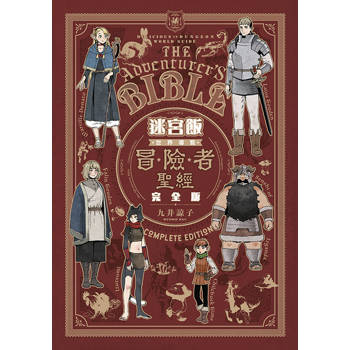那些舊信中也夾雜有些零散的日記、個人讀書筆記甚至是書中文字的摘錄等等。收集這些舊日文字的老友實在是有心了。人的記憶如同篩子,我們都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篩除那些如今心中厭棄的舊事。例如自己雖被不少同學誇讚為「過目不忘」的好記性,卻獨獨對於某些當年可稱為大陸知青人生旅程中的「大事」毫無記憶,或無意中從腦中篩除得一乾二淨。例如自己也曾申請「入團」(即指共黨下轄專為青年人官辦的「共產主義青年團」)被拒,甚至還有獲選在當年似乎是難得的「榮譽」—參加當年北大荒「師部」3舉辦的首屆「知青寫作培訓班」。於我,這些舊事想必是當年自己既厭倦卻不得不遵令參與的行為,便自動成為記憶中的空白。白紙黑字卻是我們記憶中那些舊事的證人,雖如今厭惡卻必須承認的真相。如今老友將這些舊日文字託付於我,是望我可以補綴成篇,使一個甲子之前的朋友得以再次回望我們一代共同走過的舊路麼?或是使我們在文字中得以重聚?似乎都不是僅止於此。自己究竟為什麼要執拗地想講述那些一個甲子之前的舊書信?要執拗地回望舊路?是只想用文字留下我們一代人對人世的眷戀麼?我想自己執拗地集信成文,並非簡單的念舊,況且那些舊信中大都不是些引起歡愉的記憶。或許我們的後代讀到這些舊信會莫名所以,或是感到那些信的內容如同墳墓中鬼魂發出的夜吟。那麼,希望我們的後代會多追問一句,這些「鬼魂的夜吟」起源何在?何人是「始作俑者」?若能引得後人有如此一問,我今日重述我們一代的舊日文字便並非無意義。它們或許會成為我們的後代為華夏大陸開啟再無「鬼魂」、「幽靈」或蠱毒的新時代密碼字元之一。願上蒼准我之所求,願這些舊日記憶匯入數億人心中那條記憶的江河。那條江河終會於未來某日倒捲,以滔天巨浪沖毀四壁高築的那口井,使得囚於那口井中超過十億的心靈會再次見到海闊天空。
雖然因病因傷或是自戕而埋骨於鄉間的早逝知青難以數計,但大體上那些舊信代表的十年只占了我們一代多數人一生的十分之二三,但那豈非是人生本該最張揚透明的好年華?從少年的澄澈明亮任性張揚逐漸領悟到沉穩與思索與獨立,成長為青年,如枝頭花蒂正孕育為累累青果。那短短幾年的好年華轉縱即逝,之後人生雖在繼續,到底是韶華不再了。那是永遠也找不回的年華。那下鄉插隊的十年是我們一代人從青蔥少年初入紅塵的歲月,而那時的我們即便是猝不及防被丟棄入紅塵,尚不忘帶好那自認為是裝滿「革命」與「自我改造」真誠心願的書包。但是世事又何曾如人意?事實上的我們,在這十年期間從意氣滿懷逐漸體驗到何為徬徨無措,又何為惆悵孤帆,終於是將那些書包裡的信念翻轉。我們轉成逆旅行人,同時在此過程中逐漸長成為青年。
這些書信至今也已經年近花甲,寫信的舊時朋友亦是早已經分別安家於五湖四海,終於是「漸行漸遠漸無書」,驀然回首已經是失散了舊友蹤跡。曾幾何時,我們視性情相近、相互信任到可以毫無保留地交出一顆心的同學為家人。例如我自己,甚至在「上山下鄉」之前按大陸組織規管必須填寫的《家庭情況表格》中將親近的同學填入,作為家庭成員,在《表格》中標為「關係」的一欄中填寫為「極親密」。這樣的表格必然會因不符合「組織規則」而被退回,作為廢品,須重新填寫。這些舊書信中便夾雜了數張如此的「廢品」。雖華夏大陸自毛氏建立政權以來雖然無異國入侵,我們一代卻自少時便數度經歷共黨高層內部爭鬥引發的社會動盪,那些動盪對於小民人生際遇與兵荒馬亂的戰爭亦差相彷彿,因而每個人難免有盛衰交雜的不同人生。不知道那些當年的朋友,曾在《表格》中被填寫為「極親密」的「家庭成員」的同學,一個甲子後的今天是否依然互通音問?甚至能否再相互傾心而談?」青陽逼嵗除,紅塵催人老,即如「回首已是百年身」。將近十年期間的千封書信,如今來讀,又可表達何種訊息?我想時間或是上蒼對人類的悲憫,是世間人類獲得拯救的惟一窗口。時間一秒一分地推移,永不會遵從任何獨裁者的意志而停頓下祂的腳步,任何獨裁者達到其權力與地位頂峰的一刻亦是其權力與地位下落的開始,這世間尚未見識到任何獨裁者與其創建的王朝是從「輝煌走向更加輝煌」,那只是獨裁者夢中才會出現的幸運,是虛幻世界的影像。紅粉骷髏不過是轉瞬間的輪替,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永遠會世代更替,我們一代人終將離開現世。我們終將被後代遺忘,我們今生某時自我認為是重要甚至是「偉大」的某些行為或觀念,於將來的某時可能被認作是可笑、愚蠢,甚至是罪惡的。我期盼那個「將來某時」在大陸中國儘早地實現,成為大陸中國的真實世界。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桃李一別後:與女兒讀我們一代少時書信之一的圖書 |
 |
桃李一別後:與女兒讀我們一代少時書信之一【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逸之、Lauren X. Ma 出版社: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2-10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桃李一別後:與女兒讀我們一代少時書信之一
那些舊信沉埋於記憶的深水之底,筆尖澀澀探入,
挑起的是近五十年前的一段歲月,
晝夜之梭以一代少年時的心路織成經緯,織出的盡是晦暗,
那歲月的絲絲縷縷中缺失行行且遊獵,駐足於山巔的少年意氣,
只蘊含迷失質疑與苦苦尋覓,人生之路卻是覓而不得,
願拙筆可勾勒出那晦暗歲月中,天良在執拗地呼喚我們人性的回歸。
作者簡介:
逸之
五○年代生於大陸中國,現居澳洲。祖輩父母皆就學畢業於基督教會學校,以專業人士立足於世。逸之學齡恰逢大陸文革而失學,有幸於文革結束後進入大學。法學院畢業後最終走進職場,數十年輾轉於不同國家與律師事務所,現已退休。嘗試以文字記述大陸紅色政權之下,自己與同代人的所經所見,尤其是我們一代人性在紅色教育下的喪失與其中的人性回歸。不過即使有人得以人性回歸,那回歸的往往也是殘缺與扭曲,或蘊含了無盡遺憾。
章節試閱
那些舊信中也夾雜有些零散的日記、個人讀書筆記甚至是書中文字的摘錄等等。收集這些舊日文字的老友實在是有心了。人的記憶如同篩子,我們都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篩除那些如今心中厭棄的舊事。例如自己雖被不少同學誇讚為「過目不忘」的好記性,卻獨獨對於某些當年可稱為大陸知青人生旅程中的「大事」毫無記憶,或無意中從腦中篩除得一乾二淨。例如自己也曾申請「入團」(即指共黨下轄專為青年人官辦的「共產主義青年團」)被拒,甚至還有獲選在當年似乎是難得的「榮譽」—參加當年北大荒「師部」3舉辦的首屆「知青寫作培訓班」。於我,這些舊...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緣起—「青山只會磨忠骨,綠水何曾洗是非」
M市冬末天氣如同喜怒無常的幼兒,常是於一日間使人世嚐遍陰晴冷暖,例如北風捲地、冷雨霏霏瞬間變幻為雲退風霽、豔陽高照,或是相反。澳洲人似乎不存在華夏文人緣於四季變換而傷春悲秋的敏感情緒,或許是由於天氣變幻無常無關於他們日常生活的安穩。上帝從未許諾人世永遠是暢日和風、綠茵鋪地的美景。
恰是M市冬末的某日,本是寒雨淋漓,枯坐家中,卻忽有鴻雁翩翩,叩開柴門,攜來沉甸甸兩箱郵件,如同千年之前的詩人經歷的歡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
M市冬末天氣如同喜怒無常的幼兒,常是於一日間使人世嚐遍陰晴冷暖,例如北風捲地、冷雨霏霏瞬間變幻為雲退風霽、豔陽高照,或是相反。澳洲人似乎不存在華夏文人緣於四季變換而傷春悲秋的敏感情緒,或許是由於天氣變幻無常無關於他們日常生活的安穩。上帝從未許諾人世永遠是暢日和風、綠茵鋪地的美景。
恰是M市冬末的某日,本是寒雨淋漓,枯坐家中,卻忽有鴻雁翩翩,叩開柴門,攜來沉甸甸兩箱郵件,如同千年之前的詩人經歷的歡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緣起—「青山只會磨忠骨,綠水何曾洗是非」
第一部 是是非非竟不真,桃花流水送青春
「這裡就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1968年:知青,綠皮專列卸下的貨物
「人牛力俱盡,東方天未明」—1968年末至1969年中:「舞盡桃花扇底風」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1969年末至1971年:知青心中疑惑的起始
「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是夢中?」—1970至1971年,革命?再教育?進退維谷中的知青
「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1971年:林彪事件
「分水嶺,煙雨正淒涼」—1971年至1...
第一部 是是非非竟不真,桃花流水送青春
「這裡就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1968年:知青,綠皮專列卸下的貨物
「人牛力俱盡,東方天未明」—1968年末至1969年中:「舞盡桃花扇底風」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1969年末至1971年:知青心中疑惑的起始
「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是夢中?」—1970至1971年,革命?再教育?進退維谷中的知青
「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1971年:林彪事件
「分水嶺,煙雨正淒涼」—1971年至1...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