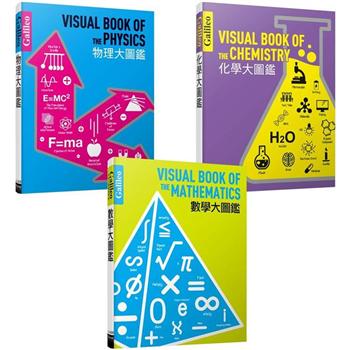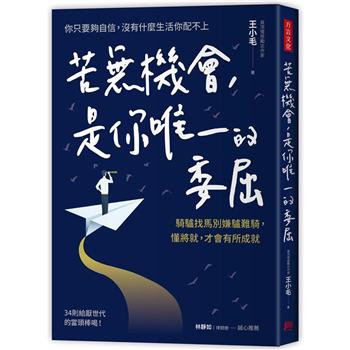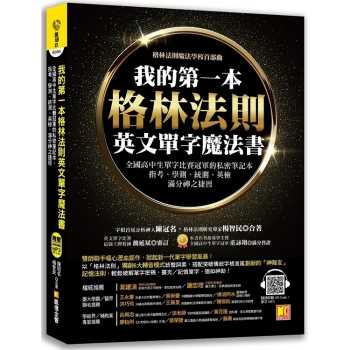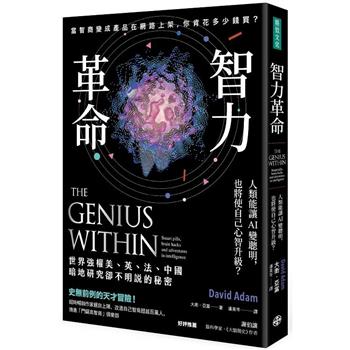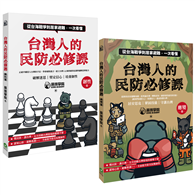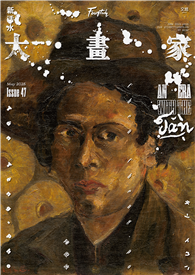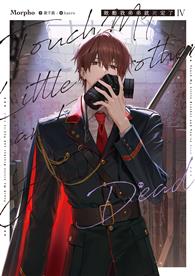看見一顆心,他說要忘記那是愛和奉獻的泉源。
打開一顆心,他會為它填進靈魂和人生。
以手術刀書寫逾半世紀,靠雙手點燃生命萬種奇蹟
★ 入圍柯斯塔傳記獎,《周日泰晤士報》暢銷榜眼、英國醫學會主席獎
★ 售出多國版權,亞馬遜4.6顆星、豆瓣9.1分,過萬讀者震撼淚推
生與死,心臟外科醫生握著兩端的繩子。
死神就坐在他的肩頭,只要手一滑,生命將永遠消逝。
超越影劇的真實人生,最刺激職涯作品集
心臟外科的手術室裡,沒有任何時間猶豫——你得用血沐浴雙手,將生命的脈動注入身體;膽小的人沒勇氣承擔,瞻前顧後者則注定錯失良機。這是史提芬.維斯塔比反覆上演的日常,旁人聞之喪膽,他卻渾然忘我,只信「救得活」。
維斯塔比是心外科的傳奇人物,也是英國第一位用人工心臟延續生命的業界先驅。在這本高潮迭起的著作中,他以獨特的最前線視角洞察心臟手術中時而鼓舞、時而淒涼的世界,同時用直白且略帶幽默的筆觸,訴說那些最驚心動魄,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手術台經歷。
心有多脆弱,就有多頑強——
如果不明白,看一場心臟手術就懂了。
■ 出身底層的起點,通向挽救眾生的使命
煉鋼廠、汗水和蒸氣,是維斯塔比童年的背景。他從一座工業小城一路闖進劍橋醫學院,在屍體、鮮血與太平間中構築起他的志向:成為一名心臟外科醫生。
■ 絕不循規蹈矩,「救命」是唯一道德標準
每一場手術,都是代價高昂的冒險:從英國到南非、沙烏地阿拉伯到澳洲,只要有一絲機會,再驚險都玩命一試……冒的不只是患者的命,還有醫生的。
喝完酒怎麼動手術?靠一雙「前人」的靴子搞定;
把心臟改造成香蕉形狀,竟能救回年幼的生命;
史無前例的機械裝置,可以取代真實跳動的心;
一顆心臟撐不下去,就用「兩顆心臟」化解危機。
沒人比他更明白心臟「跳」與「停」的距離,
死神的鐮刀有時難逃——但,萬一可以呢?
本書特色
■超越劇本的真實人生:每章至少一起精彩案例,跟著傳奇名醫維斯塔比的視角,親身體驗手術台上分秒必爭的殘酷,以及面對緊急情況的鬥智鬥勇。
■作為「救贖者」的矛盾:從第一現場,看見作為醫生的掙扎——願意拚盡一切只為救回一命,面對生命消逝卻不能投入感情。
國際媒體、各界好評推薦
這位心臟外科先驅的回憶錄充滿血腥、肌肉和腎上腺素,書中的情節令人難以置信……有時,它讓人心跳加速到不行。——《星期日泰晤士報》
正面而驚心動魄的描繪。在這本迷人的書中,每個故事都帶來一場令人緊張的嶄新手術冒險……它在許多層面上都取得了成功:政治鬥爭的吶喊、血腥壯舉的記錄、現代心臟病學的歷史,以及對患者的致敬與手術的讚歌。——《每日電訊報》
維斯塔比具備了你對特立獨行的外科天才的所有期望:權威、投入、熱情和固執己見。作為一個只寫過醫學論文和手冊的人,他的文筆好得令人惱火,讀起來就像一本驚悚小說,只是屍體更多。你會急著翻到每章的結尾,看看他那必死無疑的病人是否安然無恙。——《泰晤士報》
醫生職業是利他主義的。維斯塔比,這位與我同時代學醫的醫生,面對著難以想像的風險與挑戰,在努力把一個個現代醫學幾乎無能為力的患者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除了失敗,還有法律和倫理設置的禁區。我十分感慨的是,維斯塔比講到,在當今英國(不僅是我感受到的中國)的醫療環境下,已很難甚至不可能培養出這種優秀醫生了。這正是醫學教育和醫藥衛生改革需要深思的問題。——胡大一,著名心血管病專家,醫學教育家
雖說心臟外科救助場景不是影視劇,但卻時時上演著驚心動魄的生死大戲。心臟外科大夫的腦洞比影視編劇大得多,患者在苦難的過山車上跌宕的程度也比好萊塢大片刺激得多。——王一方,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
作者是一位厚顏無恥、鐵石心腸的執刀者,也是一位悲天憫人、熱血澎湃的救贖者;本書則既是一部催人淚下的系列人間悲劇,也是一部讓人忍俊不禁的外科醫生養成史。——李清晨,兒童心胸外科醫生,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