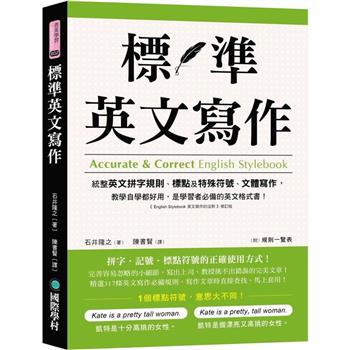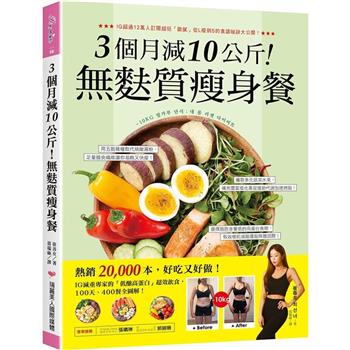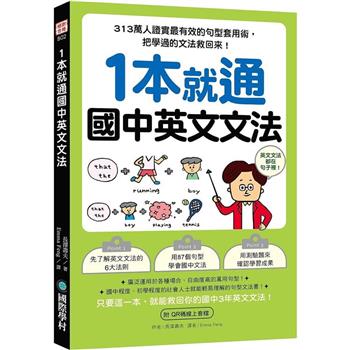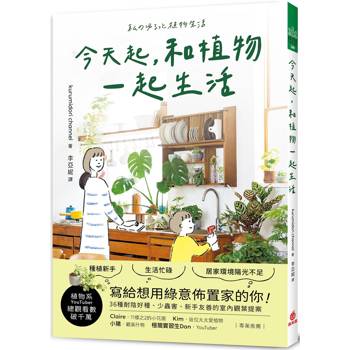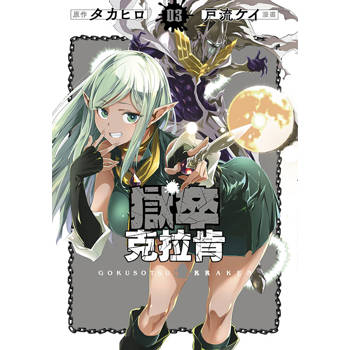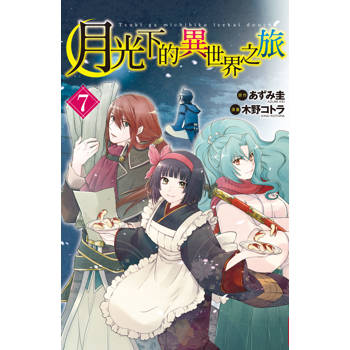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姯影:七○年代台灣女性小說家的文學再發現的圖書 |
 |
姯影: 七○年代台灣女性小說家的文學再發現 作者:戴華萱 出版社: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12-30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姯影:七○年代台灣女性小說家的文學再發現
肖瓦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觀察到,女性作家經常被屏棄在經典之外。即使她們關注的議題與男性相同,其創作仍有意無意地被遺忘、忽視。因此,唯有重新挖掘被淹沒和不被重視的女作家作品,文學史的關照才能更多元全面。
幾乎所有文學史的著作論及台灣二十世紀女性創作的兩個黃金期,都坐落在五、六○年代和八、九○年代,僅輕描淡寫地帶過七○年代的女性作家。然而,儘管女性確實不喜歡寫鄉土,但是七○年代為數不多的女性鄉土小說也不應在文學史中缺席。尤其男性作家呈現單聲調的創作公式與女性形象,挖掘女性的聲音才能更立體地呈現鄉土文學的全貌。
雖然台灣女性文學研究在現今學界已然大鳴大放,但七○年代女性作家的相關研究卻相對闕如。因此,本書就以七○年代的四位小說家曾心儀、謝霜天、季季、荻宜為研究對象,將同類型文學的主流男性作家為參照的隱線,分別自勞工文學、女性性工作者文學、大河小說、農村文學以及武俠小說的主題文學,從而產生性別的對話、差異與補充。此書的五篇專文不僅讓台灣文學的樣貌呈現出不只是單一性別的論述,同時讓七○年代的女性小說家浮出歷史地表。
作者簡介:
戴華萱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成長小說、李昂研究、性別研究。著有《聚光燈外──李昂小說論集》、《成長的迹線──台灣五○年代小說家的成長書寫》、《鄉土的回歸──六、七○年代台灣文學走向》。主編《咱的土地,咱的詩──台語地誌詩集》、《連易宗影像拾珍──一九六○年代的淡水/台灣》、《打開淡水老信徒的相簿──淡水長老教會那黑與白的年代》、《那些年,淡水古蹟說故事》、《淡水牛津學堂典藏拾珍》、《臭油棧──那二十年在殼牌倉庫的歲月》。
推薦序
自序─微姯流轉
自從任職於台灣文學系後,我對女性文學的研究始終情有獨鍾。我想,有很大的原因,是我在文學中發現早期多數的女性作家總是顯得微弱,甚至常被忽視的性別劣勢,和我自己的生命經歷有很大的共鳴。在我讀博士班的二十一世紀初,我不斷被親友恐嚇學歷太高會有嫁不出去的剩女危機,曾因在意他者的眼光而忐忑不安。進入婚姻後,不僅得周旋於廚房與書房、娘家與婆家,還要負擔較多照料幼女的責任;爾後在初任教職的很多年,苦惱於無法寫出一篇上得了檯面的論文而焦躁不已。也許是因為親歷性別不對等的真實感受,我對於台灣文學...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微姯流轉
導論
勞動與性別─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女性勞工書寫比較與對話
一、前言
二、勞動場域的透視
三、內在心理的透視
四、結論
曾心儀小說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研究
一、前言
二、關懷女性性工作者的主體性
三、批判跨種族男性同盟
四、隱喻獨立自主的國族寓言
五、結論
客家女性的歷史長河─論謝霜天《梅村心曲》的女性歷史關懷
一、前言
二、作為第一部台灣女性大河小說的《梅村心曲》
三、《梅村心曲》具女性意識的客家女性特質與深度客家日常
四、結論
女性鄉土─季季...
顯示全部內容
|